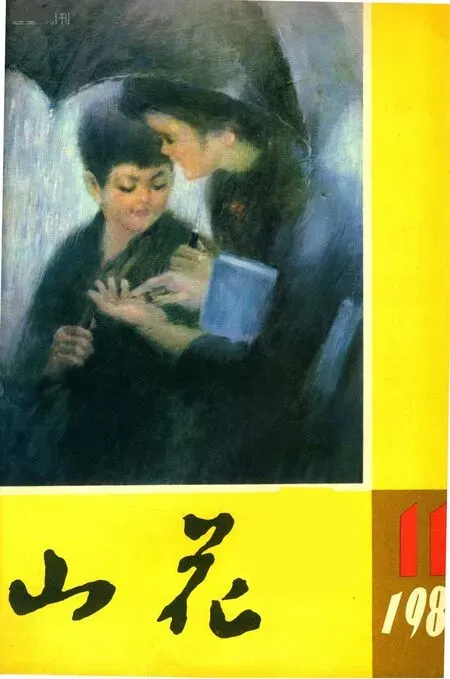撬坟记
阿乙
“破归破,德国货。”下沅村党支部书记对村委会主任这样说。
他们刚刚屁股不沾座垫,左一蹬,右一蹬,挥汗如雨,自村委会所在地骑来。他们是来觌见亲征的镇党委委员、常务副镇长何东明的。后者正在为自己此行犯委屈:从未见交给自己什么美差,碰上平坟这样的事就说,爱卿你来,要权给权,要人给人,尚方宝剑在尔手尔可以先斩后奏。村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将主要精力花在夸说何副镇长新配的奔驰二手车上。他们左手搔头,右手抚摸、擦拭轿车前盖,直到将罅缝间的油泥全都抠出来。虽说,死者、大恶人宏阳猝死当日,其堂弟宏彬前来村委会陈请土葬事宜时,他们并未完全同意(他们是这样说的:“只要镇里同意,我们好说。”宏彬说:“镇里不同意我来找你们干吗。”因此他们再次说:“只要镇里同意,我们也就不会有什么意见。”事后他们还彼此作证,将宏彬行贿的财物登记入册),但只要镇里追究起来,他们还是罪责难逃,可谓是包庇纵容甚至是带头参与违法违规殡葬行为,轻则诫勉,重则免职。他们还不能申辩“这是经由你们同意的”,虽则他们听闻,在死者宏阳昔日举办寿宴时,开玩笑说自己一旦死了就要土葬时,镇上诸要员可都是爽朗地答应了的。
何东明何副镇长朝他们点点头,背着手看风景去了。他何辣子就是喜欢看见对方这样一副惴惴然如履薄冰的样子。虽然于情于理他都应该(而且一定会)宽恕对方,但他不会这么快就将这个意思表露出来。也许到今日的事情完结,甚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不会就此表态。就让对方自个儿去琢磨、咀嚼这事儿吧。今日他带的人马足够,仅官吏就包括镇武装部长,副镇长,副科级维稳信息督导员,镇团委书记,综治办专职副主任,民政所所长,派出所教导员,土管所所长,经管站站长,水管站站长,计生办副主任,财政所副所长,文化站站长,卫生院副院长,合计十四员,要文文,要武武,已无须村委会从中转圜。起初,当他率领八十人光降时,本地小组长(犹如《西游记》中土地老儿)如苍蝇急急飞来,从七元一包的软红金圣烟(还是葬礼上遗留下的)里捉出一根,请示他抽烟否。
“不会。”何东明恶狠狠地说。只这句话就将小组长撂向一边。后者遥遥地站立着,陷入长久的恓惶中,微微发抖。何东明真想告诉他,为何不清洗下指甲里蓝黑色的泥垢呢,水沟都要清洗何况人乎。何在这里等待底下人去将宏阳那在河边临流浣衣的家属寻回。
从家属的穿扮——上身:全蓝的确良军装(系由本村复员军人所赠),下身:青色开了线的老人裤、黑色雨靴,顶上:铁灰色的头发只用块把钱的发夹夹住;神态——冷漠,茫然,像驴一样带有一股寒酸的傲气,看不出她就是继承了丰厚遗产的新孀的寡妇。她朝系在腰间的防水围兜抹手上的泡沫,望向晒谷场:计轿车七台、小客车二台、警车救护车宣传车货车各一台。最远的停到村头。货车车厢装有一台挖掘机,杏黄色的动臂悬在空中,高十数步,像是要将附近谁的屋顶给吊走或推倒。行前计议此事时,镇党委书记问纪委书记:“我欲走艾湾艾宏阳撕开口子,王书记度用几何人而足?”王书记说:“不过用二十人。”问何东明,何云:“非八十人不可。”书记点头称善。确定出征前,何东明亲自到派出所查户籍,看艾湾青壮人口数目到底几何。大军过汽配厂,他又令停车,请修理工评估车队车况,确保中途不会掉什么链子。
如今,何东明只是要底下去向寡妇宣布政策。虽则也可不宣布,但宣布还是要比不宣布好。日后人家告状时“在根本就没打招呼的情况下”这句就写不进去。
“你是死者艾宏阳的家属吗?”民政所的小马问。
“我是水枝。”她答道。
“我问你,你是死者的妻子吗?”
“什么子?”
“妻子,老婆。”
“我是艾宏阳的家属。”
此后水枝像是记起谁的叮嘱,对对方的话均应以一声“啊”。“今天天气这是怎么了”当小马做如是感慨时,她亦瞌睡似地应声,因此前者自觉作为正常人被一个傻子给糊弄了。他伸出指头在她眼前晃。指头移到她左眼时,她向左看。移到她右眼时,她向右看。村委会主任瞅见,觅到用兵之地,跑来。于是,民政所的小马照本宣科一句,他便大声解释一遍(“就是——”“意思就是——”),仿佛她聋聩了一般。如此,水枝听懂啦,她说:
“连七都没做呢。”
“什么没做?”
“就是农村做七,人死后七日才晓得自家死了。”村委会主任说。
“我知道,不用做啦。”小马说。
“那我就做不了主。”水枝说。
“谁做得了主?”小马问。
“队长,”沉吟了一忽儿,水枝又说:“房头上的。”
因此,工作队看见艾湾几乎所有男丁都出现在自家门前,或双手扶锄,或扛着铁锹、枪担,或背着犁轭,或对着青石磨刀霍霍,或将劈到柴内的斧头拔出来,就像马上要去干什么活儿。他们瞧着这边就像刚刚发现这边开来了车队。对工作队来说,这种瞧只是顺带着瞧瞧捎着瞧瞧;对那刚分割给他们每户一万元遗产的孀妇而言,他们又像是专门瞧过来的,是在声讨、抗议与示威。他们有办法将暧昧的事处理得双方都无话可说。只有他们的孩子,完全凭着欣喜,在车与车间来回奔跑,摸这摸那的,并不吝于高声赞唱每一台车。间或,会听见不知是谁,想必是看见工作队内有自己认识的,喊上:“××,你威风啊。”或者:“有本事和隔壁县的人干去在这里是逞什么能呢。”
“你妈屄的说谁呢。”只见穿着迷彩服的临时工黎军,燕颌虎须,豹头环眼,拖着红色的消防长斧,任谁也劝阻不下,走到村前。“甭说打隔壁县的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他说。村庄一时鸦鹊无声,惟青山在回响其突兀的喊叫。好些艾湾子弟因此气得咬牙切齿,浑身战栗,然而就是无法从巨浪翻滚、浩浩然响若奔雷的沉默中走出来。他们试过几次(站出来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啊),就是站不出来。直到黎军拖着斧头回去了。水枝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众人因此都觉得欠了她以及这世界什么,心下都添了不过是苟活的耻辱。
这会儿,死者堂弟宏彬还在痛苦地与自己雄辩。他坐在阴凉的石块上,眉头紧锁,右手的手背托着腮部,弓着背,膝盖弯曲稍微往上顶,整个人就像沉浸于湖水那样沉浸于痛苦而迫在眉睫的思考中。工作队开着十三台车,鸣笛,自村西缓缓驶入,摆明是要来端平宏阳的坟茔的,宏彬迹近痴呆,起身提走凳子,让开马路。后来又在思考中忘记将凳子放在哪儿。如果我还算是宏阳的兄弟,我就应该出面制止这帮言而无信的官员,可他判决我不是,那么多人瞅见了的,他说我不是——虽说他喝醉了;可真要是不是,那么我就又是在推卸责任,一个人怎么能跟醉汉计较呢。怎么能和一个烂醉如泥的人计较呢,这太荒谬了。可他妈酒醉心自明啊!啊!啊啊!宏阳,你妈屄的就像一只穿行在一大群白色的绵羊中间的毛蓬蓬的公羊,公开侮辱我,你不把我当人,你妈了个屄的。有阵子,宏彬甚至想穿越沉默对峙的双方所留下的空地,走过去搂住谁,极为抒情地告诉对方一个自己通过苦苦思索刚发现的真理:这世界竟无忠诚可言。他感觉忠诚那东西就像是即将塌方的山坡,在心里松动得厉害。将之领出思考的泥沼地的是他两个儿子中的一个。“爹,以后我们都没坟了。”后者说。他犹如醍醐灌顶,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所在,走向敌军阵中。在途中,他好像回到宏阳生前的现实:那位他和宏阳共同的朋友,时常在一起聚饮的人,政府的显要,何东明,正背着手站在那儿。
“东明,东明。”他恬不知耻地喊道。
何东明转过身,看着这智力低下却是万事都要想明白才会行动的人走来。那些试图好好表现以博得领导关注的年轻公务员阻拦住宏彬。宏彬开始费力地解释:“我跟东明怎么不认识呢,认识多年。”何东明想及自己与他,以及宏阳,十余年来打了引号的交情,想到他们对自己的信慕,觉得就这么将关系撕裂了有点可惜。
我是替他们可惜,何东明想,尔后朝他喊:“你谁啊。”
宏彬这个人就像被冰瞬间冻住。他的四肢只是略作挣扎,便僵死不动。他眼中的火光在一截截很分明地熄灭。何东明重新转过身去,将他留给底下人收拾。绝交真的是件痛快的事呀,何东明想。他自打进入艾湾后就有的空洞感,至此才似乎稍稍填满。“我是谁,我是老百姓,是人民。”不久,从他身后传来宏彬愤怒的喊叫。他听见宏彬不顾阻拦,就像是游泳一样苦苦朝自己游来。“我是老百姓。”宏彬重复道。仿佛是要跟他自己再明确一次这新的身份,以及它肩负的义务与责任。然后这位乡下男人开始他幼稚的申辩,有时他会像童稚一般发出可笑的恐吓与威胁,有时则残存着自己仍然是副镇长朋友的幻觉。敢问(他使用了这一以卑触尊的词汇)、请问、退一万步讲……,从宏彬嘴里冒出这些他并不熟悉的外交辞令,就像它们很硬气一样。何东明想起还在做纨绔子弟的时光,和哥们儿光着膀子(刺青后被洗掉),整日混迹于县工人文化宫及对面文化馆的舞厅、游戏厅、台球厅,百无聊赖,又舍不得丢弃这种自由的生活。某日,在“今昼我该干些什么”的催问下,他们归纳整理出所有能呛死活人的话语。今天他水来土掩兵到将迎(有时对方尚未说完他便已回击过去),用的正是当年的储备:合着、不敢、不敢当、是吗、对不起、你以为呢、哟、得、您说呢、您可真好玩儿、不忙、您瞧着办、哟嗬、已然、嘿、再见吧、像你这样的、你会干点啥啊、叫我说你什么好、瞧你那样。
其中光“敢情”一词,他就用出三个意思:
(1)表示发现先前没有发现的情况;
(2)当然,表示求之不得;
(3)表示情理明显,结局有必然性,不用怀疑。
当这些只有诗人才能说出口的刻薄的、讥讽的、挖苦的、揶揄的话语从自己嘴中顺顺当当不带一丝磕绊地说出来时,何东明还是为自己的阴毒及下流狠狠吃了一惊。就像这张嘴被什么附了体。那些底下的,像看着耍弄神奇法术的江湖艺人一般,惊诧地看着他。他们想到中学的年轻老师,总是将要惩罚的学生叫到教室外,收起拇指,并拢剩余四指,用腕力去扇学生的脸。规模小而精致。内藏着狠劲,以及对对方的恣意玩弄。何副镇长精心准备的伤人的话亦如此。宏彬溃败得不成样子,往往只会重复某句自以为有理的话。这说明在迫逼之下他的脑子已无法转动(如旧小说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最终停止争辩时,他噙满泪,望了眼何东明。在他黑乎乎的鼻洞当中,鼻毛像枪支交叉挺立,挂着淡绿色闪闪发光的鼻水。搞得何东明很不好意思。何很想走过去,拍拍对方肩膀,说一切都是闹着玩的。对神样的何东明来说,这并无难度。后来,那由村干部升上来的水管站站长,认识宏彬的,跟着宏彬走了几步,打给宏彬一支烟,搂着肩膀说了几句,宏彬便好像想通了。宏彬说:“早这样就好了,你早这样说就好了。”
掘坟时,村委会主任搬来靠背椅,让何副镇长坐在墈下的稻田里。后者早早旋开嗅盐瓶,嗅了一把,然后跷起二郎腿,专心瞧着上边:他们正高举锄头挖掘坟丘,每当锄刃挖进土内,他们就用力扒拉一下。不一会儿,锄柄松动,他们蹲下去用石头敲打插在圆銎内的楔子。他们埋怨着是谁将坟土拍打得这么结实简直比石头还硬。民政所雇佣的两名工人抬着褐色的担架,认真地守在一旁。
“自古,越是强人死得越奇形怪状,有的死于狂笑,有的死于蚊蚋叮咬,有的被自己撩向空中的擂鼓翁金锤砸死,宏阳死于忽冷忽热。”村党支部书记过来搭讪。
“是呀,谁死都一样。”何东明说。
“是啊。”书记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像宏阳这么大的个子,烧起来得费多少柴啊。为防尸体爆炸,火葬场是不是还得对着他连戳十几刀,戳得到处是洞?”
显赫的老政法委书记的儿子、神样的何东明没有接话。此时村民已围到马路上,黑压压的,甚至包括附近村庄如港北、文府、多石的燕窝周的村民。随着时光暗沉下去,人的视线受阻,这些在精神上重归阳痿的人们沿着田埂走过来,有的甚至走到何副镇长前头。派出所教导员像赶鸭一般,哦啰,哦啰,将他们赶到他认为合适的分界线外。“再不许越雷池半步”教导员说。虽如此,在教导员转身后,他们还是集体朝前偷挪了几步。移时之间,传来看见棺木的消息。有人在清理压在棺材板上的石头,一块块地往外扔。因为钉子钉得太深,根本没办法撬开,民政所所长决定直接劈开。因此有人一连下了十几斧,那薄薄的棺材便全部裂开。“哦,天哪!天哪!”这时只见劈棺材的人扔掉斧头,跳向一边。那原本围观的众人,像是密集的蜜蜂,轰然惊散,又几乎同时聚集回去。就像被什么深深吸引住,他们贪婪地看着棺内。擅长呐喊的刘淘淘,一直跟流子混的那名十七岁临时工,定睛看了几眼,朝山下跑,并几乎是飞着从墈上飞下来。有翼飞翔的话语迅速传到村民耳中并导致后者炸开锅。他们明知不该看,看过一定终生不得安宁,然而还是争先恐后地跑过去。有人因此摔倒,险乎被踩死。他们在墈上互相推搡,挤来挤去,将地面碾得不成样子。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将会看见什么,但在亲见时,那惊愕的成色准保不会减掉半点。
“啊,可怕!可怕!可怕!不可言喻、不可想象的恐怖!”刘淘淘仍在奔跑。
“什么事?”那些相向而行的人焦急地问。
“不要向我追问,你们自己去看了再说。”
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以后,有大员下村时会问:“你们都看见了什么,且说来听听。”
甲说:“我看见他血管爆出表皮。”
乙说:“我看见他眼球滚出眼眶。”
丙说:“我看见他鼻孔张如隧道。”
丁说:“我看见他全身紧紧绷住。”
戊说:“我看见他脊背磨掉外皮。”
己说:“我看见他十指曝露白骨。”
庚说:“我看见他额头顶得血肿。”
辛说:“我看见他口腔吃满石灰。”
壬说:“我看见他上肢右肢折断。”
癸说:“我看见他下肢左肢扭曲。”
子说:“我看见棺材内四处是血。”
丑说:“那都是他抓出来的血啊。”
寅说:“我看见银发簪卷如刨花。”
卯说:“我看见铁胸针插进掌心。”
辰说:“我看见他就像被雷劈死。”
巳说:“我看见他死于某个瞬间。”
午说:“我看见他焦躁到了顶峰。”
未说:“我看见他绝望到了极点。”
申说:“我看见他在拍打向棺木。”
酉说:“一边捶打一边疯狂呼喊。”
戌说:“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在吗。”
亥说:“我看见他在捶打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