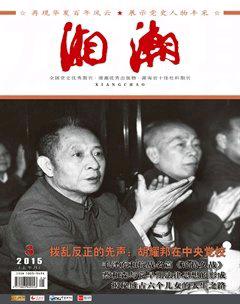中俄关系:大道无遮拦
李景贤
回望已渐渐远去的半个多世纪峥嵘岁月,感到中俄关系既绽放过绚丽的夏花,也经历了难熬的冬夜。可幸的是,两国人民最终走出一片新天地。如今忆及这一事件,我作为那段不平凡历史的见证人,在脑海中不由得生出:大道无遮拦。
伟大的友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这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对此,斯大林是高兴的。次日,中苏两国便建立了外交关系。
12月16日,在新中国成立后第77天,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身份,乘坐斯大林特意派来的列车,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终于实现了期盼已久的访苏愿望。毛泽东说,这次是为斯大林祝寿而来的。他带去装满3节火车皮的寿礼,计有山东大白菜、大鸭梨等蔬果,还有一些工艺品。21日,毛泽东参加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斯大林七十大寿庆祝会,被安排坐在寿星的右侧。会后,这两位中苏最高领导人在大剧院观看了文艺演出。演出结束后,大批观众涌向他们所坐的中央包厢两旁,长时间高呼“斯大林”“毛泽东”!
其实,毛泽东此访另有一番用意,但一直藏而不露,只说希望搞点“又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对这6个字的含义,斯大林一直琢磨不透,感到毛泽东城府很深,自然也就不会露出其真意,便将他“晾”在自己的郊外别墅里。对此,有史家称,“斯毛上演一出新版《三岔口》”。曾任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赌气地天天在别墅里睡大觉。”西方媒体遂发消息称:毛泽东到莫斯科都10多天了,一直毫无动静,因为“遭斯大林软禁”。于是,斯大林便请毛泽东向塔斯社发表谈话辟谣。毛泽东在谈话中,宣布他这次来苏联的主要目的,是同斯大林商签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次日,苏共第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受斯大林之遣,到别墅看望毛泽东,并郑重表示:“斯大林同志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中苏双方可签订新的同盟条约。”从随访的汪东兴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一天“主席的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到达莫斯科,与苏方商谈签约之事。他们两人一起,或者各自,与斯大林多次就中苏同盟条约的内容交换意见,一开始以苏方草案为基础,后来改以周恩来草拟的文本为基础相谈。2月14日,周恩来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还签订了苏联援华的一系列协定。这便是毛泽东要得到的“既好看,又好吃”的两样东西。斯大林同样得到了两样期盼已久的东西:一是在俄东部抵御美日威胁宽大无比的缓冲地带;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号战略盟友。
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的远东战略格局。而条约的签订,使中苏两国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下来,这对20世纪后半期世界格局的变化,无疑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一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中苏两大统帅——毛泽东、斯大林,对于战争形势的分析及其走向,对于重大战事的决策,对于朝鲜和谈的时机及方针、对策把握,一直通过多种方式,及时进行沟通,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对于前方总指挥提出的战术建议,只要毛泽东不提出异议,斯大林都表示赞同,双方保持着高度默契。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朝鲜领导人发生重大分歧时,对于毛泽东有利于彭德怀的裁决,斯大林都表示支持,并称赞彭德怀说:“真理在彭德怀一边,彭德怀是当代的军事家。”
朝鲜停战和谈,毛泽东和斯大林也一直紧密沟通。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决定“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不久后,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提出朝战各方“立即停火”的建议。毛泽东甚至致电斯大林,建议他“亲自领导”朝鲜停战谈判。对此,斯大林虽没应允,但从中苏间频繁来往的密电中可以看出,从谈判方针到步骤、谈法,都是中苏两位统帅共同决定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斯大林及时地向我国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中苏双方很快就开始执行我国恢复国民经济所急需的47个项目。
苏联援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离开莫斯科赴任前,斯大林对他满怀深情地说:“您这次去中国,要把全部知识和技能都告诉中国同志们,直到他们全都学会为止。”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专家们一直给予高度的信任。阿尔希波夫常被邀请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当斯大林得知后便对他说:“您以后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了,因为这样做,会使中国同志们感到难堪的,一个受外来压迫多年的民族,对这类事情是很敏感的。”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极为重视发展中苏友谊。为了援助中国,斯大林不惜修改了苏共十九大所通过的五年计划大纲。有一年,苏方企业供货严重拖欠,斯大林得知后立即撤了10多名部级领导干部的职。有一段时间,苏联缺乏硬通货,毛泽东便指示从并不宽裕的侨汇中,拨出一两亿美元来支付苏方贷款,让斯大林颇为感动。
关系的破裂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病逝于莫斯科,事先并没有留下什么政治遗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内务部长贝利亚和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这“三驾马车”,联合执政了很短一段时间。不久后,贝利亚就被从肉体上消灭掉,马林科夫则被下放到遥远的边疆。9月,赫鲁晓夫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入主克里姆林宫。
1954年至1957年,即赫鲁晓夫执政前期,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做了不少示好的事:
一、纠正了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一些不平等做法,比如放弃了苏联在中国东北、西北的特权,把旅顺、大连两大不冻港以及中长铁路的管理使用权交还给中国。
二、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156个援华项目中,斯大林时期占了47个,其余则是赫鲁晓夫执政时实施的。后一个时期的苏联援助量更大,面更宽,其中包括在核研究方面。在黄迪菲的回忆中,有个片断就相当感人。1957年12月20日,当P2型导弹及器材用10节火车皮运到边境的满洲里站时,往迎的彭德怀解开系在导弹上的红绸带,深情地对在场的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现在把他托付给你们啦,你们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
三、重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地位与作用,遇到大事时,与他商量,比如在苏共二十大后发生的“波匈事件”中,听从毛泽东的劝告:对波兰事件,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出兵镇压;对匈牙利事件,则以敌我矛盾处理,不惜动用武力。赫鲁晓夫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列入苏联高等院校的哲学必修教材。
1957年11月,在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向毛泽东频频示好,甚至提议国际共运由中苏两党“共管”,社会主义阵营以苏中两家“为首”,即他本人管西(欧美),毛泽东管东(亚洲)。
赫鲁晓夫做出以上种种举动,自有其内在需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根基尚浅的他,自然得倚重在国际共运中声誉和分量日益变高、变重的毛泽东。为此,他必须拿出一些硬梆梆的“真家伙”,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与支持。
等到赫鲁晓夫自感羽翼渐丰,就开始变脸,声称“要走自己的路”。他骨子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暴露出来,要把中国牢牢拴在苏联的“战车”上。
1958年春夏,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等人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两国建立“联合舰队”,在华设立“长波电台”。这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认为赫鲁晓夫“旧病(指斯大林企图控制中共之‘病)复发”。7月31日,赫鲁晓夫抵京密访,亲自向毛泽东提出要搞“联合舰队”“长波电台”,未达目的。
1960年2月4日,在赫鲁晓夫主导下,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宴会上,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说有人主张以苏联为首是假的,此人对人民不负责任、好战,影射攻击毛泽东是双没用的“老套鞋”。4月,借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我党连续发表3篇文章,名为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则间接回敬赫鲁晓夫的相关言论。5月22日,毛泽东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称赫鲁晓夫为“半修正主义”。
中苏两党矛盾公开化发生在1960年夏天。当时,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会上,赫鲁晓夫动员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围攻中共代表团,对中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攻击。对此,与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进行了有力反驳,谴责赫鲁晓夫的“老子党行为”。
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伍修权率中共代表团与会,与赫鲁晓夫等苏共大员进行了斗争。评述赫鲁晓夫所导演的东欧4个党代表大会反华闹剧时,我国一报纸曾写出这么一句辛辣的话:“伍泰然”四闯“恶虎村”。
1963年、1964年,中苏两党进行了“真假马列”大论战。我党发表了9篇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大文章,简称“九评”。苏共则发表致全体党员公开信等文件,批判中共的内外政策。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被解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毛泽东期望苏共新领导能改弦更张,派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周恩来与勃列日涅夫多次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苏共第四号人物米高扬插话声称:苏共新领导的对华政策,与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差别”。不过,苏联总理柯西金私下对周恩来说:没有差别呀,这是不可能的。中苏关系继续处于紧张状态。
“文革”爆发后,中苏关系迅速恶化。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东段的珍宝岛,两国军队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两国政府频频发表谴责对方的声明。在我国政府声明中,给勃列日涅夫扣上一顶“新沙皇”的大帽子。
9月11日,根据苏方提议,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举行会晤,就缓和中苏边界紧张局势达成了多项谅解,使两国关系严重恶化的势头得以扭转。不久后,两国恢复中断达五六年之久的边界谈判。
尽管如此,两国关系跌入低谷,双方只保留着两馆(各自驻在对方的大使馆)、三线(各自飞、开往对方首都的每周一个航班、一次列车、一条政府“热线”)和少得可怜的贸易(每年总共才2000多万瑞士法郎),这种状态一直维持了十几年。
关键性转折
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感到,中苏关系再如此恶化下去,只能更严重损害本国的根本利益,便设法寻找转圜的机会。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公开发表讲话,发出要改善苏中关系的信号。邓小平立即抓住这一示好的信息,并迅速作出相当正面的回应。过后不久,双方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副外长级的政府特使政治磋商。
俗话说,世事难料。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猝然去世。邓小平再次以此为契机,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14日上午9时许,黄华乘坐的班机起飞后不久,邓小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让这位特使在首都机场发表个书面谈话,以便把几句要紧的话,说给苏共新领导听一听。但身边的人告诉他,本来要坐专机赴苏的黄华,为了节省费用,改坐班机去,飞机已经起飞了。于是,邓小平便请当时正好在身边的“大秀才”胡乔木按照他口授的内容,草拟出黄华特使的书面谈话(以下简称“谈话”)。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很快就收到了国内发来的“谈话”,打印出来后一看,也就一页A4纸的篇幅。我当时在使馆任二等秘书,被指定当黄华特使的联络员。我细细地品读了好几遍“谈话”稿,感到文章虽短,但暗藏深意,话里有话,这些话只有巧用战略思维的大人物才能说得出来。
“谈话”有3个妙笔:
一个妙笔是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说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这些提法令人耳目一新,与中方多年来狠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做法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这是邓小平一个“大手笔”,借悼念逝者之机,着眼于苏联老百姓,意在做苏共新领导的工作。
另一个妙笔是,文内有这样的提法: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有意安下的一个“软钉子”,暗示正好在这一时期执政的勃列日涅夫,应对两国关系的“严重”“恶化”承担自己那份责任。这句话绵里藏针,巧妙地体现出邓小平关于对勃列日涅夫“不能光说好话”这一指示精神。
还有一个妙笔是,“谈话”末了有这样一句话:“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这里边一个“总书记”,一个“党政当局”,相当耐人寻味,暗含着对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新公开承认。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与苏共就开始相互进行大批判,而且越批火力越猛,一批就是一二十年,毛泽东一再怒斥苏共“变修”。邓小平这位当年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面对面进行大论战的主角,现在把笔锋一转,大概是想让苏共新领导听出一点弦外之音。
邓小平的对苏葬礼外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成了中苏关系的一大转折点。
1982年10月5日,中苏关系正常化政治磋商开始举行。由于双方立场差异太大,加之以当时苏联国运不昌,由病夫治国,不到3年就连损3帅,其高层自然也就无暇顾及与中国谈判,这一磋商便成了“聋子对话”。
1985年春,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连连发出要改善中苏关系的信号。邓小平借机从多方面推动戈尔巴夫乔做些实事。
1988年底,中苏关系正常化水到渠成,戈尔巴乔夫定于次年5月中旬访华,与邓小平举行高级会见。双方商定,中苏外长此前进行互访,为高级会晤作准备。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定于1989年5月16日10时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9时10分至20分,李先念、姚依林等领导人陆续来到了东大厅。9时35分,邓小平在女儿萧榕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邓小平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中苏双方都理性分析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诚恳承担各自应负的责任,深刻吸取个中教训,这是一笔无形的巨大政治财富,为日后双边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991年12月26日,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停止存在”。次日,俄罗斯联邦接替其在联合国的席位。29日,中苏关系被中俄关系所继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俄关系得到了异常迅速的发展。在短短3年多时间内,由于双方领导人共同努力,中俄关系实现了一个“三级跳”:从一般国家关系发展到友国关系——建设性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尽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长期奉行“偏西(欧美)政策”,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还是十分看重中俄关系。根据他的提议,两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辟国与国之间战略伙伴关系之先河。
20世纪最后一天,叶利钦总统经过大半年反复思考、权衡后,明智地宣布提前让位给总理普京,这预示着俄罗斯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有史家称这一天为“普京大帝元年的开启”。普京2000年春当上俄罗斯总统后,中俄关系更上一层楼,发展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目前则处于一个新的阶段,“驶入一条可以疾驰的快车道”。中国高铁开进莫斯科——这是中国总理李克强2014年10月访俄期间,我国民间创造出的一个含义颇深的形象化说法,它“称”出中俄务实合作新规模的巨无霸级重量。稍后,普京对中国记者说:“在二战期间,苏联和中国是两大盟国,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兄弟般友谊,为当代俄中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俄两国决定2015年共同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70周年,这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中俄双方签订的文件和两国领导人发表的言论看,中俄关系可具体拆解为六大合作关系:真诚互信的政治合作关系、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关系、共同创新的科技合作关系、和谐友好的人文合作关系、团结互助的安全合作关系、相互配合的国际合作关系。中俄战略合作不是昔日那种共同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各自捍卫本国根本利益的自然诉求与体现。在当前形势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大业的意义更为重大,成为两国各自抵御重大政治风险的强有力屏障。
2014年11月9日,普京来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峰会。当日晚,习近平会见他时高兴地说:“今年以来,我们加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领引,密切地沟通接触,精心栽培了中俄合作的常青树。”这是习近平任中国国家主席两年来第10次与普京会面。双方签订了17项务实合作协定。对此,有媒体评称:“习普会”1年平均5次,破了中俄领导人以前会见密度的纪录,而两人这次会见,则奏响了中俄合作的“亚太新曲”。
苏联解体后23年多,特别是普京主政俄罗斯以来的实践证明,中俄关系成为邻国间、大国间相互信任、和谐共处、尊重和支持对方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合作共赢的典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国与国关系中,中俄关系是一对“含金量”最高,最为“实打实”的双边关系。
65年多,弹指一挥间。回望中俄关系从“花开花落”到“花谢花茂”,我想起“大道无遮拦”这一禅语,似乎忽然悟到其真谛。中俄睦邻友好合作乃大道也!这是一条不怕遮拦,也不可遮拦的大道!在中苏关系中,曾出现过不少严重障碍,但并没能阻拦中苏人民沿其前行。我们坚信,中俄两国人民也必将世世代代,沿着这条大道越行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