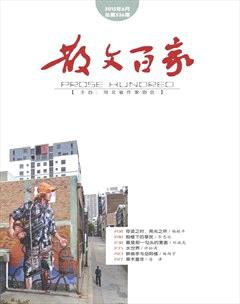雾灵山的眼睛
●戴建志
说燕山山脉是北方的巨峦大嶂,不如说是来自天边的一排翻卷的浪,而雾灵山是被截取的诸多高峰中的一个“定格”,两千多米的高度足以展示一幅壮丽的画卷。我第一次登雾灵山,对它的理解还停留在山高柏森而“雾”上,尤其是顺着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拾级而上的时候,自然就想到了古人“清泉石上流”、“客洗心流水”的诗句。前挂瀑布,驻足观看,就想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然而,再攀雾灵山,我就觉到了这游观之所的“灵”的一面。明代学者顾炎武晚年曾考察雾灵山,在《昌平山水记》卷下记载:“其山高峻,有云雾蒙其上,四时不绝,上多奇花,又名万花台。山之左右,峰峦拱列,深松茂柏,内地之民多取材焉。”深入岩峰与绿色,我看见了雾灵山的目光。
溶洞中的地之眼
在山的半山腰,陶家台村村民一直很纳闷:有一个獾子洞,冬暖夏凉,常年有雾气冒出。于是,他们自筹经费,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在2003年3月的一天,他们在挖挖停停中发现了高大的、带着各种颜色的石笋。为此,他们欣喜得流下泪来。这是一个大型石灰岩溶洞,发育年龄达十几亿年,是我国最古老的溶洞之一。
这个溶洞现在还在生长期,一进洞里,空气清冽,水滴还噼噼啪啪地从上面掉下来。在地面浅浅的水中站立着两三只玻璃杯,里面的水清澈冰凉,听讲解员说,这是研究人员用来分析滴水中矿物质的。
溶洞内被洇湿的钟乳石千姿百态、晶莹剔透,恍若仙境:吊球、玉珊瑚、双色瀑、石剑、竖镜、飞碟、煎蛋、石笔等,特别是垂挂的鹅管群,因形态像鹅的羽毛管而得名。很多景观是国家级的,甚至在世界上也属罕见。大自然从容地变迁,把一个时间的故事演绎得“绘形绘色”。
灯光下,是一个清透的、冷美人的世界。她们梳妆起来总是耐心地、潜移默化地塑造,在不经意中完成自我。我小心翼翼地用目光触摸她们的肌体,捕捉真水无香的经验。她们多姿多态,仅仅是一个视角的变换,就能给你一个美丽的惊喜。
最让人展开想象的是那个叫“地眼石睛”的景观,英文是“Eyetoeye”。据说,这属于国家级景观。它起初是一个圆头石笋,后来从上面不断地滴下水珠,在笋的头部渐渐地冲击砸成一个洞穴。当其他的滴水积水在石笋周围形成一个小水池后,虽然石笋被淹没,但那个洞穴却保留着,而且穴中有穴,从上面看上去像一只极为生动的圆眼睛,还有清晰的瞳仁,灵动有神韵。它警惕地看着从身边走过的人,使你不自觉地要回过头来,再望它一眼。实际上,那个“地眼石睛”总是在向上看,因为穿过厚厚的岩石,地面上也有相同的景观。
人们都说,地下溶洞的千姿百态,是地面景色的缩影。如果你仔细寻找它们是可以对应的。就是,地面上有的山和石,溶洞里也有;溶洞里有的潭和瀑,地面上也有。这需要你认真观察,更何况地下溶洞有很多尚未开发,有些景观你不得而见。
仙人塔,高48米,说它似塔,一是因为有个狭瘦的身材,拔地而起;二是裸露在外面的岩石非常清晰,一层一层的,好像是垒起来似的。所以,我说它仙风道骨。“仙”在哪里?听说它经历过多次地震,仍然没有倒塌,那就仙在长生不老吧。“道”在哪里?它像一把巫师手里的利剑,念念有词、斩风劈雨;尤其是在淡淡的月光下,它像一个行走深山的巨人,踏水扣石,森然欲搏。更奇怪的是,它与相隔不远的溶洞里的那把石剑有几分相像。我想,仙人身上岩石嶙峋,是从地下钻到地面时留下的痕迹,尤其是方圆几公里处有许许多多的潭和瀑,是仙人身上落下的水积聚而成的,如卧龙潭、楸潭、阴阳潭、玉水潭、净潭、香杨潭、锦鳞潭、泻潭、映月潭,还有之字瀑、飞环瀑、银龙瀑、八音瀑。不说别的,单就这潭这瀑的名字,就足以说明仙人的来历不凡。在离仙人塔并不很远的东北方向,有一块花岗岩巨石,上书“雾灵山清凉界”,据说有几万吨重。它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狠狠地砸在森林中,周围溅起了绿色,更显出它的独特来。
在仙人塔的西北面,有八座峻峭挺拔的山峰比肩而立,半山腰多被绿色包裹着,只是趋向顶部的地方显出白色的岩石,好一派坚硬、顽强以及敢于担当的气势。兴隆,曾经的抗日战场。日本人为切断抗日武装与百姓联系,毁掉上千个山村,制造出千里“无人区”,至今山上留存着他们放火烧山的痕迹。焦黑的树干,记下了罪行;过火的土地,长出了仇恨。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支队与日军曾在兴隆多次交手。这里要记住的一个人名是李运昌。他出生在李大钊同乡乐亭县胡坨乡木瓜口村,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上过农民运动讲习所。更重要的是,李运昌作为创建以雾灵山区为中心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实践者和领导者身份被载入史册。他先后担任支队司令员、冀东军区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司令,终于将零星根据地发展为颇具规模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20世纪80年代,文革以后,司法行政系统正在恢复重建中,李运昌担任司法部第一副部长。因为我曾在北京市司法局工作,也就是李运昌担任副部长时期,所以,对他在兴隆的抗日事迹就格外关注。我想,只要你肯于凝视,雾灵山能够为我们提供文化破解的“DNA”。
古香杨的树之眼
我去过承德避暑山庄很多次了。那是清代皇家园林,山中有园,园中有山。它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成为清代盛世的见证。有意思的是,就在承德市西南面的兴隆县,也有一片属于皇家的林地,叫“后龙风水禁地”。兴隆县距遵化的清东陵几十公里。乾隆皇帝时期,将皇陵禁地向东北扩大到雾灵山地区。中国的风水理论讲究“前有照后有靠”,就是皇陵前面要有水、后面要靠着山,这样才牢固。这就是说,雾灵山是皇陵的最大的“后靠”。作为上百年的后龙风水禁地,雾灵山地区自然是松荫遮天、荒草铺地,而且那时是“鸟禽蔽日,走兽成群,自生自灭,无人取用”的。
置身于绿色之中,清风骤至,气爽撩人。山杨林、油松林、桦木林……虽然都不是太粗壮的树,但都是成片的、挺拔的,有如立柱,努力地支撑起一片蓝天。仰头观望,阳光从高高的、密密的树叶缝隙中洒下,使林间充满了五颜六色。有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古香杨树,藏在道旁的丛林中。它有三百多年,上端的叶子还是密密匝匝的,只是那五六个人才能合抱的树干已经空心了。人从裂开之处钻到里面,仰头望去,可以看到远远的上方有一个明亮的小孔,这就是雾灵山风景区著名的“树里观天”一景。人们从这里经过,总是要体会一下的。实际上,如果静下心来,坐在树里,用手触摸四周,软软的木质,仍然可以感觉到生命的腹部;用鼻轻嗅四周,淡淡的木香,霎时能够感受到生长的气息。树屋,拥坐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忽然,我心里一惊,顺着树干往上看,那远远的亮光,分明是一只向下看的丹凤眼。不知怎地我就想到《诗经》中“硕人”的句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树是有灵性的。清露芳尘,留在年轮中、藏在木纹里,记录着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经长年累月,地上的枯草、落松、萎叶积得厚厚的,成了大地的保温层;树根躲在隐秘深处伸向四方,紧密相连,亲上加亲。我走在蓊蓊郁郁的树林里,脚底软软的,倍加小心。我能感觉到它们在默默地注视着你;走入越深,越感觉全身心有一种交流的渴望。寂静中,能听到草叶正因你踩到它伸出的手而喃喃嗔怪;风拂过,能断定树林正因你的到来而交头接耳。
在城市里不知什么时候空气变得叫人这样挂心。木香弥漫,深深地吸一口,沁人肺腑,可以唤醒体内已经被浊气闹得焦头烂额的细胞。据说,落叶松能释放杀菌素,能强健人的呼吸系统。在清凉界、仙人塔那里,我见到大片的落叶松。我想,大自然为我们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观察植物的生长样态,是观察生命的一种方式。你看,植物似乎并不计较空间,一个小小的花盆,可以挽住春色,可以孕育果实。但是,植物却是在意地点的:哪里藏储丰富的生长养分,她们就在哪里展现生命。美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奥罗姆认为:现代城市太偏爱“空间”,而对“地点”却太漠视。地点担负着“定义我们生存状态”的使命。现实中,我们太关注自己的居住面积,却把活动地点放在次要地位。空间并不能使我们躁动的情绪变为稳定,而绿色的环境、美丽的花朵,却让我们赏心悦目、恬静超然、气舒情畅。我们需要高楼大厦的记忆,也需要亲近草木葱葱的经验。大厦是文明的投影,草木是生命的脉络。
观测站的天之眼
星芒灿烂,草木葳蕤。地上有一种植物,天上就有一颗星与之对应。天上的星星影响和引导着植物生长,并在暗中照亮植物。这是一个英国人的看法。无独有偶,德国有个艺术家说:“从凡·高开始,向日葵就已成为一个神话般的主题了,但你不能就把它的意义停止在那里。当我看到那成熟的、长满黑籽的葵盘重重地弯向地面的时候,我便看到天宇和星辰。”看来,寻找植物和星宿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的思维惯性。
雾灵山天文宁静度好、大气透明度高,非常适宜天文观察,所以,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获得国际观测编号,由此取得的天文数据为许多国家采用。我在天文观测站的展览室墙上看到著名的星云照片。这要感谢在雾灵山闪烁着的大眼睛,是它揭开了天空的神秘,并把一幅又一幅美丽的天景贴在我们的记忆上。天文圆顶是天文观测的标志性建筑,它像一只凸着的眼球,瞪着天空,好像在跟谁较劲似的,突然感觉挺滑稽的。在兴隆观测站山上,这样的大眼睛有好几只。每到观测的夜晚,圆顶天窗打开,它们就像揣着好奇心的孩子,捕捉观察辽阔太空中的任何一个异常。
飘渺浩瀚的宇宙。“上帝之眼”,说的是一个螺旋状星云。恒星的外一圈是红色光芒,然后向里渐渐呈黄色,核心部位是夹带诡异的蓝色,那就是“瞳孔”了。从拍照下来的片子看,真像一只大眼睛,美丽而有神。螺旋星系是距离地球最近的行星状星云之一,即使这样,它距离地球约700光年(1光年可能是九万多亿公里吧,反正距离特大),光直径大约就是5.7光年。这个天之眼,是1824年被德国天文学家卡尔·路德维希·哈丁发现的。就是说,在这之前,这个神秘的大眼一直默默地关注着地球。我想,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笼罩在上帝爱抚的目光中,可是我们不一定能够读懂上帝的眼神。每至此,我往往情不自禁地把普通的生命当作神圣的生命来阐释。
“上帝”是一个精神符号,其内涵丰富,以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我对上帝的理解,时而是模糊的,时而是清晰的:模糊的是令我神往的奥秘和推动我无边想象的冲动;清晰的就是它一直在那里,来自遥远的,却分明在注视着的目光。“人在干,天在看”。在确立志向的时期,在做事历情的阶段,我能感觉到这个目光,尤其涉世已久,我更懂得上帝的目光可以使人有理性和意志的品性。星空的纯洁,让人想到道德的高尚;道德的高尚,让人想到星空的纯洁。康德的那段名言是有在场感的。
实际上,在古代中国,人们就看到了天之眼。唐朝韩愈有诗云:“念此日月者,为天之眼睛。”尤其是夜晚,月亮当空,最容易牵出人的思绪,唤起人的想象。宋朝苏轼在中秋节望月,就想到了“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遂令冷看世间人,照我湛然心不起”。经过银河的洗濯,天眸更加明亮清冷。在如此目光下,人的内心杂念无处躲藏。上帝、天公,是东西方文化对天之眼的一种认识,其中共同点就是想象在人类之外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LAMOST”是“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仪”的英文简称,也叫“郭守敬望远镜”,是兴隆观测站里重要的天文仪器,也是世界上排在前列的光谱获取率最高的望远镜。从远处看,这个天文望远镜像一座被高高架起来的横卧于南北方向的超大型的炮,其炮筒高抬可能是5°左右,距离炮管低的一面大约两米外有一座六层楼高的圆顶的“炮座”。起初,我想象那就是一架大型望远镜,人们从这一头镜面看到那一头镜中的天上画面(技术人员曾笑着对我说,那个样子是在作秀,不能跟这个比的)。然而,待我进入炮座后,全是另外一种景观,巨大的镜面下连接着密密麻麻的线路。从天文圆顶洒下的夜空光源投射到庞大的天文望远镜的镜面上,再由它折射到朝天的炮口的镜子上,以后又折射回来到另一个镜面,最终成像。我想,大自然帮助我们形成科学的思想。人们通过观天,辨别这样和那样的星云,认识我们的太阳系与银河的关系。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却知道了别的星球有太多的荒凉,由此一次次燃起对现实绿色家园的炽爱和珍惜之情。
由此想到人之眼
我想,大自然给我们生活启示。地之眼、树之眼、天之眼,更多的是人们因其外形的酷似而赋予自然有着人一样的眼睛。无论是天之眼还是地之眼,抑或树之眼、人之眼,都有这样的功能:你看它,它也在看你;你望它,它也在望你。比如,当人们肆意地掠夺、践踏大自然的时候,它们会以风、雷、闪电、地震的形式发出警语。所以,我们要努力读懂它们深邃的眼神。即便如此,我敢断定谁也不能宣称已经读懂了其中大多数的秘密。
学者庞朴曾说,中国文化体系的密码是“三”。天地人之美,不在于天是天、地是地、人是人,而完全在于天地之间的关系。天是天地是地,但是将天地合在一起,词义就变得广大无边:“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那就是整个大自然,就是整个世界。一旦天地与人合在一起,那就是生活,就是文化,就是哲学。
孔子在《系辞传下》中说:“《易》之为书,广大备矣。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我想,雾灵山就是一部关于哲学的书。易者,变化也。雾灵山是因变化而来,又无时不在变化中。这里有太多的思想元素,可以体会天道、地道,更由此觉悟人道。天之道,在高远;地之道,在博大;人之道,在精神。天的作用在“化”,就是给出条件,使事物产生变化,从无到有;地的作用在“育”,即提供各种物质资源来养育万物;而人的作用则在“赞”,就是帮助天地来化来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