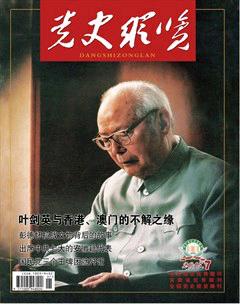袁殊:“与狼共舞”的红色特工(下)
卢荻
周旋于两国四方之间
1937年4月,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日本排华事件不断发生,袁殊决定立即回国。岩井也找到袁殊,希望在日中关系“破裂”后袁殊能继续和日方合作。但袁殊回到上海后,首先去找冯雪峰,汇报了自己在日本的情况,希望党对他今后的工作有所指示。鉴于袁殊的情况特殊而又复杂,冯雪峰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安排为好。当时不少同志都认为袁殊早已是“转向”人物,不能轻信。冯雪峰于是让袁殊先利用旧关系找点事情做起来再说。袁殊只好独自行动,他找到旧帮会的关系,由杜月笙资助他办了一个并不起眼的“时事刊行社”,实际上不过是做了杜月笙门下的一个食客。一贯雄心勃勃、热衷于追逐政治浪潮的袁殊,一时间竟成了一个没有政治立足点的“盲流”,他感到十分彷徨。
不过,没有多久,他就找到把他引上革命道路、引上情报战线的领导人潘汉年。潘汉年1933年离开上海,先到江西中央苏区,其后参加长征,后来辗转于莫斯科、南京、陕北等地。1936年秋后,他以中共代表身份,回到上海,与国民党代表开展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不久,潘汉年担任了中共上海工委主任,抗战爆发后又担任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全面担负起了指导整个上海党的工作。
袁殊向潘汉年汇报了自己近几年的大体经历,恳切地表示希望能够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日尽一份力。为了表示真心和诚意,他将一份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军用地图作为情报资料交给了潘汉年。当时冯雪峰、夏衍仍对袁殊颇具戒心,认为他难以信任。但潘汉年从党的战略与策略高度出发,经过慎重考虑,排除了夏衍等原先表示不宜用袁殊的意见,决定接受袁殊的要求,恢复了与他的联系。与此同时,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急需日军情报,而他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后来,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表示要委以重任。当袁殊将这一情况向潘汉年汇报后,潘汉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从当前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参加军统敌后工作有利于抗日;从长远看,在军统打入一个楔子,以后在情报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潘汉年同意袁殊加入军统工作。于是,袁殊接受了戴笠的任命,一跃而成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少将组长。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双方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使中方避免了很大损失。
上海沦为“孤岛”后,潘汉年撤离上海前往香港,暂时中断了与袁殊的联系。袁殊奉戴笠之命继续留在上海。他不仅大搞情报,而且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组织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头面人物,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炸毁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8年秋天,袁殊被召赴香港参加戴笠召开的军统骨干工作会议。会上,戴笠对潜伏敌后有功人员恩威并举,一面对他们大大奖励一番,并当场送给每人两把最新式的加拿大手枪,一面又以冷峻的口吻警告他们,谁如果对我们的团体不忠,你们也可以拿这个去对付谁。听了戴笠的话,袁殊内心有些惶然,他知道戴笠对他这样非黄埔嫡系的人是不会完全信任的。会议结束前,戴笠还单独接见一次袁殊,亲自向他交代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他回上海后设法将已经投敌充当汉奸特工头目的李士群除掉。
在香港开会期间,袁殊秘密会见了正在香港活动的潘汉年,向潘汇报了自己一年来在上海的工作。潘汉年语重心长地对袁说:“你这次来开会说明戴笠待你不错。现在虽说是国共合作,但本质上两党是对立的。一个人的前途是在关键时刻决定的,向右,你可以跟着戴笠干下去,成为他的红人。但我看你成不了他的红人,军统是清一色的黄埔派。这就要看你自己的决定了。”
袁殊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即按照戴笠的部署,策划暗杀汉奸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的计划。谁知这一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就因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和另一位军统头目陈恭澍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捕获叛变告密而败露。袁殊也因此而逮捕。李士群和袁殊过去就很熟,而且关系不错。但这次袁殊直接指挥暗杀自己,不能不使李士群十分恼怒。在审讯袁殊时,李士群严厉地向袁殊交底说:“要么你就归顺我,和我合作,做我的帮手;要么我就按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指令,将你处以极刑,希望你尽快做出选择。”
在如何处置袁殊问题上,汪伪特务头子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特工头子丁默邨主张杀掉袁殊,而李士群因与袁殊在中统“干社”共过事,知道他是个日本通,认为此人有“可用之处”,主张刀下留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袁殊趁其妻马景星到牢房送换洗衣服之机,暗示她去找潘汉年求助。潘汉年知道袁殊与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有情报关系,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岩井闻讯后,立即带了两个助手来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魔窟,以领事馆名义和以袁殊是外务省系统情报人员为由,向丁默邨和李士群要人,丁、李不敢得罪主子,只得将袁殊放了。
袁殊脱险不久,岩井就要求他尽快写出一篇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发表,要他公开表态。迫于无奈,袁殊便以“严军光”的名义写了一篇《兴亚建国论》,内容大体符合日本人所谓“大东亚共荣”的论调。此文得到了岩井英一以及“梅机关”机关长、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少将的认可,被译成日文在中日多家报刊上公开发表。这样,就把袁殊从幕后推到了前台。
卧底日特岩井公馆,大量获取日本情报

1939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兼华南情报局局长的潘汉年,在组织香港情报工作的同时,又奉命着手加强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他要搜集延安中枢机构急需的有关日伪以及美、英与蒋介石政府关系方面的情报,自然想到了与国民党军统、日本情报部门有联系的袁殊。而袁殊更希望从潘汉年那里获得对今后工作的指示。见面时,袁殊将自己近一年来的情况向潘汉年作了汇报。他说,岩井在领事馆以外的地方弄一座楼房以岩井公馆的名义搞了一个情报摊子开展活动,要他参与此项工作。潘汉年经过认真思考并报请中央批准后,决定让袁殊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他对袁殊说:“你可以答应岩井的要求,将计就计,在敌伪之间建立一个亲日的团体,既可干扰汪伪政权的建立,又可为我党所利用。”
根据潘汉年的指示,袁殊按照岩井要求,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挂起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招牌,成立“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的机构。袁殊担任主任干事和《新中国报》《兴建》杂志社的社长。潘汉年在幕后给袁殊以积极的帮助。他从香港把改组派的旧人,经何香凝、廖承志做工作,表示愿意为抗日做些有益工作的陈孚木弄来担任“兴亚”的主任委员;又从桂林《救亡日报》把袁殊的旧友、中共党员的翁从六调来当《新中国报》经理;将进步记者叶文津派到报社工作;还把从延安来的情报干部刘人寿安插进岩井公馆担任机要工作。“兴亚”本部主要人员均由中共秘密党员充任。所设电台,亦由党员掌握。“兴亚”本部实际上成了中共在敌占区的一个重要情报机关。由于延安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急需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三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袁殊则利用这个机构,通过与敌方首脑人物个别接触、参加宴会、定期出访、阅读文件等多种渠道,搜集到许多很有价值的战略情报,经刘人寿、翁从六,转给潘汉年坐镇的华南情报局本部,然后由潘汉年和张唯一综合整理及时发给延安中央社会部。
为保持与军统的联系,潘汉年还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袁殊在信中说明由于王天木出卖,爆炸76号事败露,被日宪兵司令部判死刑。因岩井出面营救,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并表示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希望继续为抗日做贡献,请戴笠予以谅解。潘汉年请一位与戴笠交情甚笃的人士亲赴重庆,将此信送交。戴笠鉴于蒋日之间的微妙关系和情报工作的需要,遂亲笔回信对袁殊表示理解和安抚,勉励他继续为军统效力。
据刘人寿、何荦等回忆,潘通过袁殊等人的关系,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13日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报告,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等。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
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苏军仓促应战,节节败退,日军下一步究竟是北进配合德国夹击苏联,还是南进和英美作战,这对中国和世界局势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据说当时的毛泽东为此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头,袁殊提供的日军南进战略情报,不仅为潘汉年,而且也为毛泽东解了燃眉之急。从1941年7月到9月间,潘汉年及时将袁殊等人提供日军南进的战略情报报告给延安。潘汉年侄子潘冠儒在接受采访时说:“所以主席说了一个就是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而且还让康生给小开(指潘汉年)回电,写一个最大的好。康生说,在电文里体现不出这个最大的好,主席说那你就写好好好好好,就五个好。”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获得中共提供的日军南进可靠情报后,斯大林这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人的兵力到西线。后来,苏联历史文献纪录片《莫斯科保卫战》解说:“根据来自中共的可靠情报,斯大林果断调兵”,从而击退纳粹德国军队,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袁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胜利,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利用职务之便从事秘密工作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紧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等,指示立即帮助宋庆龄、何香凝等在港文化与民主人士安全离港。这年12月8日,袁殊自宁返沪,向潘汉年报告,汪伪陈璧君、陈君慧、林柏生等已飞抵香港,意图诱骗滞港名士与南京合作。此后,300多名在港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如宋庆龄、柳亚子、陈济棠、邹韬奋、茅盾、胡蝶等,经各方努力,被成功转移内地。
其时,袁殊颇得汪伪信任,先后担任了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伪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伪江苏省教育厅长、伪镇江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职。他利用职务之便,及时向中共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等情报;建立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营救新四军被俘成员,掩护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等。袁殊任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后,暗中开展“反清乡”活动:他首先向党组织报告了日军清乡的重点区域划分,粟裕部队得到消息后,用门板搭在桌椅板凳上,连夜跳出篱笆墙转移。他还利用职务之便营救被俘的新四军、释放被关押的地方党群干部30余人。
1942年9月,中共中央电示仍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潘汉年,考虑撤退问题。为保证刘晓和潘汉年安全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袁殊接受了掩护撤退的任务。镇江,本为连接苏北的交通要道。他利用职权以及与汪日人员的关系,套取情报,使他任伪职的镇江成为中共人员转移的要道。此外,袁殊还为潘汉年从岩井处取得由领事馆签发的一张特别通行证,上书:“凡驻沪军、宪、警等人对此证持有者有所检问,务须与日本驻沪总领事取得联系,不得造次!” 这无疑是一张护身符,保障了潘汉年的往来安全。
秘密转移到解放区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日汪气数将尽。袁殊辞去了其他汉奸伪职,只保留一项伪上海市政府参议的头衔。这时,潘汉年已离开上海两年多,接替他在上海工作的人虽和袁殊仍有一些联系,但已很少。当此历史又将发生重要转折的关头,袁殊再一次面临了今后去向的选择。
按后来袁殊自己的说法,当时面前有3条路:第一条路是携带家眷前往日本,做一个海外寓公。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汉奸,但他不想走当汉奸的这条路;第二条路是接受国民党的收编,仍然可以高官厚禄。抗战刚一胜利,军统的王新衡就赶到上海,代表军统任命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中将站长。然而,袁殊深知军统内部派系林立,互相矛盾倾轧甚深。像他这样非黄埔嫡系的人稍一不慎,是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
于是他选择了第三条路,回归他早年就曾经追求过,中间又经过了反复曲折的革命之路。临走前,他着手清理“岩井公馆”所属的财产,将3大皮箱的金条、美钞、英镑以及大批房契、地契、银行单据等价值近千万元的财产,转交给了上海秘密党组织,显示出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45年10月7日凌晨,在上海中共秘密组织和华中局联络部的精心安排下,由交通员黄炜护送,袁殊与翁从六、梅丹馨、李钦方等人通过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驻地,又穿越国民党军队管辖的狼山地区,从水路进入淮阴解放区。华中局联络部部长杨帆亲自到码头迎接袁殊一行的到来。到达驻地后,陈毅、饶漱石分別宴请袁殊,欢迎他来到解放区,然后袁殊安全转移到苏北解放区,结束了长达15年的秘密情报生活。而直到第二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了袁殊回到解放区的消息,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还对袁殊下达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
袁殊投奔解放区受到了热烈欢迎。数月之后,组织部门让袁殊重新登记入党,并任命其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定为旅级,负责国统区宁沪一带的策反工作。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建议袁殊暂时改名,对外改姓曾。从此,袁殊改名为“曾达斋”,一用就是近40年。在3年解放战争中,袁殊先后在苏北、胶东、大连从事内勤工作。
坎坷的晚年岁月
1949年2月,北平解放。李克农亲自调袁殊到国务院情报总署与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这是袁殊一生中最为红火的日子。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专门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定期为《世界知识》撰写有关日本问题的政论性文章,在部里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袁殊曾应邀为部里的干部和年轻同志作情报工作报告,朱德在听了他的报告后,夸他是“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

1954年军委在审干中给袁殊正式做了政治结论:1935年被捕时自首变节有严重政治错误,后来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谁知“结论”的墨迹未干,1955年4月发生了潘汉年冤案,当年曾在上海为潘汉年工作过的秘密党员几乎无一幸免。同月26日,44岁的袁殊亦被捕入狱,1965年,袁殊被以“军统特务”“日本特务”和“汉奸”罪名被判15年徒刑。1975年5月离开秦城监狱后,袁殊的行动仍然受限,被送到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参加学习和劳动改造。
在20年的牢狱生涯中,袁殊通读了《资本论》、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撰写了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并仍然关注着党的情报事业,写下了近8万字的《南窗杂记》,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的经验。
1978年10月,袁殊第二次回京探亲时,到中组部递交了要求重新复查自己问题的信函,向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他表示:“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回到农场后,袁殊继续进行申诉。他在给儿女的信中说:“监狱里的审讯记录,都是我赖以平反的依据……政治上我对党问心无愧,这一点我死可瞑目。”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袁殊等大批受潘案牵连的人也得到了平反。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撤销1965年判罪,宣告袁殊无罪。同日,公安部、调查部复查袁殊政治问题,确认他于1931年加入中共,恢复其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享受原定级别待遇。原没收财物折价归还,于北京西苑分配新房一套。当一切都成为历史之后,他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原名,他认为“用袁殊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此后,年逾古稀的袁殊曾回到潘汉年的家乡,悼念逝去的战友,缅怀过往的峥嵘岁月,写下了《履痕重印江南路》的文章。1987年11月26日,袁殊在北京解放军309医院病逝,享年76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