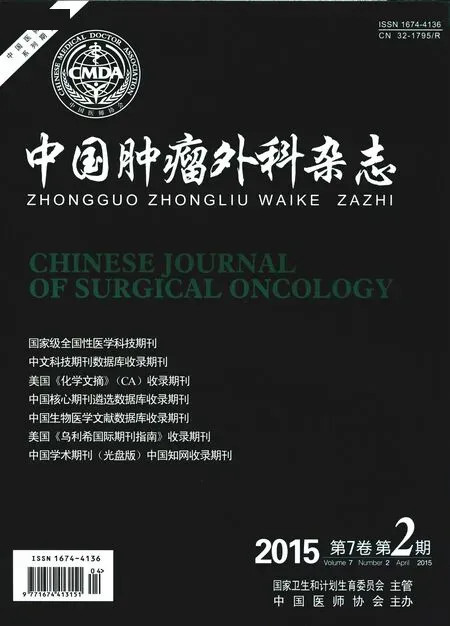鞍区黄色肉芽肿1例
廖艳彪, 李 江, 陈朝华, 李 辉, 杨明方, 彭立辉, 卢 明
病例报告与分析
鞍区黄色肉芽肿1例
廖艳彪, 李 江, 陈朝华, 李 辉, 杨明方, 彭立辉, 卢 明
颅内占位; 鞍区肿瘤; 黄色肉芽肿
黄色肉芽肿是一种组织细胞增生症,多表现为皮肤多发呈黄棕色丘疹或结节。病变极少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国内外仅有零星病例报道,我院收治1例鞍区占位性病变,经手术后病理确诊为垂体黄色肉芽肿,现报道如下。
1 病例资料
患者,女,50岁,因“视物模糊4年余,右眼失明1年”入院。患者于2009年起无明显诱因出现视物模糊,2010年底视物模糊加重并出现颜面部浮肿,伴双下肢乏力。检查垂体泌乳素为2 155.0 μIU/ml;头部MRI示:鞍区占位性病变(颅咽管瘤?垂体瘤?血管畸形并卒中慢性血肿形成?)。患者视力渐进性下降,部分视野缺失,考虑为垂体瘤而行伽玛刀治疗。2012年起患者右眼视力完全散失,颅内占位效应明显,存在视力失明可能,与患者和家属沟通同意行手术切除。2013年7月10日在全麻下经右侧翼点入路,显微镜下切除肿瘤,术中见肿瘤呈苍白色,外膜边界清楚,大小约2 cm×3 cm,质韧,与双侧前床突联系紧密,右侧视神经被肿瘤包绕,切开可见淡黄色液体流出。术后病检报告:黄色肉芽肿。免疫组化:CD68(+);HMB45(-);MLA(-);GFAP(-);KI-67(-);CgA(-);CD34(-);上皮成分:EMA(+);HCK(弱+);LCK(+)。手术后半年复查未见复发。

图1、2 MRI显示鞍区及鞍上见37 mm不规则囊状信号改变,呈分层改变,边界清晰,病灶经鞍上池向右上方凸出,与右侧视神经关系密切并压迫右侧额叶,视交叉受压显示不清。图3 HE染色×100。图4 HE染色×400镜下显示玻璃样变纤维组织,含铁血黄素,慢性炎细胞,少量巨细胞及泡沫细胞,胆固醇性裂隙,少量单层或复层鳞状上皮。
2 讨论
黄色肉芽肿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疾病,有一定自愈倾向,偶可见于呼吸、泌尿等其他系统。黄色肉芽肿常见多种系统性肉芽肿病变,如:EndheimChester病,WeberChristian病等[1]。其发病机制不明确,可能与自身免疫有关。最近有学者发现颅内黄色肉芽肿可能与单核细胞系统的异常增高有关[2]。
由于颅内黄色肉芽肿罕见,对于黄色肉芽肿的诊断与治疗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影像学检查对于颅内黄色肉芽肿的诊断和病情变化是一项重要的诊断方法[3]。也有人认为当怀疑颅内黄色肉芽肿时应该积极活检[4]。但另有学者认为不能过分强调病理学检查,由于黄色肉芽肿具有自愈倾向,其过程缓慢,长期随访密切观察对于诊断十分重要[5]。在治疗上,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特别适合术后有多个残留病灶[6]。Sun等认为对于单发性的颅内黄色肉芽肿可以采取手术切除,肿瘤的切除首先要保证手术安全和保护神经功能;对于手术不能切除的可以采用放疗联合化疗[7]。国内也有相似观点,仪晓立等[8]认为中枢神经系统的黄色肉芽肿可能自然消退,当然也可能存在危及生命的情况发生,主张在安全可行的情况下,争取手术全切,对于不能全切或多发病灶,可以尝试放化疗。Chidambaram等[4]人也肯定了激素治疗、化疗、放疗有一定疗效,但也认为把握好手术时机可取得更好的效果,即在颅内黄色肉芽肿增大时选择手术治疗。这与Kasliwal等[5]的观点相同。虽然放化疗以及激素治疗文献报道有一定效果,但是Chiba等[9]人在对1例多发性颅内黄色肉芽肿患者追踪时发现该例患者对于化疗无效,激素治疗虽然可以改善临床症状但是可能导致黄色肉芽肿的再复发。另外有报道发现全身累及到颅内的黄色肉芽肿患者预后要好于单发于颅内的患者,颅内单发性黄色肉芽肿应该选择手术治疗,术后应该长期随访,如病变有增大趋势应考虑尽早给予辅助治疗[10]。
总之,颅内黄色肉芽肿十分少见,而本例发生于鞍区垂体临床罕见。当发现患者颅内囊性占位性病变且进展缓慢时应该考虑黄色肉芽肿可能,并重视活检以免漏诊。本例患者在手术前已经行放射治疗,但是治疗后仍然出现视力减退等症状。综合国内外文献报道,作者认为颅内黄色肉芽肿的治疗应倾向于手术治疗,放化疗以及激素治疗可作为辅助治疗,其疗效缺乏大规模的临床实验不排除有增加占位效应的风险。
[1] 曹旭东,仁增,蒲智,等. 颅内硬脑膜型黄色肉芽肿一例并文献复习[J]. 西藏科技, 2010,(8): 41-42.
[2] 董必锋,程岗,李亮,等. 青少年颅内单发黄色肉芽肿1例报告[J]. 中华神经外科疾病研究杂志, 2011, 10(3): 279-280.
[3] 白凤森,邹继珍,苏英姿,等. 累及中枢神经系统的幼年性黄色肉芽肿二例[J]. 中华放射学杂志, 2011, 45(11): 1074-1076.
[4] Chidambaram B, Santosh V. Giant orbital and intracranial xanthogranuloma——a short report[J]. Neurol India, 2001, 49(2): 208-210.
[5] Kasliwal MK, Suri A, Rishi A, et al. Symptomatic bilateral cerebellar mass lesions: an unusual presentation of intracranial xanthogranuloma[J]. J Clin Neurosci, 2008, 15(12): 1401-1404.
[6] Nakasu S, Tsuji A, Fuse I, et al. Intracranial solitary juvenile xanthogranuloma successfully treated with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J]. J Neurooncol, 2007, 84(1): 99-102.
[7] Sun LP, Jin HM, Yang B, et al. Intracranial solitary juvenile xanthogranuloma in an infant[J]. World J Pediatr, 2009, 5(1): 71-73.
[8] 仪晓立,袁新宇,白凤森,等. 幼年性黄色肉芽肿引起中枢性尿崩症:1例报告并文献复习[J].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2013, 29(3): 261-262.
[9] Chiba K, Aihara Y, Eguchi S, et al. Diagnostic and management difficulties in a case of multiple intracranial juvenile xanthogranuloma[J]. Childs Nerv Syst, 2013, 29(6): 1039-1045.
[10] Tamir I, Davir R, Fellig Y, et al. Solitary juvenile xanthogranuloma mimicking intracranial tumor in children[J]. J Clin Neurosci, 2013, 20(1): 183-188.
410003 湖南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暨解放军第163医院 神经外科
廖艳彪,男,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脑外伤神经康复,E-mail:liaoyanbiao1986@163.com
10.3969/j.issn.1674-4136.2015.02.022
1674-4136(2015)02-0131-02
2014-10-21][本文编辑:李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