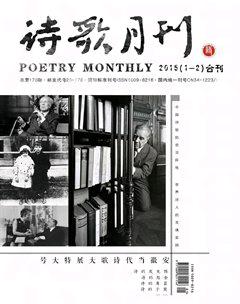樊子的诗(10首)
樊子,1967年11月出生于安徽寿县,现居深圳。在《诗刊》、《十月》、《星星》、《山花》、《作品》等近百家文学期刊发表过诗歌、随笔和评论作品。
赶考记
一条羊肠小道弯曲又弯曲,靠近铁轨的方向,也就是
油菜花褪色的五月,在广场之外
我们什么时间学会了三五成群,露宿野岭,从村落里
偷来羔羊
三刀剁下,羊血没有四溅。学贼不行,我们斯文扫地,
嚎啕大哭
你爬过最高的山肯定不是泰山,去过最长的河流自然
不是黄河
仅仅就这些真实了,不要去谎称自己的身份和来历
我们要不不学人模狗样,我们要不随无数条羊肠小道
弯曲再弯曲,索性不上京城了
中途在一个叫安徽的地方停下来睡一个好觉。
再从村落窃来公鸡,放在山头的苦楝树上
一早,雄鸡会喊醒河南、江苏、湖北、江西、浙江和
山东,闹得它们要早起
要上厕所
要洗昨夜的内裤
祖国
足够辽阔了,在这片土地上我已跪下很久了
我有骄傲的时候,会用刀子划破膝盖,我不知道什么
叫疼痛
偶有发自内心的崇高
祖国,你有弯路和坎坷
在我站立的尊严中,你应该也有胆怯与羞耻
绳索
奔跑的马匹有着和广场雕塑一样腐烂的过程
马匹靠绳索走完它的方向,伟大的雕塑借助绳索
一寸寸完成臀部和额头的对接
奔跑的马匹颠簸着奶子或者阴囊,我们视而不见
我们喜欢远观马匹的气势,羞于说出马的性别
面对塑像,我们细察其脸庞、眉毛、手势,耻于
猜想花岗岩材料隐藏的某种部位
老子日:“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老子是一条绳索,绳索的一头叫美,另一头叫恶
中间部分该为道
这点我弄明白了,伟大就是卑鄙,龌龊即为崇高
君子乃为小人,逆贼实为良民
绳索两端系成疙瘩就是家国和人生
绿皮火车
绿皮火车在榛莽未除的山坡上发出咔嚓咔嚓的摩擦声
枕木最早铺在藏有星光的山洞里
时间慢慢蠕动
如夜鸟惺惺地叫着
它的喧闹,它的地平线,它拉风的胃
它把臃肿和肝病涂上颜色,像
羊吃完最后一株青草时嘴角的绿色唾液
它没有盐分
它是一条失去冬眠习惯的蟒蛇
它是一个手握烂苹果和麦芽糖的起义者
它还不懂得转过身子来
我在它相反的时间里铺着枕木,从老年
铺到少年
它一生都在听我的肋骨和颧骨从不间断的塌陷声
阴谋者
我和阴谋者一起登山远眺,
一起驾舟远行,
一起赶着一群牛羊。
一头母牛停止走动,盯住我们,它尾部下垂,翘起尾巴
我对阴谋者说:“你的帽子掉在地上了。”
阴谋者摸摸头,他没有戴帽子,
我指前面母牛屙下的一团热气腾腾的牛粪,
阴谋者哈哈大笑。
阴谋者学母牛状把臀部下蹲,涨红脸,试图憋出几声响屁
阴谋者指着天空,说:“打雷了。”
我仰起脖子,说:“对。”
天空真的响起滚滚雷鸣,
阴谋者一脸惆怅,他说这个年代雷鸣是TMD噪音,
不如放屁。
雷鸣越响越大,
我涨红脸对阴谋者发誓,真的没有听见他的放屁声,
阴谋者有一些失落,他请求我再陪他去登山远眺一回,
架舟远行一次,
然后在大地上赶一群牛羊,
基于他伟大的想法,我答应了……
而我们遭遇同样的过程:一头母牛停止走动,盯住
我们,它尾部下垂,翘起尾巴
我慵懒地对阴谋者重复一句:“你的帽子掉在地上了。”
打铁
是在我们的春天里,烂泥烧成了瓷器
石块凿成磨盘,镰刀经过锻打,成为铆钉
一只陶瓷想过起义者的火炬
一块磨盘想过比乳房还干瘪的南瓜
一把镰刀想过乌黑的辫梢
一个铆钉想过骰子,它滑动,跳舞,咦,解决了
腐朽与永恒的矛盾
它们都是对的,在纷攘的春天
暴力也会带来喜悦的气氛,吃草的
羊群被乌云卷走
乌黑的山巅沉到溪水之中
它们都有自己的欢乐
在春天的土地上,经过淬火的铁块
散落在每一个角落
它们有各自的想法
它们喜欢自己的想法:
一个铆钉想过骰子,它滑动,跳舞,咦,解决了
腐朽与永恒的矛盾
这暧昧的春天,它的色彩充满滑稽的生机
我劳累的一生,试图
把所有圆、长、方、扁、尖的物件
锻打成一种成形的信念
我多么的可怜和无知
手臂不曾去想强盗的快乐
头颅从未分享过阴谋者的正义
旧物
我翻看过祖父留在尘世上的衣领和袖口
土墙上破烂的棉絮里
死亡的虱子是暗红色的
锄头、木锨、马灯和酒壶,它们没有了温度
你知道,在这个冬季,我一一拿起它们又放下
没有放在它们固有的位置上
我显得多么的无知
有一些时光是注定不能重复的
我接着去掏祖父曾经的衣兜
这个无常的世界啊
我去年就这样掏着祖父破旧的衣兜
摸到僵硬的东西拿出来看看
是一个镍币和四粒豌豆
悲歌
雨啊,它淹没我的脖子时,
我看到的闪电,很久撕不开越积越厚的帷幕。
风吹破穷人家的屋脊时,我想起你庭院里的香樟树
它的叶子上有着美好。
我爱的人啊,我想怀抱一个女婴
听她哭出未来尘世间的苦。
大风歌
信仰的方向在哪里?大风从四面八方吹来
翻滚的石头,激起的浪花,折断的树木
这些都不是大风所为
早晨消逝了,夜晚也消逝了
那些不知去向的海水、逃遁的山巅
和有色彩的言辞
本身就是无边无际的空白,不如月亮的岛屿有活的气息
你有肮脏的容颜和责任,早晨消逝了,夜晚也消逝了
当你明白一滴泪水从来都没有被大地接受的时候
你也知道大风是伟大的骗子,它跛着脚,披头散发
满嘴胡话连篇
当你所有的疼痛仅仅会信仰正义
你不如一只蚂蚁更清楚,大风走过的土地
从来就不会产生什么意义
樊家村
西北方有朔风,枯树的枝桠散乱在云层里
我们有门朝南开的村庄
东边坡地上歪着年久失修的宗祠
西边为一片白晃晃之湖
我起的最早,一个少年要去宗祠上香,然后给一排灵牌下跪磕头
这时候雪飘下来了,大雪加重了村庄的寂静
羊在栅栏里孤独而固执地叫着
你不可在此时来到樊家村,从西边坐船过来,你要选择在春天
瓦埠湖浩淼百里,水的尽头嘉树四合,水到了曲折平衍处
你鼻腔里水的腥味和钉木船的桐油味会被油菜花香替代
不要告诉我你看见了土坯房里发育的奶子和我衣领上的红花
不可驻足,不可观望过多,几只芦花鸡在粪堆上觅食
大黄狗伸长舌头去舔一只黑母狗屁股
春天充满蠢动和危险,你也可在夏夜从西北方过来
西北方苦楝树成林,老鸹会在你经过时发出“哈”的骇笑声
所有的星光都隐遁于树的褶皱里,树林在闷热中长出硕大的繁枝
生长是一种力量,有腥、臊和汗臭味
樊家村就错落在夏夜的树林中,蚊子叮咬男人的脸、女人的屁股
也叮咬着畜生的下巴
坡地下的南瓜藤长到坡地上的玉米地,湖里的蛇把身子盘在池塘的荷叶上
这些都是我描述给你的:樊家村在瓦埠湖东岸,岸若僵蛇蜿蜒,
没有尽头也看不到岸的起点,东岸之东为一洼地,是瓦埠湖闭塞之所,
形同簸箕状,沿溪水深入,驻足石拱桥,能见洼地多田畦和牛羊,
六个村落羼杂于一体,一阵风把一汉子顶上的泛黑的草帽吹落,
那顶草帽会正好落在用弯镰勾槐树花的妇人的蓬松的头上
这种原始况味的景致描述过多有何意义呢?
夏天的樊家村,星光依旧带来贫苦
你不可再来,我从十月离开樊家村,稻谷成熟,母亲光着身子手被镰刀割破
父亲撑船,醉卧船头,旱烟杆时不时敲击着斑驳的船舷
宗祠的坡地上,死去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酗酒、赌博、打架、搞女人,
偶有怨气者化成鬼火在乱冢中嚎啕大哭
我没有听见鬼的哭声,时常听见愤怒的磨刀声和可怜的呻吟之声
我还是回头从十一月拐进十月,拐进母亲的稻田,又在船头扶起父亲
我清楚村里有八头牛、一口井、两个碾坊和一间酒铺
然后,再从十月拐进六月,雨季中,土屋坍塌,父亲的船舷上粘满黑黑的螺蛳
我又径直奔向三月,告诉我在春风中长高的石榴树和在阳光下苍郁的柏树
哪个更接近于棺木?
现在,我退回十二月,宗祠绿色琉璃筒阴瓦被簌落的雪覆盖
西北方的朔风带来沙尘和推土机的轰鸣声
樊家村会在十二月变得寒冷和萎缩,百里之内的合肥灯火辉煌,
千里之外的京城威严四射
樊家村,在我还没有彻底离开之际,不忍去
——撕去每一户门上经年的门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