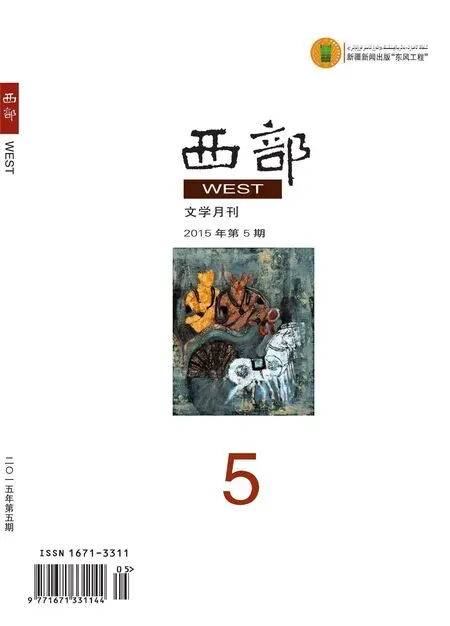陌路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著 钟志清 译
周边
陌路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著 钟志清 译

阿摩司·奥兹,当代最富有影响力的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早年曾在希伯来大学攻读文学与哲学,获学士学位,后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和特拉维夫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著有《何去何从》(1966)、《我的米海尔》(1968)、《沙海无澜》(1982)、《了解女人》(1989)、《莫称之为夜晚》(1994)、《地下室里的黑豹》(1995)、《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等十余部长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乡村生活图景》(2011)、《朋友之间》(2012)等短篇小说集,以及多部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曾获多种国际文学奖。
《陌路》与《亲属》选自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2011)。
1
傍晚时分。鸟叫了两遍。其中意味无法得知。微风拂煦,而后又止。老人搬出椅子,坐在门道里,观看路人。汽车时而从那里经过,消失在公路拐弯处。一个女人缓缓地走过,她拿着一个购物袋,从杂货店回家。一群孩子在街上吵吵嚷嚷,他们走过之后吵嚷声便消失了。一条狗在山坡后吠叫,另一条狗回应着它。天空变得灰蒙蒙的,只有西边透过成荫的柏树可看到落日的余晖。远处的山峦黑黝黝的。
考比·埃兹拉,一个郁郁寡欢的十七岁少年,站在一棵桉树后等待,桉树树干被涂成了白色。他身材细瘦,样子有些虚弱,双腿瘦骨嶙峋,皮肤黝黑,脸上总流露出忧伤的惊奇,仿佛不久之前经历了一场令人不快的意外。他身穿一条沾满灰尘的牛仔裤,还有一件印有三巨人节传说字样的T恤。他不可救药地坠入情网,困惑迷茫,因为他所爱的女人年龄几乎比他大一倍,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情人,所以他怀疑对方对他的感情只是礼貌的同情。他希望她能够猜出他的真实心意,但又怕她一旦猜出就会拒绝他。今天晚上,如果她男朋友没开着他的柴油油罐车过来,他会主动提出陪她从她上白班的邮局走到她上晚班的图书馆。也许这次他终于可以说点什么,让她了解他的情感。
邮政局女局长阿达·达瓦什也是特里宜兰村图书管理员,一位三十多岁的离婚女子。她身材不高,快乐,丰满,面带微笑。她留着披肩发,垂到左肩的头发比垂到右肩的头发要多,走路时一对硕大的木质耳环摆来摆去。她那双褐色的眼睛让人感到温暖,一只眼睛有点眯眯眼,为她平添了几分魅力,好像她故意眯缝起眼睛,有些顽皮。她喜欢她在邮局和图书馆的工作,做事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她爱吃夏季水果,酷爱轻音乐。每天早晨七点半,她分拣邮件,把信件和包裹放到居民的信箱里。八点半她打开邮局门,开始营业。一点钟,她锁门回家吃饭休息,从五点到七点又在邮局开门营业。七点她锁上邮局的门,每逢周一和周五,她径直去往图书馆。就她一个人,处理信件、包裹、电报和挂号信,热情欢迎顾客前来购买邮票和航空邮简,支付账单或罚金,或者登记购买汽车或卖掉车子。大家都喜欢她随和的态度,如果柜台那里无人排队,他们则逗留片刻,和她聊聊天。
村子很小,来邮局的人不是很多。多数人只是来检查固定在外面墙上的邮箱里有无信件,之后便离开了。有时会有一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都没人走进邮局。阿达·达瓦什坐在柜台旁边分拣信件,填写表格,或者把邮包排列得方方正正。村里人说,有时,会有一个两条浓密的眉毛聚在一起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前来看她,他不是本村人,身材高大魁梧,总是身穿蓝色工作服,脚穿工作靴。他把他的柴油油罐车停在邮局对面,坐在入口的长椅上等她,并不停地把一串钥匙抛向空中,然后一只手接住,自娱自乐。每当他把油罐车停在邮局对面或她家门前,村民们就说,阿达·达瓦什的男朋友又来度蜜月了。说此话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几乎充满深情,因为阿达·达瓦什在村里颇受欢迎。四年前,当她丈夫与她分手时,村里多数人都站在她这边,而不是她丈夫那边。
2
借着暮色,男孩在桉树下找到一根木棍,他一边等待阿达·达瓦什干完邮局的工作,一边用木棍在地面上画出男男女女的形状。这些人画得有些变形,好像他在画画时心存厌恶。光线越来越暗,因此没人可以看见这些人物画,实际上连他自己几乎也看不到。后来,他自己用拖鞋抹掉了这些人形,扬起一股烟尘。他设法找到合适的字眼以便陪同阿达·达瓦什从邮局走向图书馆时与她交谈。以前他有两个偶然的机会陪她,他热情洋溢地说起自己酷爱图书与音乐,然而没能传达出任何真情实感。也许这次他应该和她谈论孤独,可是她也许会形成一种印象,以为他是在说她离婚的事,可能会冒犯她,或者伤害她。上次她跟他说喜欢《圣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读上一章。因此这一次或者从圣经爱情故事谈起,谈谈大卫,谈谈大卫对扫罗女儿米甲的爱,或者谈谈《雅歌》,可他对《圣经》知之甚少,他害怕如果开始讲自己知之甚少的主题,阿达会轻视他。最好和她谈谈动物:他喜欢动物,与动物非常亲近。比如,他大概可以谈某种歌鸟的交配习惯,也许他可以用歌鸟来暗示自己的情感。可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和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在一起会有什么希望吗?也许至多唤起某种怜悯。从怜悯到爱,距离就像从映照在水坑里的月亮到月亮本身之间的距离一样,遥不可及。
与此同时,光线愈加黯淡。几位老人依然坐在自家门前的椅子上打盹,或者两眼盯着前方,但多数老人收起椅子回家去了。街上空空荡荡。村子周围山上的葡萄园里响起了胡狼的嚎叫,村里的狗狂叫着予以应和。远处传来一声枪响,划破了黑暗,随之而来的便是蟋蟀唧唧,响成一片。再过几分钟,她就会出来,锁上邮局,再去图书馆。你会从阴影中出现,像前两次那样询问她,是否可以与之同行。
她上次借给他的《达洛维夫人》一书,他还没有看完,可是他想让她再借给他一本,因为他计划整个周末都看书。你没有朋友吗?不打算去娱乐吗?没有,他肯定没有朋友,没有计划。他宁愿宅在家里看书,或者听听音乐。他学校的朋友喜欢吵吵闹闹,喜欢喧闹的环境,而他则喜欢安静。这一次他要这样跟她说。她会由此看出他的与众不同。你为什么总是和别人不一样呢?父亲总是劝他,你应该出去,做些运动。他母亲每天晚上走进他的房间,检查他是否还有干净的袜子穿。一天晚上,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第二天父亲没收了钥匙。
他用木棍刮擦着涂上石灰的桉树树皮,接着摸摸下巴,看看两小时之前刮的脸是否依然说过得去。他的手指从下巴摸向脸颊和额头,想象他的手指是她的手指。快七点时,从特拉维夫来的大巴到了,停在村委会办公室前。考比躲在桉树后,看到人们拎着大包小包走下大巴。他从人群中认出了斯提纳博士,也认出了他的老师拉海尔·弗朗哥。她们谈论着拉海尔的老父亲,他出门去买一份报纸,忘记了回家的路。她们说话的声音传到他这里,但他听不懂她俩在说些什么,也不想知道。人们散去,声音也消失在远方。又可以听到蝉鸣了。
七点整,阿达·达瓦什从邮局出来。她锁上门,也锁了扣锁,检查了一下是否锁牢,然后穿过空空荡荡的大街。她身穿一件宽松的夏装和一条质料轻薄的大摆裙。考比·埃兹拉从藏身之地冒了出来,声音轻柔,好像怕吓着她,又是我,考比。我可以和你一起走走吗?
晚上好。你在这里站了多久了?
考比想撒谎,但不知为什么竟然说了实话,我在这里等你有半个小时了,甚至还要长一些。
你为什么等我?
不为什么。
你可以直接去图书馆的。
当然。但我更愿意在这里等。
你是来还书的吗?
我还没看完呢。我来是想让你再借我一本书,周末看。我把两本都看完。他就这样一边和她走上奠基者大街,一边告诉她,他差不多是班里唯一读书的男生。其他男生沉迷电脑或运动。女生呢,对,有些女生读书。阿达·达瓦什一清二楚,但不想提起,免得让他难堪。他一直走在她身旁,滔滔不绝,好像是怕一旦停下她就能发现他的秘密。她猜出了这一秘密,却不知怎样才能避免伤害他,又不误导他。她不得不克制自己伸手抚摸他的头发的冲动。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只有前面留了一缕额发,使他平添了几分孩子气。
你没有任何朋友吗?
男生都很幼稚,像我这样的人对女生又没有吸引力。
接着他突然加了一句,你也和别人不大一样。
她在暗中笑了,抻抻有些歪斜的上衣领口。她走路时,那副大木耳环来回摆动,好像有它自己的生命。考比继续说个不停。他说社会缺乏信任,甚至蔑视真正有价值的人。他一边说,一边感到有种冲动,想去摸一摸身边走着的女人,不管是轻轻地还是短暂地摸一摸。他伸出手指,指尖几乎碰到了她的肩膀,但在最后一刻,他缩回手指,攥紧拳头,垂下胳膊。阿达·达瓦什说,这家院子里有一只狗,有次追我,咬了我的腿。我们赶紧过去。
当阿达提到她的腿时,男孩的脸腾地红了,他高兴的是天很黑,她注意不到。可是她确实注意到了什么:不是注意到他脸红了,而是注意到他突然陷入了沉默。她轻轻地碰了碰他的后背,问他觉得《达洛维夫人》怎么样。考比开始激动地谈起此书,声音发颤,紧张,好像正在坦白自己的情感。他谈了很长时间的《达洛维夫人》,也谈了其他的书,他认为只有当人生忠于某种主张或情感,一切均围绕这种主张或情感进行时,才有意义。阿达·达瓦什喜欢他精巧的用词,但是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如此孤独并显然从未交过女友的原因。他们来到图书馆时,他还在滔滔不绝。图书馆位于文化厅后翼的一层。他们从侧面入口走了进去,时间是七点半。阿达建议给二人冲杯咖啡。考比开始嘟囔,不,谢谢,不需要,真的,但是他随即改变了主意说,实际上,干嘛不呢。谢谢你。他说,也许自己可以帮上什么忙。
3
明亮的白色氖灯灯光把图书馆照得通明。阿达打开空调,空调启动时发出轻柔的咯咯声响。图书馆里排列着漆成白色的金属书架,所占空间不大,书架之间形成了三条平行过道,虽然灯光也照到这里,但不那么明亮。在入口附近,放着一张办公桌,办公桌上放着电脑、电话、一摞小册子和期刊,两摞书,还有一台旧收音机。
她走进一个过道,从他的视线中消失。在过道一头,有洗涤槽和通往厕所的出口。她在那里把水壶灌满,通上电。她一边等着水烧开,一边打开电脑,让考比挨着她坐在办公桌后头。他垂下眼帘,看见她的柠檬色裙子未盖住她的膝盖。看到她的膝盖,他的脸又红了。他把双臂放到大腿上,转念一想,把双臂交叉在胸前,最后把一双手放到了桌上。她看看他,他觉得她左眼轻轻一瞥,正在朝他使眼色,似乎在说,没那么糟糕,考比。你又脸红了。
水开了。阿达·达瓦什冲了两杯黑咖啡,问都没问就往咖啡里放了糖。她把一杯咖啡推向他。她看到他的T恤上写着三大巨人节,不知是什么节日,三巨人又是谁。已经七点四十分了,没有人来图书馆。办公桌一头放着上星期收到的五六本新书。阿达给考比演示怎样把新购置的图书在电脑里编目,怎样给图书加盖图书馆的图章,怎样给图书加一层结实的塑料薄膜,怎样在书脊上粘贴书号标签。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助理馆员了,她说,又加了一句,告诉我,家里人不盼着你回去吗?吃晚饭?也许他们已经为你担心了。她眯缝着的左眼深情地眨动着。
你也没吃晚饭呀。
可我总是等图书馆关门后才吃。我从冰箱里抓些吃的边吃边看电视。
一会儿我再陪你从这儿走回家,你就不用一个人摸黑走路了。
她朝他微笑,把自己温暖的手放到他手上。
不需要,考比。我的住处离这里只有五分钟。
她的手一碰他,从他的脖颈到脊梁骨便涌起一股甜蜜的颤抖。他从她的话中推断出她的男朋友,那个开柴油油罐车的司机,一定在家里等她,即使他现在不在,她也许期待他夜里晚些时候再来,因此她说不需要他陪她走回家。可不管怎么样他会像只狗一样,跟着她走到她家台阶,等她关上房门,他会留下来坐在台阶上。这一次他也会握着她的手道晚安,当她把手放在他手里时,他会轻轻地握两下,这样她就明白了。这个世界在他眼里很糟糕、很畸形、很可鄙,一个柴油油罐车司机竟然比他有优势,只是因为他年纪大。他在想象中,突然闪现出柴油油罐车司机的样子:两道浓眉聚在中间,肥大的手指从前面插进她的衬衣。这幅幻影令他感受到欲望和耻辱,夹杂着极度的愤怒,并想做些什么去伤害他。
阿达用眼角瞥见他,注意到了什么。她建议围着书架转转:她可以给他看各种小宝贝,比如爱勒达德·鲁宾书稿,稿纸边有他个人校订时的眉批手迹。但他还没有回答,两个老太太就走了进来,其中一位矮矮墩墩,身穿宽松的中长短裤,头发染成了红色,另一位一头短短的灰发,眼睛凸出,戴着一副深度眼镜。她们来还书,想再借几本新书。她们相互聊着,也和阿达聊着整个国家都在谈论的一部新出的以色列小说。考比逃进了一个过道,他在一个低矮的书架上发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他翻到书中间,站在那里看了一两页,以便不听她们的谈话,但是女人们的声音传到他的耳际。他发现自己无意中听到其中一个人说,我认为他不断地重复自己,他一遍遍地写同一本书,变化甚微。她的朋友说,连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也都重复自己,那又怎么啦。阿达微笑着说,有些主题和母题作家会一遍遍重复,因为它们显然是作家的生命之源。
当阿达说到“生命之源”时,考比感到某种东西在挤压他的心。那一刻,他很清楚她肯定要他无意中听到这个短语,她实际上是在和他说话,而不是在和老太太们说话,她试图说明他们的内心深处拥有同一个源。他在想象中走近她,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把她的头靠在自己肩上,因为他比她高一头。他能够感受到,她的双乳贴在他的前胸,她的腹部贴住他的腹部,接下来那副景象令人钻心地疼痛,无法忍受。
女人们走后,他在原地待了一会儿。等身体平静下来,他用比平时略加深沉的声音对阿达说,他过一会儿就来。与此同时,她在电脑里输进两个女人还书与借书的信息。
阿达·达瓦什和考比并肩坐在办公桌旁,好像他也在图书馆工作。两人一声不吭,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氖灯的滋滋声打破了沉寂。他们谈起在二战战事正酣之际投河自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阿达说无法理解为何有人会在战争中自杀,很难想象她没有一点参与意识,一点不想了解结果如何,谁能在那场可怕的战争中取胜,那会从某种方面影响世界上所有人,她甚至都不想知道她自己的国家——英国能幸存下来,还是会被纳粹占领。
考比说,她绝望了。
阿达说,那正是我不能理解的。至少总有一件东西对你是宝贵的,你不想与之分离,哪怕只是一只猫,或者一只狗,或者你喜欢的扶手椅。雨中花园的景色,或者窗外的落日。
你是一个快乐的人,绝望显然与你格格不入。
不,不是格格不入,但是绝望也不吸引我。
一个二十多岁戴眼镜的姑娘走进图书馆。她屁股滚圆,身穿花上衣,紧身牛仔裤。明亮的氖光刺得她眯起眼睛,她冲阿达微笑,也冲考比微笑,问考比是不是要做图书馆副馆员。她希望帮她找些1936—1939年的事件,又叫阿拉伯反叛的资料。阿达带她到放有以色列历史和中东历史类图书的书架,二人抻出一本本书,查看目录。
考比走向厕所旁边的洗涤槽,清洗两个咖啡杯。办公桌上的时钟指向八点四十分。又一个晚上即将逝去,你还没向她表露你的情感。这一次你不能让机会溜走。当你二人再次单独在一起时,你必须双手拉住她的手,直视她的眼睛,最终告诉她。可是你究竟要告诉她什么?要是她哈哈大笑怎么办?或者相反,要是她惊慌着缩回手怎么办?也许她对你说抱歉,把你的头贴在她的胸前,抚摸你的头发,把你当成了孩子。对他来说,怜悯比拒绝更为可怕。他很清楚,如果她对他表现出歉意,他会控制不住放声大哭。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眼泪,那样一切就会结束,他会从她身边跑开冲向黑暗。
与此同时,即使咖啡杯已干,他还是用挂在洗涤槽旁边挂钩上的抹布擦个不停,边擦边盯着不顾一切朝氖灯扑去的一只飞蛾。
4
戴眼镜的姑娘说声谢谢离开了,她用一只塑料袋拎了五六本关于阿拉伯反叛方面的书籍。阿达把办公桌上的图书卡片信息输进电脑。她向考比解释,其实每次只能借两本书,可是那姑娘十天后要提交论文。马上就九点了,阿达说,我们就要锁门回家了。听到回家这两个字,考比的心开始在胸膛里跳荡,似乎这两个字里包含着某种秘密承诺。接下来他翘起二郎腿,因为他的身体又开始兴奋,威胁着要令他难堪。一个内在的声音对他说,来吧耻辱,来吧嘲笑,来吧遗憾。他不能放弃,要告诉她。
阿达,听我说。
什么事?
如果我向你要某种个人的东西,你介意吗?
你说。
你爱过什么人,可他无法用爱来回报你吗?
她立刻看出他要把话头往哪里领,她喜欢这个男孩,但有责任慎重对待他的感情,她在二者之间犹豫片刻。在这两者之下,她也感到自己有脱口说出同意的朦胧冲动。
有,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是怎么做的?
女孩子都那么做。我吃不下饭,夜里哭,开始穿漂亮的吸引人的衣服,接着故意穿得没有光彩。直到一切过去。会过去的,考比,尽管暂时看来它会持续永远。
可是我——
另一位读者走了进来。这一次是一个年龄大约七十五岁的老太太,身体干瘦轻快,身穿一件对她来说有些过于年轻的浅色夏裙,瘦骨嶙峋的褐色手臂上戴着银手镯,脖子上戴着两排琥珀珠子。她向阿达打招呼,好奇地问,这个挺有魅力的年轻人是谁呀?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阿达微笑着说,这是我的新助手。
我认识你。老太太说着,朝考比转过身去。你是开杂货店的维克多·埃兹拉的儿子。你是志愿者吗?
是的,不是,实际上——
阿达说,他是来给我帮忙的。他喜欢书。
老太太还了一本外文小说,询问她是否可以借那本大家都在谈论的以色列作家写的书,先前来的两个女人已经发过请求了。阿达说已经有许多人在预约了,图书馆里只剩下两本。
我把你放在预约者名单上好吗,莉萨?大概需要一两个月。
两个月?老太太说。那时他又写完另一本小说了。又一本小说,更新的小说。
阿达劝她先对付着看一本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的小说,有很好的书评。老太太走了。
考比说,讨厌,还是个长舌妇。
阿达没有搭腔。她翻看着老太太还来的那本书。考比感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几乎难以忍受的急迫。这里又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但是再过十分钟,她会说关门的时间到了,也许机会又会失去,也许就这一次机会了。他突然恨起了令人眩目的白色氖灯,就像牙医的灯一样。他觉得灯光似乎阻止他向她表白。
咱们看看你是否真能做我的助手,阿达说。你可以记录一下莉萨刚借走的那本书,还有她刚还的那本书。我来教你怎么操作。
可是她把我当成什么了?他突然感到怒不可遏。她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孩子,她让我玩一会儿她的电脑,然后让我去睡觉?她怎么这么蠢呢?她什么都不懂吗?一点也不懂?他感受到一种盲目的冲动,要去伤害她,咬伤她,粉碎她,拽下她那副大大的木质耳环,让她醒一醒,让她终于明白。
她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够了,考比。
她用手触摸他的肩膀,令他晕眩,但也令他难过,因为他知道她只是设法安慰她。他转过身,用双手抓住她耳环下的双颊,使劲儿把她的脸转过来。他不敢把嘴唇凑近她的嘴唇,就这样抱了她很长时间,双手捧住她的脸颊,两眼死死盯着她的嘴唇,那嘴唇既没有张开,也没有紧闭。在耀眼的氖灯灯光下,她脸上露出他未能识别的表情:她看样子没有受到伤害或者冒犯,他想,是忧伤。他轻柔地然而坚定地抓住她的头,把嘴唇靠近她的嘴唇,整个身体在欲望和恐惧中颤抖。她没有抗拒他,也没有试图挣脱他的手,而是等待。最后她说,考比,我们该走了。
他放开她的脸,眼睛还在看着她。他跳起来,用抖动的手指寻找电灯开关。氖灯立刻灭了,整个图书馆一片漆黑。现在,他对自己说,如果你现在不跟她说,你会后悔一辈子,永远后悔。他在欲望与情感的冲突中,感到一种要庇护她、保护她的朦胧冲动。它发自内心。
5
他展开双臂摸寻她,发现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办公桌后。他在黑暗中靠着她,不是脸对脸,而是用脸抵住她身体的一侧,臀部压住她的腰部,呈T字型。黑暗赋予了他勇气,他亲吻了她的耳朵和鬓角,可是他不敢把她扳过来,用自己的嘴唇来搜寻她的嘴唇。她站在那里,双臂和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既不反抗他,也不配合。她的思绪驰骋,想到那个胎死腹中的孩子:她在怀孕五个月出现并发症后将孩子生下。医生说她不会再有孩子了。接下来情绪低落的几个月,她为孩子的死责备自己的丈夫: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大概在死胎事件发生之前的某个夜晚他和她同房。她不需要他,但任其行事,因为她从孩提时代起,就在意志坚强,尤其是在意志坚强的男人面前表现出顺从,这并非因为她生来就唯命是从,而是因为男人的坚强意志给她一种安全感、信任感、接受的感觉与屈从的愿望。现在她接受了一个男孩的侧面拥抱,既不鼓励他,也不阻止他。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两条胳膊耷拉着,脑袋也耷拉着。她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考比对此不知如何解释。
这是快乐的呻吟,就像他在电影中听到的那样,还是一种微弱的抗议?可是,一个富有想象、饱受性煎熬的十七岁青年人带着强有力的欲望,在她的髋部摩擦。因为他比她高整整一头,他把她的头拉到他的胸前,嘴唇温柔地在她的头发上犹豫,轻轻地触摸她的耳环,好像在分散她的注意力,要她别太关注他的腰部在对她做些什么。羞耻感并没有抑制他的欲望,而是使之愈加强烈:他知道现在他正在毁灭、践踏他和所爱之人之间的关系,将其扼杀。这种毁灭令他头脑晕眩,他用手去摸她的乳房,但惊恐之中他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他的腰部继续摩擦她的髋骨,直至脊梁骨和膝盖被快感吞没,颤抖不已。他得靠住她,免得摔倒。他感到腹部湿漉漉的,立刻移开,以免玷污她。他站在黑暗中喘着粗气,浑身颤抖,离她很近,但没有碰她。他的脸发烫,牙齿打战。阿达打破沉默,轻轻地说,我把灯开开。
考比说,好的。
可她并不忙着开灯,说,你可以去那边整理一下。
好的。考比说。
他突然在黑暗中喃喃自语,对不起。
他摸到她的手臂,抓在手里,用嘴唇挨擦,他再次请求原谅,转身走向门口,从图书馆的沉沉黑暗逃到夏夜那带有亮光的黑暗中。半月在水塔上空升起,在屋顶、树梢和东边阴影迷离的山峦上撒下苍白迷蒙的光。
她打开眩目的氖灯,一只手拉平上衣,另一只手抚平头发。她开始时觉得他只是去了厕所,但是图书馆的门大敞着,她随后走了出来,站在门阶上,让浓烈的夜晚气息充盈她的肺腑,那气息闻起来隐约像干草、牛粪和某些她叫不上名字的芬芳花朵香。你为什么离去?她自言自语,你为什么走开,孩子,你为什么如此惊骇?
她回到图书馆,关上电脑,关上空调和氖灯,而后锁上图书馆的门回家。路上陪伴她的有青蛙和蟋蟀的歌唱,还有吹来荆棘与泥土气息的轻风。也许那个男孩正躺在某棵大树下再次等候她,也许他提出陪她回家,也许这一次他会有勇气抓住她的手,或用胳膊搂住她的腰。她感受到他的气味,黑面包、肥皂和汗水的气味陪伴着她。她知道他不会再回到她这里来了,今晚不会来,也许今后任何一个晚上也不会来。她为他的孤独、他的懊悔以及他无意义的羞耻感到抱歉。然而,她让他神魂颠倒,这一让她感受到某种内在的快乐和精神振奋,近乎骄傲。他向她索要甚少,要是他索要更多,她兴许也不会阻止他。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她有些伤感,为没有对他说出一些简单的话,不要紧,考比,别害怕,你没事的,现在一切都好了。
柴油油罐车没有在她家门外等候,她知道今夜她会寂寞。一进家门,两只饥饿的猫在脚下迎接她,蹭她的腿。她冲它们大吼,呵斥它们,对它们表现出溺爱,给它们食物,把水放进它们的喝水碗里。接着,她去了洗手间,洗了洗脸、脖子,梳了梳头。她打开电视,节目演了一半,说的是北极冰川融化以及北极生态系统的毁灭。她往一片面包上涂抹黄油,在上面铺一层奶油奶酪,切一个西红柿,做了个煎蛋卷,然后又给自己倒了杯茶。接着她坐在扶手椅里观看关于北极生态系统毁灭的电视节目,边看边啜饮香茶,几乎没有注意到她的脸颊上布满了泪水。即使她意识到了泪水,她还是继续吃喝,两眼盯着电视,只是抹了几次脸颊。泪水没有止住,可是她觉得舒服多了,她对自己说了本想对考比说的话,没关系,别害怕,你没事的,现在一切都好了。她站起身,脸上依然挂着泪,她抱起一只猫,又坐下了。差一刻十一点,她站起身,关上百叶窗,关了多数的灯。
6
考比·埃兹拉在村街上游荡。他两次经过文化厅和家人用来谋生的杂货店。他走进纪念公园,坐在被雨露打湿的椅子上。他不知道她现在怎样看待他,她为什么没抽他两个嘴巴。他突然挥手狠抽自己的脸,以致伤着了牙齿,耳朵嗡嗡直响,左眼布满血丝。耻辱犹如某种令人作呕的黏稠物质,充满了他的体内。
埃拉德和沙哈尔,两个与他年龄相仿的男孩,经过长椅,没有注意到他。他蜷缩在那里,脑袋埋在双膝之间。沙哈尔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她撒谎,连一秒钟也不会相信她了。埃拉德回答说,我是说这样的撒谎情有可原。他们继续往前走,鞋子咯吱咯吱踩在石子上。考比想,他今晚做的事永远不会被抹去。即使很多年过去,人生将其带到一个令他想象不到的地方,即使他到大城市去找妓女,像其经常想象的那样,任何东西都无法根除他今晚行为的耻辱。他本来可以和她在图书馆聊天,不去关灯,即使发狂关了灯,他本来可以利用黑暗作掩护来表达他的感情。大家都说语词是他的强项,他可以运用语词。他本来可以引用比阿里克或耶胡达·阿米亥爱情诗中的某些诗句,他本来可以坦白他本人也写诗,他本来可以背诵写她的一首诗。另一方面,他想,她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责任,因为整个晚上她对他的行为就像一个老妇人对待孩子,或者老师对待一个小学生。她假装我没来由地在邮局对面等她,和她一起去图书馆。实际上她对情况了如指掌,只是装模作样,免得伤害我的感情。如果她不这样做就好了,如果她问一问我的感情就好了,尽管可能有些尴尬。如果我有胆量当面告诉她,她这样的人没理由追随一个柴油油罐车司机的。你和我情投意合,你深知这一点。我比你晚出生十五年,但我还是爱上了你,这一点无法改变。现在事情发生了,一切都失去了,永远失去了。事实上,我的所为什么也改变不了,因为其结果从开始就已经注定。我们没有机会,你我都没有,没有一丝希望。也许(他认为)等我服完兵役后,我自己要考取驾照,去开柴油油罐车。
他从长椅上起身,走过纪念公园。拖鞋下的沙石小路咯吱咯吱作响。一只夜鸟发出刺耳的叫声,远处村边一只狗不停地叫唤。他从午饭时分就什么也没吃,他感到又渴又饿,但一想到家,想到父母和姐妹们也许正痴迷在在吱吱哇哇的电视机前,他就泄了气。真的,如果他回到家,谁也不会和他说什么,谁也不会问什么;他会从冰箱里抓些凉东西吃,一个人宅在自己的房间内。可是在他的房间里,废弃了的鱼缸里漂了一条死鱼,那条鱼一星期前就死了,还有他的床垫脏乎乎的,他在那里做什么呢?最好待在外面,也许整夜都在空荡荡的大街上逛荡。也许最好回到那条长椅上,躺在上面,睡到天明,没有梦。
他突然产生了去她家的念头:要是柴油油罐车停在外面,他就爬上去往里面扔一根火柴,于是一切会炸得四分五裂,永永远远。他在衣兜里找火柴,他知道他没有。接着他不由自主地来到由三条水泥支柱支撑的水塔。他决定爬上水塔,这样离正在东边山丘上移动的半月会近些。铁梯的横挡冰冷而潮湿,他迅速地爬上去,很快发现自己到了铁塔塔顶。这里有一个“独立战争”时期的老观察哨,还有破烂的沙袋和观察孔。他走进观察台,透过一个观察孔向外观望。那里有股陈腐的尿臊味儿。夜晚在他面前延伸,变得广袤、空旷。天空明亮,繁星闪烁,相互之间形同陌路,星星与自己也形同陌路。黑暗深处传来间隔短暂的枪声,那枪声显得沉闷。村民住房的窗户里仍然有灯光,偶尔他也可以从敞开的窗户里看见电视机屏幕闪动着蓝光。两辆小车从脚下的藤蔓街驶过,车前灯把黑漆漆的一排柏树照亮。考比寻找着她家的窗户,因为他无法确定,故而选定集中在一个方向多多少少正确的窗户,决定那就是她家的窗子。窗帘垂下,灯光昏黄。他知道,从现在起,他和她在大街上擦肩而过时会形同陌路。他再也不敢向她说一个字。她也许会躲避他。如果有朝一日他不得不去邮局办事,她会从护栏后面的柜台里抬起头,声音平淡地说,好的,您有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