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堂散记
商 震
146
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也拿到了《诗刊》编辑赵四翻译的《萨拉蒙诗选》。过去曾零散地读过一些萨拉蒙的诗,印象不深。只觉得萨拉蒙是一位很注重意趣的诗人,在东欧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当萨拉蒙离开我们时,知道再也读不到他的新作了,才开始重视手中的这本《萨拉蒙诗选》。我在问自己:为什么其人已去才想起细读?这很像中国的一句土谚:活着不孝,死了乱叫。
用两天的时间把《萨拉蒙诗选》读完,对这位东欧诗人有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印象,也修正了过去对萨拉蒙粗浅的认识。萨拉蒙是一位追求凸显个性的诗人,他的诗有许多即兴的成分,超现实的成分,部分诗歌写人与环境关系的作品却有着中庸的成分。一个出色的诗人,本来就是由复杂经验构成的,每一首诗的创作,都是对复杂经验的梳理、整合后,根据情、景、境来具体处理的。
有一节诗,被我抄到了笔记本上:
天堂里没有性,我感觉不到手,
但是所有事物和生命完美合流
它们奔突离散,职位变得甚至更为一体。
色彩蒸发,一切声响都像是眼中的海绵。
现在我知道,有时我是雄鸡,有时又是牝鹿。
我知道有子弹留在了我体内,它们正在瓦解消散。
我呼吸,多么美好。
我感觉自己正被熨烫,但全然没有灼伤。
——萨拉蒙《红色花朵》
我抄这节诗,完全是因为在阅读时与自己的心境相契合,而不是认为这是萨拉蒙诗中最出色的一首。
对一首诗的喜欢,像热爱一个人,与年龄、长相、学识、地位、财富无关。能与自己的心气相通,与心境契合就好。为其他附着的条件去喜欢,都不是爱。
诗是用词语构成的,但我读不到萨拉蒙的词语。我读到的是翻译赵四提供的汉语。我不想纠结诗可译不可译的问题,想说:译诗不可以去本土化。
我的小女儿在四川长大,吃惯了川菜。时常馋了,就在北京到处找川菜吃。但吃过后,都觉得不正宗、不过瘾。她问为什么?我说:川菜到北京,就必须有北京特色,让北京人接受,才会有市场。这就叫:本土化。于是她实在馋得无奈了,就跑回四川去吃几天。
我们读的译诗是汉语的,为了让更多读者读出译诗之好,就要尊重汉语的习惯。语言句式的结构、用词是汉语的,有些抒情手段也是汉语的,但不能完全去掉原创的原汁原味,而成本土作品。当年,有好事者把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译成五言押韵的类格律诗,结果是:我们既看不到波德莱尔,也读不到好诗。
负责任地说,赵四译的《萨拉蒙诗选》是很好的。所谓好,那就是:在译成汉语的诗歌背后我看到了萨拉蒙的形象,感受到了萨拉蒙的美学追求,甚至能看到他说话时的口型与语速。
翻译作品,就是土洋结合的产物。译作,一定要有翻译家的再创作。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有一批诗人的作品被誉为“翻译体”。就是一些人读了太多的译作,并尽量让自己的作品习洋去土。甚至想,最好能写得直接是译作。写作时,从结构到用词都模仿“洋话”,结果只是外在的建筑像“洋”体,而内核不土不洋混乱不堪。不管是喝羊奶长大的还是喝本土奶长大的,只要说中国话,就得尊重中国话的习惯,否则就是疯人呓语痴人说梦。读者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辨析能力是很快的,靠披洋旗做虎皮是蒙混不了几天的。失去读者,作品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好在现在这种现象近乎绝迹。
嗨,说萨拉蒙,咋把话题扯出这么远。
147
因要随中国作协组织的作家团去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访问,而且主要是诗歌交流,我就觉得该备备课了。当代的塞尔维亚诗人我知之甚少。记得有一年在“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看到过一位塞尔维亚的诗人,叫什么名字也忘了。临行时,我们在作协集合,我问谁知道塞尔维亚的诗人,作协外联部的处长吴欣蔚告诉我一串名字,并说她译过一本塞尔维亚诗人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维奇的诗集叫《红山之鸟》。我一下放心了,有诗集译本,就不愁交流了。但同时我也在自责,对东欧诗人了解得太少了,平时咋就没多留心读读呢。
这本诗集译本不厚。上了飞机,坐定,就开始阅读。这本诗集,同样是很好的译本。我认真地读,并边读边想,到了塞尔维亚该怎样交流。真是急用现读,有现买现卖之嫌。不过,我对诗歌的阅读一向很自信。在这本《红山之鸟》中,我还是找到了与当代汉语新诗的相同与差异。当然是诗人生存状态与文本之间的相同与差异。
《红山之鸟》的扉页上有作者照片,我仔细看,似乎回忆出在青海见到他的样子。
这位叫德拉根的塞尔维亚诗人,很智慧,真性情,诗歌的内容也很丰富,略显理性,是一位追求意义的诗人。同时,我也看到他的生活环境与我国诗人的生活环境大致相同。当然了,我所看到的语言是翻译吴欣蔚根据原意重新组织的现代汉语。
他的两首诗,我很感兴趣,与中国当代的优秀诗歌没什么差异。我拿出笔记本就抄录下来:
保守秘密
让我们自由地迈向未来,
但要保守秘密。
不是美好的幻想,
也不是残酷的言语。
没有什么可以拭去就在唇边的名字。
那未写完的书想要向这个世界昭示什么?
被遗忘的快乐是怎样的伟大?
不管希望如何飘渺,
总胜过没有回头路,
深邃是一首未完成的诗所用去的时间。
——德拉根《保守秘密》
如果不注明这是塞尔维亚诗人德拉根写的,我一定相信是当代中国诗人写的。我也当然地相信翻译吴欣蔚是忠实原意而直译到汉语来的。
这首诗对我的触动很大,丰富、灵动、通透,生命的状态、情感的坚韧都表现得几近完美,是我想写却一直没写出来的诗。我的思绪随着飞机摇摇晃晃,心里也在想一个名字、一个秘密、一首诗。
就这一首诗,我已准备好了与德拉根先生的交流话题。
还有一首很短的诗,也被我抄录到笔记本上。
我的伤逝
我的伤逝广泛而警惕地存在着,
那无法掌握的秘密
囚禁于朦胧清晨里的露珠中。
我愕然伫立在那扇从未开启的门旁。
上帝,当您让我堕入此途,
难道这就是您赐予我的一切?
——德拉根《我的伤逝》
这首诗,虽然稍嫌理性,但留下的可阐释空间是非常大的。我抄录完,心里已经升起敬意。
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后,我们团的第一站,就是去伊沃·安德里奇基金会。安德里奇是前南斯拉夫作家,1961年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安德里奇没有后人,去世前就设立了这个基金会。现在这个基金会负责处理安德里奇的版权等事宜。这个基金会的负责人就是诗人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维奇。
德拉根很高兴地接待我们。我们坐下来后寒暄了一些客气话,然后他就以一个安德里奇基金会负责人的口吻和我们谈安德里奇版权的出售和翻译的情况,还提到了中国的一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安德里奇的作品,也没和他们签过约,纯属盗版,并委托我们的团长阎晶明先生帮着查查。并说:稿费不要了,样书送来就行。
没有谈诗歌。他只说了这次中国诗人来交流的诗作是他译成塞尔维亚文的。我们去之前,先把诗作译成英语,他再从英语译成塞语。我不知道,一首汉语诗歌转译两次后会成为什么样子,嗨,反正什么样子也得接受。最后,他委托我们代问他在中国认识的两位朋友好,这两位是吉狄马加和吴欣蔚。
第二天,我们到塞尔维亚作协开诗歌朗诵会,我读的是汉语,塞尔维亚国家作协主席读我的诗歌,用的就是德拉根翻译的塞语。我听翻译说,德拉根先生把我的诗译得不错。台下坐着的听众的眼神和掌声给了我一定的信心,但我知道有礼貌的成分也有诗歌朗诵的效果。
期待和德拉根先生交流诗歌,因行程安排得很紧,终于没能实现。好在我们都互相读了作品,也算有了单边交流。
没见到德拉根先生之前,我用他的诗歌来猜测他的形象,见面后,我在猜想他是在什么时间和状态下写的诗歌。我的结论是,用诗歌来给诗人画像,差异一定是很大的。
和德拉根先生见了两次面,说过的几句话大多是寒暄。他的面容可能我很快就会忘记,他的诗歌,我会永远记得。
148
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进行文学交流,我并不兴奋。因为我对那一带地区的文学状况知之甚少,也就是没读过几个前南斯拉夫的作家诗人的作品。互不知彼,如何交流。但这是一次以诗歌为主的文学活动,我又没有推却的充足理由,就答应了。
6日,北京的午夜起飞,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转机才能到达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北京到贝尔格莱德竟没有直飞?我问:为什么?有说贝尔格莱德机场小的,有说航线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些原因都站不住脚,一定有我们百姓所不知道的秘密。到贝尔格莱德是上午十点,依然是6号的十点。有七个小时被地球的自传公转给吞噬了。也好,我们消耗了两个6号。
贝尔格莱德国际机场和北京的长途汽车站的规模设施差不多。
出机场,我们来到一家咖啡厅打尖休息。这家咖啡厅门框上有一个标牌,上面印着大红色的“?”,一问才知道这家咖啡厅就叫“?”。 这个的名字很有意思,“?”。我们对这个名字都很感兴趣,问翻译乌拉迪米尔。乌拉迪米尔是个小伙子,在中国语言大学学习过一年,汉语很好,和我们交流没有丝毫的障碍。他说:这家咖啡厅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他的对面就是东正教最大的教堂圣萨瓦教堂,侧后面是前南斯拉夫公国的王宫,这家咖啡厅开张时就不知道该起个什么名字,不知是谁说,就叫“?”吧,于是这家“?”咖啡厅就诞生了。
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向窗外张望。天是阴郁的,街上行人很少。偶尔走来几个人也是低着头不紧不慢地踱步,让我们既看到他们的悠闲也看到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东欧人的闲散,我是有过耳闻的,今日一见,果然如是。
我又开始琢磨这家咖啡厅的“?”了,问什么,问谁!咖啡厅的门很低,进来出去都要低头,都要把自己的腰身弯成问号。因为我们预定的酒店要下午才能入住,所以,这个上午就得泡在这家“?”里。我拿出笔和本,开始用诗的形式记录此时对“?”的感受。虽然有点酸劲,但也是习惯。
?
这个符号藏有秘密
用左眼看是淋漓的鲜血
右眼看有滚烫的吻
这是一家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咖啡馆的名字
咖啡馆只有三十平米
它正面对着贝尔格莱德最大的东正教堂
背面是16世纪南斯拉夫公国的王宫
几经战火和多少代王权更替
教堂无损王宫无损咖啡馆也无损
咖啡馆弱小
问号却穿透了时空
咖啡馆的门框很低
出出进进的人
都要把自己弯成问号
问着进去问着出来
什么人起的名字
把人的生活状态做了咖啡馆的招牌
葡萄酒和咖啡不能把问号拉直
王宫和教堂呢
我在这家咖啡馆里
只喝了一杯咖啡
问号就在心里动起来
诗写完,合上笔记本,大家就去往酒店了。路过一座桥,翻译说:“下面是萨瓦河,下游不远,萨瓦河就与多瑙河汇合了,萨瓦河就在贝尔格莱德结束了。”我们大家对萨瓦河知道得不多,对多瑙河的记忆多来自电影。但在电影里看到的多瑙河不是贝尔格莱德这一段。前南斯拉夫的电影看过两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那是少年的记忆。《桥》的主题歌《啊,朋友再见》,在中国流行了几十年。
贝尔格莱德这座城市不大,规模、占地、建筑都无法和中国的中等城市比。很快我们就到了酒店。
塞尔维亚之旅,就算正式开始。
149
我们入住的酒店,名字叫“zira”,据说很像英语中“零”的发音。酒店的斜对面是一座花园似的处所,我问翻译,那是什么所在?乌拉迪米尔说:那是一座公墓。哦!住在零里,对面50米就是公墓,这是生与死的距离?我又开始冒酸水了。进房间稍加整肃,就出发公干。在汽车上我拿出笔记本,草草写下几行字。
距 离
住进贝尔格莱德的宾馆
宾馆的名字叫“zira”
据说很像英语中的“零”
我们住在“零”里?
我不断地翻检读过的哲学句子
宾馆的斜对面
有一座绿树花草掩映的花园
我问翻译:那是什么地方?
翻译说:那是一座公墓
并补充说:距宾馆50米
50米!
是隐喻还是规定
是生与死的距离
还是零到墓地的距离
150
塞尔维亚曾是土耳其的占领地,卡拉梅格丹城堡是塞尔维亚最古老的城堡,也是贝尔格莱德这座城市的起始城,城堡现在还保留着原貌,比如还有伊斯坦布尔门等。城堡的修补痕迹就是历史的痕迹。站在城堡的另一端,就看到了萨瓦河与多瑙河的汇合。一条河流结束使命,另一条河流壮大起来,河流在活生生地演说人类历史的进程。
卡拉梅格丹城堡的外面是个很大的广场,绿树掩映,矗立有许多雕像。我问乌拉迪米尔,这都是谁的雕像?乌拉说:这里就是诗人广场,这些雕像都是过去的诗人作家,有些诗人作家活着时并不是很有名气,也未必有什么成就,但当他们去世后,人民还是要给他树个雕像。我愣了一下,接着就对这些雕像送去崇敬的目光,对这个民族致以崇高的敬礼,当然,也有慨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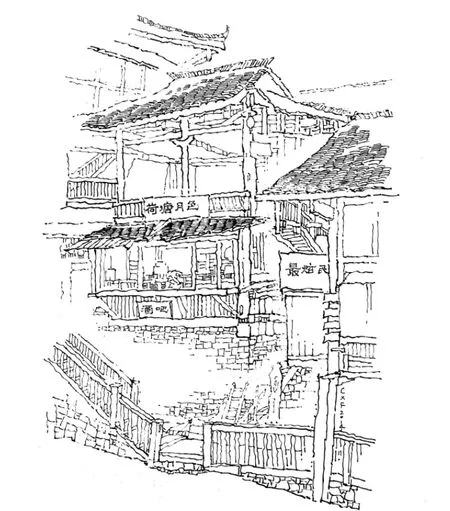
塞尔维亚全国仅有八万多平方公里,贝尔格莱德占地三百多平方公里,这个诗人广场占地两平方公里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对诗人作家的热爱、尊重就不必多说了吧。
诗人广场边有一家咖啡馆,我踱了进去,屋里有一个很大的书架,书、报、刊都有,而我此时是目不识丁的。有两个年轻人拿着一本书在讨论着什么,我稍走近一点,看到他们拿着的应该是一本诗集。我无法告诉他们,我也是一位诗人,我也想参与他们的讨论。他们也发现我在看他们,他们的眼中也认不出我是诗人,并且眼中充满警惕。为了不让他们捂着钱包奔跑或不让他们报警,我自觉地走了出来。如果他们是诗人,也只能是相逢不相识啊!
天空下着小雨,鸽子和麻雀在我们的脚前放松地走来走去。据说麻雀是贝尔格莱德的市鸟,还做过一次大型国际运动会的吉祥物。哦,麻雀。适应环境的能力强,生命力旺盛,繁殖能力强。
应该向麻雀学习,我说的是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