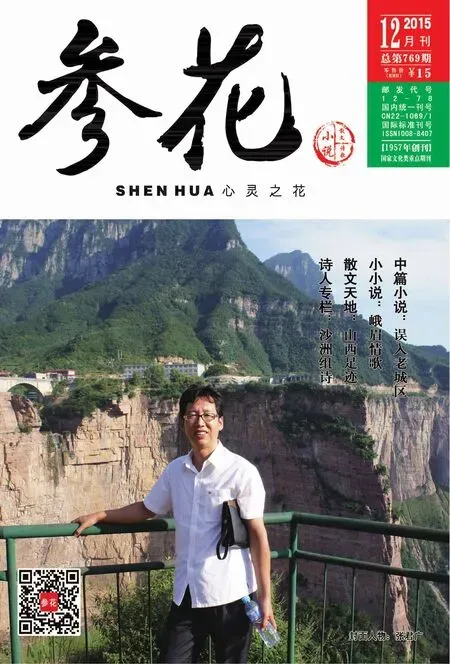纯粹精神象喻及中国现代文学诗化叙事最初的发轫
摘要:从纯粹精神及其象喻的角度,内在地定义现代文学的诗化叙事形态。西方传统的纯粹精神象喻指向命运或是彼岸的超然存在;中国传统的纯粹精神却是此岸和入世的,它在发轫之初体现为生命模式和意象/自然模式。
关键词:纯粹精神象喻 生命模式 意象模式 伦理向度
鲁迅先生写于1922年的《社戏》可看作中国现代文学诗化叙事的发轫之作,在整个现代文学诗化小说的叙事模式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从《社戏》出发,可由此发掘现代文学诗化叙事在首创之初,所具有的一些内生性特点,并由此启发后来的作家在这种形式的叙事中,可能具有的一些共同性。
一、纯粹精神象喻
诗化叙事或者诗化小说是一种美学风格的表述,这个表述也是现象性的。为了进一步深入进行本体论的思考,笔者曾在相关文章中,将类似于这种灵性觉醒的瞬间,称之为纯粹精神及纯粹精神的展现。具体来说,就是生命中一瞬间的直觉,超脱狭窄的自我的有限性,直接关涉到整体的时间、历史和宇宙。任何一个具有直觉体验的人都了解这种瞬间,尽管从本体论上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建构,才能从根本上明确其基础。纯粹精神理论说明了意象为何存在:正是在纯粹精神向外投射的过程中,意象使其显性了,或者说自然或意象成为其象喻。自然本无一物,自然精神也并非超然自在、运行大化的实体,正是人的纯粹精神的投射,使其渡入了精神性的言说范畴,而这一切尽在心智之中。
西方传统中的纯粹精神往往系于绝对化、超然化的命运或宗教。古希腊时期的悲剧即是明证,“悲剧是与古希腊人的命运及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命运是悲剧意象世界的意蕴的核心。” [1]17另一方面,西方人的纯粹精神要么直接在天国和基督教的灵性生活中找到象喻,要么委身于崇高的情感,而“崇高是希伯莱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所培育出来的审美形态。神是崇高的、最纯粹、最原始的形式。哥特式教堂是崇高的典型代表”[1]17。
有趣的是,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传统却完全不同。西方的纯粹精神象喻指向超然形态;中国的纯粹精神也是超然的(正如此概念所指明的),但其象喻模式却是此岸的、入世的。在《社戏》中,这一象喻指向了两种模式:生命模式和意象/自然模式。这也不由得令人深思:中国传统中的纯粹精神并非缺席,但其象喻模式无论是意象还是特定的生命形态,都被放置于一个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感知系统中,不像西方的基督教无论教义还是世俗的教会、教堂系统所具有的普世性。很明显,这就堵塞了中国式的超然纯粹精神形态向一般社会的普遍渗透。因为意象模式是一种美学模式,需要对象首先是半个诗人,且不像宗教教义传播的那样具有可操作性。基督教历史上有不少不远万里,将耶稣福音带入广袤世界某个极为陌生偏僻的角落的传教士。中国的意象式的超然形态能够想象吗?虽然美学形态和宗教信仰具有某种同构性,但缺了一个集约化、以人的面貌出现的神,以及教义、教会系统,结果就大为不同了。上帝世界的世俗形式很平白,眼睛看得到,不需要想象力,连上帝的天国都有可视性。对普通人而言,在信仰的事情上需要的是克尔凯郭尔所谓“主体性的抉择”。
这个纯粹精神象喻的出现,在《社戏》中还有一个极具中国文化特点的前提:伦理亲和的有情世界。这个世界值得寻味的是,这是一个和作者鲁迅所处的那个现代性时间毫无关系的世界。
二、伦理亲和的有情世界
“我们鲁镇”开启了一个神话叙事。“我们”的话语的出现拉近了距离,将鲁镇这一社会性的场所内心化了,甚至鲁镇本身也意象化了。鲁镇成了某种共同体,将儒家的伦理性的约束放开,“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尔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少少,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几不识字。”耿占春先生在提到乔伊斯的写作时说,“在乔伊斯的著作中,神话化诗学被用作克服生活世界的支离破碎和杂乱无章的形式化功能”[2]349,那个由高脚窄凳、胖绅士所象征的挤压的世界——京城,正在被鲁镇的神话叙事所克服。
宗教仪典与节日赋予鲁镇伦理性与时间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扫墓、归省、社戏都有仪典和节日的双重性,强调的是人神、人伦关系的存续。和西方的纪念已故亲人不同,祖宗是人伦——宗教关系的一体二位。对于鲁镇那些活动着的人物来说,这三者体现的都是一种儒家式的人的位置和身份的适宜性,兼顾人神,实际上也把人的位置提升了,由此取得人和社会整体的和谐。从节日的角度来讲,“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没有节日就没有时间……所以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假如祭司不于每日的清晨执掌火祭,那么太阳就不会升起”[2]275。在人类学意义上,时间是与祭献活动一起诞生的,而且祭献活动“它切断了世俗时间,并使其向神圣时间转化”[2]275。对于祖宗或祖先来说,“古列维奇写道:‘祖先和他们活着的子孙存在于两种不同的时间体系中。然而,仪式和节日,构成了连接这两种不同时间感觉,即两种不同的理解现实的纽带。因而在人类意识中,线性时间并不居支配地位;它从属于对生命现象的一种循环感觉,从属于对世界的神话想象。”[2]276从《社戏》的时间意识来看,它体现出的至少是对现代性一种疑惑。
三、象喻的双重模式
第一,纯粹精神象喻的生命模式。这种生命模式指的是“童年”这一特殊的生命形态。童年的生命形态在叙事中并非还原本然,而是经过成年视角的重构的,它的呈现属于纯粹精神的一个象喻过程。这种象喻在萧红的《呼兰河传》里表现得最为直接。在后花园里,和祖父在一起的时候,通过童年生命形态的叙事,强烈地表现了存在的觉醒、本真的回归。在《社戏》中,则集中于表现人性的淳朴天真状态,以及游戏的隐喻。纯粹精神的超我性和童真的无私有天然同构性,这当然是象喻的基础。“我们”不仅每天玩着钓虾这样的游戏,而且《社戏》整体就像是一个游戏的隐喻。钓虾是游戏,划船是游戏,看戏是游戏,吃罗汉豆是游戏——童年生命的本质就是游戏。生命就是非功利、非目的性的游戏,没有什么比这种想象更为纯粹的了,因此纯粹精神直观化为这种象喻。
第二,纯粹精神象喻的意象。古典诗歌就是精神上不断的意象显性。在《社戏》中,它通过诗情的多重镜像显现。这种镜像因为将音、色、形融为一体,因为感觉层次的敏锐和丰富,更因为纯粹精神的强度,而具有强烈的抒情魅力。这种镜像,或者是体现为一个“深度瞬间”的“静美的迷失”,“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婉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或者是最初幻象重现——感受的深度改变了时间的线性关系,“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或者是童话叙事,“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
写于1921年的《故乡》,借助童年叙事的对比,最终体现的是绝望中的肯定的担负,对历史时间的承担的决心。《社戏》却相反,体现了一种对历史进程、现代性时间的深刻的疑惑。在伦理向度方面,1932年郁达夫的《迟桂花》,1934年沈从文的《边城》都体现出了这种偏好,这将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诗化叙事脉络的一个前提。
参考文献:
[1]叶朗.美在意象——美学基本原理提要[J].北京大学学报,2009,46(03).
[2]耿占春.叙事美学[M].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郑文浩,男,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