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粮
刘万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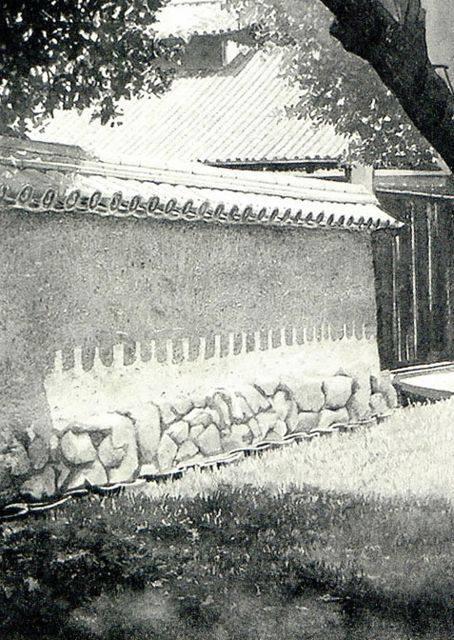
1
村妇三月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时隔多年后自己会再次和儿子薛顺娃同坐在奔驰的列车上,而且是进京的直快列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秋那个晴朗的早晨,从省城兰州开往首都北京方面去的绿色快客列车徐徐停靠在西塬车站,顺娃紧紧牵着娘的手踏进了六号车厢。娘儿俩毫不费劲就找到了他们的座位。三月刚要起身朝行李架上搁行李,却被儿子制止了,顺娃说:“娘,还是我来吧。”说着,顺娃就脱掉黑色条绒布鞋站到座椅上去,把行李稳稳当当地架在了上面。搁好行李,顺娃坐在娘对面靠窗自己的座位上。顺娃从随身带着的包里掏出几颗鲜红的楸子果递到三月面前,说:“娘,吃楸子吧,临出门时我从咱家楸子树上摘的,新鲜着哩。”三月看着儿子递到她面前的鲜红的楸子果,说:“我顺吃吧,娘这会儿还不想吃哩。”听着娘儿俩的对话,坐在邻座上的一位妇女跟三月说:“你儿子真懂事呀,大小伙子了你听叫娘还叫得那么甜,肯定是个孝顺的孩子!”三月甜甜地笑了笑说:“我顺可孝顺着啦!他最懂得疼娘了!”邻座妇女又问:“你们娘儿俩这是出远门去吧?”三月的眼里闪着按捺不住地笑,说:“我顺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我要送他去入学。”那妇女吃惊地瞪圆了眼睛看着顺娃,说:“啧啧,真是想不到哇,孝顺的孩子学习竟也这么好!妹子你真是好福气啦,养了这么有出息的儿子!真是让人羡慕死了!”听了邻座妇女的话,三月的脸颊一下红扑扑的,她和顺娃同时腼腆而会心地笑了。
说话间,列车已经驶离了西塬车站向着京城方向行进。三月和顺娃便不约而同地将脸转向了窗外,窗外路基两旁的山塬、河流、村庄、树木纷纷向后面倒去。此刻,在列车咣当当咣当当节律铿锵的行进声中,三月的心中油然涌起了强烈而难言的感慨,多年前她去陕西背粮的那一幕往事再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2
一九七六年的一个春日,在陇海铁路线陕西省境内的一个普通小站上。一列冗长的货车悄无声息地停靠着。从远处看,它仿佛一条沉沉睡去的黑色巨蟒。黑色巨蟒的头朝着西北方向,不知是要去甘肃、青海、宁夏或是新疆。
小站上一派寂静,让人极易想到夜间野地里的某处坟茔。不过,隔一段时间,就会从站房里闪出五、六个身穿草绿色军便服,左臂带着红袖章的“棒棒队员”的身影。他们依次在站台、铁道、列车边晃来晃去地巡逻,严密监视着小站上的一切动静。
少妇三月黄鼠似的从小站斜对面一个塌废的窑洞里伸出脑袋来,向小站上探了探,只见几个“棒棒队员”正一节一节挨个查看着车厢,便赶紧缩回了身子。她重新坐在了身边的半口袋粮食上。他们查得好紧啊,她想。口袋是用胡麻毛线织成的,又沉又硬,已经被磨损得光秃秃的发亮,里面装着八十多斤玉米。此刻,三月是真正发愁了,想,今天麻缠透了,极有走不脱的危险哩。她似乎听见自己的喉咙里挤出一声无望的叹息。馍袋里的馍早已倒腾空了,连一点渣渣都没剩下。那些馍还是她从粮食主人那儿讨的哩。说起来人家老陕们还是挺不错的,同情她一个女人家孤身出门在外不容易,当她红着脸说出自己想讨点干粮路上吃的意思时,主人就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给她装了满满一袋子馍。“我娃,带上,带上,出门人嘛,万万不能饿着肚子呦。”主人帮她打点好了口袋,一直把她送到了庄口的路上。馍却被她两天时间里就吃完了。眼下,瘪塌塌的馍袋就被她绾在粮食口袋的绳子上,无声地敞着口子,像一张沮丧而饥饿的嘴巴。忽然,三月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咕咕地叫了几声,像是窥透了主人心里的隐秘一样。三月就捂紧了肚子,肚子不叫了,她脸上绽出一缕无声的苦笑。过一会儿,肚子又咕咕咕地叫了起来,如同一只不知趣的蛤蟆。无奈之下,三月便打开粮食口袋,抓出一大把金灿灿的玉米来。她将玉米喂到嘴里咯嘣咯嘣地咀嚼起来,很快,一股玉米特有的清香味儿在口腔里迅速弥漫开来。直到此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饿了。她一口气吃下了三大把玉米,才觉出有一股精气神在血液里涌荡。五谷是人的精神啊。老人们说得不错。她想。
安稳了肚子,三月就想迷糊一会儿,好觑机扒车。可怎么也睡不着,连个盹儿也打不着。她就只好斜倚在粮食口袋上盯着窑洞门口银灰色的蛛网出神。那里有一只黑色的大蜘蛛正在不辞辛劳地织网。
三月的家在甘肃中部,在一条名叫关川河的河岸边的黄土褶皱里。那里的太阳似乎比别处的毒,一年四季很少见雨星子。站在家乡的梁峁上,放眼望去,漫塬上光秃秃的,就像无数和尚的头。河里呢,除了夏季发几次洪水以外,其余时间就只有一线若断若续的咸流了。这几年,陇中连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山民们人心惶惶,纷纷外出去讨生活。有上新疆的,有下四川的,也有有去宁夏、内蒙的,而更多的是去陕西背粮。
记得两年前刚过门的第二个晚上,三月就有点沉不住气了。三月对男人说,天旱得快要着火了,不想想办法这春荒怎么熬呀。男人却躺在那儿不吭声。看着两人瘪塌塌的被窝,三月又说,你们家吹吹打打连哄带骗地把人家糊弄来就是让饿肚子的啊。男人还是没吭声,却紧紧地搂住了她,拿眼神向三月暗示男人的激情。三月就有点失望,制止了男人的激情,说,五谷的事情还没着落哩,咋就尽想着六谷的事呀,怀了娃看你咋养活呢?听了三月的话,男人一下子就蔫了。是该想想办法了,只听男人小声嘀咕道。不一会儿,婚床上就响起了男人浑浊的拉鼾声。
可是天亮后三月就发现男人不见了。
公公说儿子夜里扒火车去陕西背粮了。
那次男人果然从陕西背来了近二百斤玉米。这些玉米帮衬着一家人度过了春荒,熬过了大半年的苦焦日月。男人当时就显得很得意,一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的样子。于是,他就再一次作别新婚的媳妇下陕西去背粮了。男人走后,三月天天掐着指头算日子,眼巴巴地瞅着太阳朝升夕沉,盼着自家男人的归来,也盼着那金灿灿的玉米的出现。那金灿灿的玉米多诱人呀!远要比政府救济来的薯干片碾成的“薯面”强多了。政府救济来的薯干片头几顿吃还凑合,在锅里煮了,吃起来有点儿涩涩的甜味,但愈吃愈腻,直至难以下咽。而薯干面擀下的饭、烙下的馍简直就黑得像驴粪蛋。村里就有人把薯面馍戏谑地称作“黑团长”。薯干面吃到后来竟吃得塬上人口干喉涩肚子胀,大人娃娃整天价蔫不拉叽打不起精神来。但是,即便是这薯干片吧,也极其有限,有些成分大点的家庭还得不到哩。社员们依然难躲避饥荒的威胁。人们开始偷偷地想办法了。有人就摸到了邻省陕西。那里有肥沃的渭河平原,出产粮食。关川河两岸的农民们偷偷地揣上几块钱,或者背上一口袋化肥,扒上陇海线东去的火车,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陕西地界儿。来到渭北平原,悄悄找个村庄溜进去,随便来到某一家就可以背上所需要的粮食。到了人家屋里,甘肃客们从身上摸出一叠带着体温的花花绿绿的零碎票子,或者从肩上卸下一蛇皮袋兰州生产的化肥:“老哥,背你半口袋粮食。”“行咧。行咧。”主人答应着,露出一脸的笑意。老陕们那时候粮食稍微宽裕些,麦子舍不得出手,就给你玉米吧。“玉米就玉米,行得很行得很哩。玉米才是庄稼人的粮食,比麦子更能养活人呢。”甘肃客们大多都背的是玉米,他们叫苞谷。于是,粮食就这样背上了。
可是,三月的男人第二趟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两个月后的某一天,村子里忽然来了两个铁路公安,铁路公安说三月的男人搞投机倒把,扒火车时被管制人员追撵而坠车身亡。三月最终连个男人的尸骨都没有见着。事隔多年后,她才打听到当时铁路上的人是按盲流人员草草把她男人的尸体就地掩埋了,后来连个葬身之地都找不着了。三月当下就悔青了肠子。恨自己不该从新婚的热被窝里撵走心爱的人。我这是疯了吗?她当时陷入了深深的愧疚和自责之中。
男人倒下了。就等于家里的天塌了。
家里只剩下三月和年迈的公公俩人。
……捱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小站西道口那边的扬旗牌子(即信号牌)终于翘起了。死寂了大半天的黑色巨蟒忽然活了,有了动静。机车先是重重地打了两声汽笛,然后开始喷汽。机头上喷出的白色的水汽笼罩了山脚,一直被风挟卷到了三月藏身的洞口。冰冷的水雾飘落到三月的头上脸上,她接连打了两个很响的喷嚏。三月的心里狠狠地骂了句什么,然后又扑哧一声笑了。她忽然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趣事来。记得在自己十一二岁的那年头,她经常跟着父亲到铁路上去扫煤土,他们把从火车煤机头的烟囱里冒出来、又落到路基两旁的细煤末扫起来,就成了煤土。那是铁路沿线乡民们绝好的免费燃料呢。灰黑的煤末,再掺些碱红土,用水和成煤泥,打成简易煤砖,就成了乡民们人人眼羡的稀罕物。他们可以用它来烧水、做饭、取暖……那一次三月跟父亲去铁路边扫煤土时,被使坏的司机美美地喷汽耍笑了一次。当时正值腊月天气,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等火车开过去后,父女俩的衣服、头发上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壳。三月清楚地记得两个司机都很年轻(差不多二十岁左右吧),喷了他们后有一位还探出脑袋向他们扮鬼脸。当时站在父亲身边、正在啃吃一块冻馍的三月被喷急了,将手中才咬了一口的冻馍疙瘩拼命掷向司机的脑袋,岂料正好击中了那位司机娃的鼻头,殷红的鼻血瞬间就从他的鼻孔里喷了出来。机车过去了老远,三月还看见那位司机娃吃惊而尴尬的笑一直贴在僵硬的脸上。她当下就捧着肚子笑倒在路基上,全然忘记了隆冬的寒冷……平素木讷憨厚的父亲见了,也一扫裹着一身冰壳的狼狈相,站在那嘿嘿嘿直乐。唉,童年的生活固然清苦,可多么有趣呀!
夜幕降临的时候,货车开始松闸。嚯囔囔的响声自车头一直响到车尾,就像一串炸响的霹雳。站台上执勤的人员开始挥动手中的绿旗。机车又很响地打了两声汽笛。车眼看就要开了。三月遽然从窑洞里猫起身来,弓腰撅腚地背着粮袋摸到一节车厢下。她刚摸着车厢扶手要攀上去,忽听身后不远处有人喊:“抓住她!抓住她!”就见两个“棒棒队员”朝她追了过来。他们手电筒的光在三月身上撕来拽去,要把她拦住似的。三月急了,伏下身子拽着粮袋一轱辘钻到了车厢那边。瞬间,货车就开动了。三月急忙背起粮袋,瞅准一节车厢就上。然而,车厢晃动得厉害,三月脚下还没站稳,就被背上下坠的粮袋猛然向后一拽,她的上半身就悬悬地后仰在空中,背上的绳索死死地勒着她的脖子,三月呼吸都困难了。蓦然间,她看见前面路基旁的水泥杆子狰狞地向她疾速扑来。她已软得像一根面条,浑身没有了一丝儿气力。三月眼看就要被粮袋拽下车厢去了。她似乎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她甚至产生了幻觉——影影绰绰的夜影中,死鬼男人的魂灵仿佛在向她频频招手。三月听见一声艰涩而绝望的叹息从自己喉管里挤出,她悲戚地闭上了眼睛。她几乎是在晕厥中等待着自己粉身碎骨的那一刻。
就在三月彻底死心的刹那间,蓦然觉得有一只手猛猛地向上推了她一把,接着又推了她一把。蓦然,三月奇迹般地站直了身子。后来,她终于被下面的一双手帮扶着扒上了车厢。到得车厢,三月急忙甩下自己的粮食袋子,转身向下望去。这时候,她就看到了那个小小的身影和他背上的一疙瘩粮食!
那个小身影就是顺娃。当时三月急忙翻身下到悬梯上,把已经攀到车厢上的顺娃拼命地拽上了车厢。那是一张脏兮兮的稚气未脱的小男孩的脸,小脸上一双亮亮的细眼睛。看到气喘吁吁的三月时,他向她顽皮地笑了笑。三月的眼泪就出来了。她一把揽过他,撩起衣襟沾了唾沫给他擦脸,她擦去了他小脸上的煤尘。三月看出小男孩顶多也就十一二岁。就问他:“你是哪疙瘩的?”男孩答:“薛头坪的。”“喔——”三月有点儿激动,“薛头坪,薛头坪离我们那疙瘩不远呢!仅隔着一条关川河啊!”三月看见小男孩的眼睛亮了亮。她又问:“你这么小点儿人,怎么就敢跑到这老远的地方来背粮呢?”小男孩的眼睛霎时暗了下来:“爸死娘嫁人,家里只有俄(我)和瞎眼的奶奶了,俄(我)不来背谁来背?”三月听了半天无语,她心里酸酸的。她自然又想起了窝在自己心里的那些难肠事。
自从自己男人背粮路上出事以后,她只能与公公茕茕相伴。男人去时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公公脾气瞎,又是个犟板筋,一不顺心就冲她发火。还怨她命硬,剋死了男人。有一次公公竟然拿指头戳着她的眼窝凶凶地骂道:“你这个丧门星!剋夫的贱女人!上岘子的张半仙说了:男人破月破丈家,女人破月破自身。女人家啊——猪兔羊破正、虎马狗三星、蛇鸡牛四害、猴鼠龙六凶。你是属马的生在了三月,是破月哩,你当我不知道?你快快滚出这个家吧,免得剋完了我全家!”面对公公的责怨,她无言以对,只能默默饮泪罢了。但她没有走,她知道公公离不开她。老人说到底也是个苦命人,需要有人来照料他……
黑色的煤机头不断地咀嚼着空气、冒着黑烟,拖了一串长长的车厢向着西北方向急驶,路基两旁的山塬、河流、村庄、树木、炊烟纷纷向后面的黄昏里隐去。脏污的车厢里,三月搂着顺娃的头,望着远处的山影出神。她觉得这情景很特别,很亲切,就像小时候曾经看过的一部黑白老电影里的某个镜头,令她温暖,又令她伤感。这样想着,她原本抽紧的心一下子舒展了许多。“姨,你的额头渗血了!疼吗?”顺娃忽然问她。暮色里,顺娃的眼睛亮亮的,就像天幕上的两颗星子。三月这才隐隐觉得额头上真的有点疼。她才意识到刚才在小站上只顾了钻车厢,没顾及额头碰在了车帮上。三月抬起胳膊正要擦额头,顺娃却抢先了一步。只听他“嗤”地一声从自己的衣襟上撕下一块布头来,替三月擦拭了额头的血水,又从他的衣襟上拽出一绺棉花,从怀里摸出一盒火柴,将棉花燃成灰,轻轻地敷在三月的额头。三月感激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有一股晶亮的液体在她的眼眶里打旋。“今黑要不是碰上这娃,我可就死定了。”她想。三月又一次搂紧了顺娃的头。
黑色的货车喷着黑烟一直向着西北方驶进。车轮撞击着铁轨发出有节奏的钝响,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夜色彻底降临了,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四周的景物慢慢地笼进这黑色的网里而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半年之后,在一个黄叶飘零的秋日,三月拉了一辆架子车来到关川河对岸薛头坪的顺娃家。她把薛顺娃和他的瞎眼奶奶接到了自己家里,将两家人合成了一家。三月这样做时,她的“犟板筋”公公也没有反对什么,老人竟然默默地接纳了两位与自己同样命运的可怜人。三月一直没有再找男人,她一人独立支撑着这个新家。新家四口三代人,竟然生活得很安适很平静呢。不久,三月送顺娃进了村小学,让他继续读他的书……
3
这年夏末的一天,忽然从关川河村爆出一条新闻:村妇三月的儿子薛顺娃,以全县第一名的高考成绩被某大学所录取!这是关川河村,乃至全乡的第一个名牌大学录取生!整个关川河村一下子沸腾了!乡亲们足足庆贺了两天一夜。
秋天来临时,顺娃该入学了。临启程的那几天,顺娃缠着要娘亲自送自己去北京。其实,这也正是三月的一桩心愿,她便痛快地答应了儿子的请求。
这不,娘儿俩又一次坐在了急驶的列车上。当然,这一回他们坐的不再是当年那乌叽麻黑的货车,而是草绿色的快客列车。
你瞧,娘儿俩这会儿正大大方方地坐在净洁、舒适的座位上看着窗外的秋景呢!绿色的快客列车载着三月和顺娃的梦想,载着关川河人的自豪,飞驰在陇海铁路进京的途上,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快客列车向着京城欢快地驶进,驶进……
责任编辑/文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