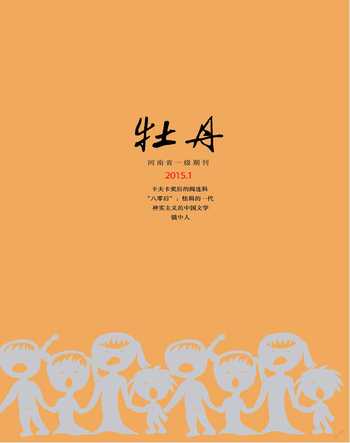神实主义的中国与文学
阎连科
1
对于读者,文学常常引领生活;对于作家,生活总是在逼迫着文学。
今天的中国,正以快马加鞭的方式,欲以用最短的时间,超越欧美二百年的历史进度。于是,一切的规则与过程,都被目的所取代。不择手段的捷径,成了发展、富裕、英雄和成功者的智慧和阶梯;权力与金钱,又合谋偷换了人们的灵魂,这就使得那块有十四亿人口的古地上,每时每天所发生的事情,都惊心动魄,嚼味无穷。它荒诞复杂,混乱无序,一切的美丑、善恶、好坏、实在与虚无、有价值和无意义,都无法评判和梳理那儿连缀的发生和存在。人类对事物的一切解说,在那儿都如一块磁铁面对土塬的无语,它有力的磁性和磁场,如一块陨石落入大海而不复存在了。
看守所中的半盆洗脸水,确实把一个人给活生生地淹死了。
春节到来时,上海的黄浦江上确实有一万多头死猪浩浩荡荡漂浮而过了。
中国某地由土葬改为火葬时,人们为了赶在火葬场开机焚烧的前一天死去而土葬,老人们确实纷纷地自觉选择自杀了。
一切都是不够真实的,违背人类常情逻辑的。可它又是日常的,每时每刻发生的,如不知怎样就质变了的水和空气样,普遍而弥漫。这是一个新的国家,也是一个旧的国家。它是极度封建专制的,却也是相当现代富有的;是极其西化的,也是固有东方的。世界在改变它,它也在改变全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全部新异就是用人们不能理喻的真实来超越和挑战人类发生与想象的底线。于是,它有了不真实的真实、不存在的存在、不可能的可能。有了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甚至也无法感受的发生规则和规律。
它有了新的逻辑和新情理。
有了一种可谓“神实”的普遍之存在。
这种神实的现实与历史、真实与发生,让中国人先是惊诧和怀疑,进而日常和习惯,最终就麻木并认同这种在世界上近乎独一无二的历史了。在全世界面对中国今天日日的奇情异事都目瞪口呆时,中国所有作家的笔和键,面对这些超越了人类历史经验的实在,都感觉到了写作面对现实的无力与无奈。世界文学中一切的流派、主义和技巧,在中国奇异的故事面前,都会发出为力的喘息和感叹。
中国的现实,在逼迫着一种新的写作。
最为不可理喻的历史与实在,在催生着一种可谓神实主义文学的产生——用最独到的文学之法,展示看不见的真实,凸显被掩盖的真实,描绘“不存在”的真实;让文学的脚步走在灵魂与精神(不是生活)的路上,去追寻那些在幽深之处引爆现实与生活的核能。
2
在我们固有的小说中,关于故事、情节、细节乃至于人的心理与言行,没有因果关系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无法存在的。这个因果之关系,以科学与逻辑的名誉,霸占了人类和宇宙的一切,其合理性的链条,如同今天的到来,是因为昨天的失去样,环环相扣,节节因果。有了阳光,也就有了万物;有了交配,也才有了孕育;有了发动机的出现,也才有了一种新的运动。因果逻辑之情理,在这儿鲜明得如一顶贵族的帽子。
在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那儿,所有的人与事物的展开和进行,都事出有因、全面完整,并必然为因果相均等。一百斤重量的原因,一定要有百斤重的结果;之后有百米尺度的所以,之前一定要有百米尺度的因为。因为与所以,可以隐藏、含蓄和不写,但决然不能不存在。这种因与果大小的完全性和一致性,可谓现实主义的“全因果”。全因果中因与果的对等性,就是故事最为上佳的逻辑性。现实主义严格按照这个对等的逻辑关系来铺陈和展开,舍此的超越或偏离,就不再是或不纯粹是现实主义了。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直到小说的最后,卡夫卡都没有告诉我们萨姆沙从现实事物和人的生理上是“为什么”、“怎么样”变为甲虫的。
果仍在,因却消失了。
——这是卡夫卡对现实主义最有力的地叛。于是,他在文学中发现(创造)了现实主义之外的“零因果”——没有因为的所以,没有条件的结果;或者是没有结果的原因(《审判》和《城堡》)。如此,荒诞产生了。一种新的写作,为文学播下了伟大、现代的粒种。
“他(墨尔基阿德斯)拽着两块铁锭挨家串户地走着,大伙儿惊异地看到铁锅、铁盆、铁钳、小铁铲纷纷从原地落下,木板因为铁钉和螺丝没命地挣脱而“嘎嘎”作响,甚至连那些遗失很久的东西,居然从人们寻找多遍的地方钻了出来。”
因为磁铁的到来和召唤,木板上的铁钉和螺丝为挣脱而做出“嘎嘎”的回应——被卡夫卡丢掉的因,在这儿又游戏、欢笑着回来了。然而回来的这个因,又和果没有那种现实主义的对等性,它是三七或四六的“半因果”。所以,当半因果统治了《百年孤独》,并或多或少总是让各种情节的关系、转换都和生活中常识性的真实逻辑相互关联时,世界向这种半因果的故事渐次发出了欢呼和尖叫,把荣誉如饥饿中的馒头样,送给了拉美和那儿的作家们。
3
神实主义被中国的现实催生后,它以怎样的因果逻辑存在呢?
到今天,中国人最终明白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大跃进”,一把劈柴和一把沙,为何就能炼出一块钢铁来;一亩地或二分田,为何能产出一万、两万斤的小麦来——原来人类最荒诞不经的中国现实与历史,总是有看不见的内真实。
内真实中总有一个或几个“内因果”。
是内因果在决定着最荒诞的现实、历史和人们,如《圣经》中的神说要有光,也就有了光;神说要有水,也就有了水;神要把白昼和黑暗分开来,也就有了白天和黑夜。而中国的现实与历史,现实中的一切荒诞、无序、混乱和不解,人心、灵魂的苦痛和纠结,都隐藏在内真实包含的因果里,当写作抓到了这个内因果——引爆现实与生活的核——神实主义的“神”,也就成为了一种在现实中看不见但在文学中却看得见的真、可存在的真。神实主义的真,不是为了证明生活中1+1确实等于2,而是为了让人们感受、感知1+1为何不等于2;B的发生,为何与A无关联;不仅为了说明人们为何相信一亩地可以产出一万到两万斤的小麦与稻子,而且还展示了亩产一万、二万斤小麦、稻子的缘由、过程和“真实”。
在《四书》那部小说中,有一位被改造的作家,为了种出亩产万斤的小麦来,他选了一块不一样的地。这块土地下埋着曾经呼风唤雨、权力无上的封建古皇帝。土地是块皇帝陵。作家就在那埋着威权皇帝的墓地上播种小麦粒,待小麦发芽需要浇水时,他浇的不是水,而是一次次地割破自己的食指,把自己的鲜血和水混在一块浇小麦,乃至于在小麦灌浆时,他把自己的动脉血管割开来,让自己的血喷向天空,和雨水一道落在麦地里。如此着,收获时他种的小麦穗就和玉米穗儿一样大,亩产就果然万斤了——人的最深处看不见的苦痛和灾难,在创造着人类的一切和可能,这就是亩产万斤的内因果。
现实主义严格遵守逻辑关系中的因果对等性。
而荒诞往往抛弃这种因果性。
魔幻又找回现实的因果来,却又不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对等之因果。
当所有的小说大抵都在这种因果逻辑中展开人和物事时,神实主义从中国现实中抓住了深藏不见的内因果,抓住了核裂变中看不见的核,至于裂变过程中怎样的荒诞、混乱和无序,不真实和无逻辑,也就可以理喻、理解了。《炸裂志》努力呈现的,就是那个促使混乱、裂变的核。在今日混乱之中国,小说一旦抓住了生活中看不见、土地中似乎也不存在的野荒之根须,至于土地和生活表面的真实怎样还有那么重要吗?《炸裂志》试图在黑暗中缉拿“最中国”的因,如画家要画出了一条河流深处看不见的河床的错落与嶙峋,在这样的境况下,谈论河水表面的平静、湍急的合理与不合理,又有什么意义呢?
神实主义,要面对的就是深水静流掩盖的河床与堤岸,要展示的是海面以下三分之二那看不见的冰山的内真实,以此来据证海面以上那三分之一人们看到的冰山为什么是这样而非那样。
神实主义不是为了主义而产生,也不产生于作者的头脑与笔端,它完全来自今日中国那让世人无法理喻的普遍怪诞中的人与物事。它不仅是一种“发现小说” 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更是今日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故事”本身最根本的存在和精神;甚至它本就不是一种文学观,而是中国现实之本身、本质和本源。
责任编辑 王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