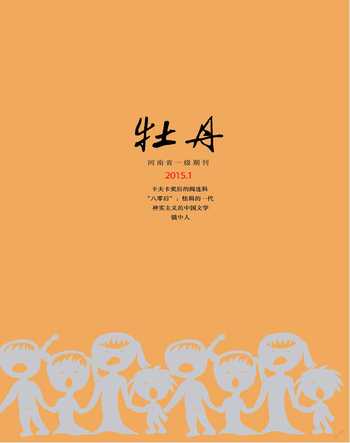冬之味
杨鹏杰
黄昏,沿着一条条渐次亮起灯盏的小街巷走进已是漫天飞雪的旧城。飘逸的雪花掺合着氤氲的晚风不时地掠过街边明清建筑的屋脊廊檐,顽皮地一会儿在你额头上稍作安代舞步的翩翩停留、一会儿又害羞地轻轻吻别你的双唇,迅速地消隐于灯光的雪莹中了。而当你还沉浸在与来自天穹的白雪仙子美丽邂逅,还没来得及欣赏冬雪尽染青城的净洁与苍茫时,一份潮热而温润的烟火味儿不知不觉已迎面扑来,似曾熟悉的味道便丝丝缕缕地钻进鼻翼、麻麻痒痒地直拂心尖……小巷转角处一个门内透着通黄灯火,门口燃着无烟煤烤炉的小饭馆,里面腾腾的热气裹挟着暄闹的人声和炖羊肉的清香,从布满油渍的帆布门帘缝隙处伴着“祝酒歌”的悠扬旋律钻将出来,随着烤炉升腾起的通红火焰,在整条小巷久久地弥漫着。于是,把持不住的怀乡忆旧的思绪,叠印着家乡——呼和浩特冬天独特的味道如纷飞炫舞的雪之哈达一样潺潺流淌进了旧日时光。
上世纪70年代的隆冬时节,呼市家家户户都有一到两个形状、个头大同小异,或是烧烟煤的铸铁炉或是专烧机制蜂窝煤的煤炉,用来取暖和做饭。每当夜幕降临,一家人围坐在冒出茵茵火苗、烧得旺而炽烈的火炉旁,吃着烩菜馒头、唠着家长里短、听着单田芳沙哑跌宕的评书,简单而惬意。而我喜欢托着下巴、歪着脑袋,暖洋洋地趴在窗台上,或是透过布满冰花的玻璃窗,傻傻地眺望外面冰封的世界,或是痴痴地端详着窗户上叠影纷呈的冰花,懵懵懂懂地欣赏着那若山若水、化入仙境的天赐之作。此刻,一份夹杂着煤烟和饭菜的暖香便久久地充盈了整个小屋。记得当年的火炉都配有导烟的炉筒,每隔十天半月还得打炉筒,就是将炉筒拆卸下来清理炉筒内壁积存的煤灰。我家的炉筒是父亲用白铁皮打制的,有七节,每节1米多长,打制炉筒可是个技术活,特别是做拐脖,没有一定的钣金技术,即便裁好的两个半拉的料也拼对不成角度合适的拐脖。我曾看着父亲灵活自如地挥舞着铁剪刀、木榔头,将一块块裁剪好的白铁皮垫在铁砧上几番折边弯扣、叮叮当当之后,滚圆修长、银光闪亮的炉筒就魔术般成型了。几节炉筒需要依次套接,套接时小头朝外,炉子和炉筒之间用拐脖连接,这样烟才会顺着炉筒一溜小跑到屋外、带着冬日里的一抹温馨融入苍茫原野。
小时候,除了喜欢围着只有十几平米大的旧屋中央那架红彤彤的炉火,还期盼着母亲的腌菜快点出缸,好顿顿吃上那让人开胃生津、垂涎欲滴的别样美食。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冬天的菜蔬基本就是土豆、白菜和萝卜。而谁家要是整个冬季总能吃上用腌制的白菜、芥菜、心里美等烹调出的酸辣入味、爽口醇香的菜肴,是很让人羡慕的。母亲常说:秋分种菜小雪腌,冬至开缸吃过年。记得每年腌菜时,母亲将买回的大白菜一颗颗晾晒、洗净后,放进干净的瓷缸里,铺一层白菜撒一层盐,直到把缸塞满,再压上一块浑圆的大石头,然后就只等着个把月后尽情享用了。腌菜时放盐很重要,盐放多了会咸得齁嗓子,放少了又会酸得呲牙咧嘴,腌菜的手法更加讲究,手法差的腌出菜来吃不了几天就软塌塌的烂了,手法好的腌出菜直到来年春天都还是嘎嘣脆。有时候母亲还会在白菜心里包裹上几粒红辣椒和鲜姜片,待腌制好后直接当做开胃小菜切盘,那黄灿灿的叶片、红艳艳的椒丝和着酸酸辣辣的香,随着一道道堪比如今山珍更地道的酸菜炖土豆、酸菜炒粉、酸菜萝卜汤……在母亲高超的烹饪技艺下隔三岔五地便端上了餐桌。悠悠晃晃间那鲜美绝伦的味道已滑过舌尖深深入喉留驻心头,成为一生一世的诱惑,化作千年的岁月沉香。
也就是这样一间虽不富裕却也充满温馨的小屋,洒满了我童年的趣事和人生的向往。如今再去回味那份腌菜的酸爽和那一膛炉火的烘烤,亦变成一道体悟秋收冬藏的生命历程。此时此刻,冬夜的飘雪依旧,七彩的霓虹仍然映照着窗棂里面所有的人间烟火,随着风尘过往在夜色璀璨中缀成深邃而空灵的别样意蕴,将家乡冬之味在心底澄清,思绪飞扬过后,凝炼成北国特有的苍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