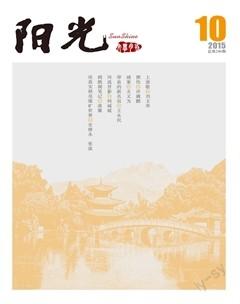鸦鹊湖笔记
油菜花
刚刚落座,从会议室的窗口望出去,一大片金黄的油菜花吸引了我们的视线。春霞手里拿着一架单反相机,提议趁人员到齐之前去看油菜花。那片油菜花原本是我嘴里喊出的,大家的目光才投向那里。我当然赞同。
路是绕的。从乡政府门前的花园通到街道,再从街道转入一条巷道。绕行到窗口所见的那片油菜地,纷纷纭纭的油菜花如一大片云朵覆盖在大地上。从镜头里看油菜花,一大片金黄里有一张明媚的脸,眼睛里有带电的光波,在花蕊上飞舞的蜜蜂围着她转一圈儿,便飞离镜头,去收集喷香的菜花蜜意去了。
很多年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近油菜花了。我站在这片云朵前,让同伴给我摁动快门。背景便是这片浩荡的金黄,远处有一两栋富裕后村民盖的小楼。我将鼻子抵近花蕊,一股蜜甜袭来,整个脑髓都被清洗如新似的。
给我们当向导的周主任,青春的气息洋溢在他脸上。他拍摄的角度很好,让油菜花和人完美地嵌入相机。仰头看见天空的白云漫过头顶,那似乎是天穹给予我们的最美奖赏。
阳光铺在大地上,让人感觉从骨血到皮肤外都是暖融融的。油菜花鲜艳、灿烂,我们的脸上染上油菜花和阳光的混合色。
来鸦鹊湖的路上,一路都有油菜花切换镜头。驻停脚步,被这片油菜花吸引成为理所当然。清新甜蜜的气息,让我一下子联想到年少时家乡的油菜花景象,我与小伙伴们在菜花地里玩耍,捉迷藏,金色的花粉沾得满头满身;在广西巴马见到的油菜花,生长在一条有着“命”字形体的河流旁,那是别一番滋味的花香……婺源的油菜花诠释了很多人对乡村的向往,那是花与民居构成的文化景观……在大地之上,还有哪一种花能超越油菜花的辽阔呢?
油菜花给鸦鹊湖涂上了一层耀目的金黄。向前走,那是花的纵深处,花遮蔽着我,整个身子沐浴在花海之中。油菜花的香气层层叠叠地包裹着我,多少往事一齐朝我袭来……
几座坟墓占据着地形,与一旁刚建起的楼房形成反差。楼房初具规模,钢筋水泥和砖块显露无遗。而坟包凸起、碑石森严处,有青草和野花相伴。
一簇萝卜花很惹眼,两个年轻人在拍摄那些花,镜头不时避开那几座墓地。我对露出地面的树根发生兴趣,树根上生长着几只褐色的木耳。放眼四望,草木开始葱郁茂盛起来。一些小花小草,相比油菜花的繁荣显得势单力薄。但它们也要分享这个季节,分享春天……
祈兴村
一个古老村落,老房子的命运要么被拆除,要么在风雨飘摇中静静等待被拆除的命运……
矗立在村中的新楼已经取代旧宅。一些即将开工的新楼正在摧毁那些有着历史记忆的老宅。而尚未拆除的老宅主人恨不得变魔术般立即拆除旧房子建造新楼房,这样在村里才不会被人小看。看见那摇摇欲坠的几栋老宅,不免让我心生不舍。老宅主人拆除那些住了半辈子的老房子,也是迫于无奈。从现实考虑,住着楼房确实有楼房的优势,干净、舒适;随着人口的增长,三代同堂已经不适宜继续在老宅挤住,在经济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亟需盖新房来改善住宿条件……可是,这种拆除,村庄的历史在灭失,心底不禁生出无限惋惜……
那些被拆除的红石屋墩、红石门槛随处可见,多半是村民拆除旧房遗弃所致。新楼都是钢筋水泥结构,这些石块失去原有的光辉,与地面废弃的砖石为伍,不失遗憾。
宽阔的地面用石块砌成一个圆圈,碾槽深陷,可以揣摩出年代的久远,那是石碾。过去没有电,便用石碾碾米,这是农耕文明的象征。
旗墩上被村人竖起铝合金的旗杆,有些生硬,过去的木制旗杆早已腐朽成泥。但旗墩的存在,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令村人自豪的过去……
我与向东脱离队伍,去寻访老宅。走近第一家老宅子的大门,遇见一个孩子挡住去路。他生着女人般的脸,但短发显示他是男性。他的衣着似乎有很长时间没有换洗,嘴里咿咿呀呀地不知道说什么,是个智障少年。我们退出来,他依旧在不停地咿咿呀呀地胡言乱语……第二家,屋里屋外收拾得很干净,看起来就是正经活命的人家。我跟一个大肚子女人说明来意,我极力赞美这栋砖木结构的老宅。一个老年女人在一旁,不置可否。我的脚跨进门槛,遇见从厨房走出来的那个男人。他言语中对我们的贸然闯入表示极大的不信任。我极力赞美这房子的好处,砖木结构,冬暖夏凉,通风透气……对主人说,这样的房子不要拆,拆掉可惜,那些楼房不如这些旧房子好……这样说着,很宽他们的心。到厨房和后院转了转出来,我拉着男主人,让向东给我们拍了张照片。主人感觉出我们的善意,这才很好地配合,还冲我露出好看的笑容。
一个老太太与三四个孩子围着一堆藜蒿在忙活。我走近前去,与老太太攀谈起来。那些青色的藜蒿产自鄱阳湖,一根根藜蒿的叶子在她们的手指运动下被剔去。藜蒿是闻名遐迩的食材,我用手机拍下了她们精心劳作的场景。老太太说,自己得了血吸虫病,也叫大肚子病,肝腹水,医治难愈……我不免产生同情之心,希望政府大力解决血吸虫病问题,使老百姓不为血吸虫病所困扰。两个女孩子很乖,帮着剔除蒿叶,但却并不是老太太的孙女。别家的孩子过来玩儿,这么卖劲地剔着蒿叶,是蒿叶的青翠吸引着她们,还是老太太为人善良吸引着她们?
旗墩、石碾、红石门槛、仅剩的老宅……勾起人们对村庄历史的追溯。一棵大樟树遮蔽着阳光,伞状的树荫下阴凉宜人。经过几百年的风雨,老樟树依旧健壮挺拔。我们在老樟树前站立一会儿,与这棵见证过村庄历史的古樟合影,也便与这个村庄的历史擦肩而过……
绿 洲
绕一个好大的弯儿,上了湖堤。在堤外是苍翠绿洲和茫茫水域,这就是鄱阳湖。
松林是鸦鹊湖的地理通,跟随他绕过菱角湖、司马咀,就像蜜蜂从这朵花飞翔到那朵花一样轻而易举。汽车丈量着大堤。堤上坑坑洼洼,刚下过雨,很多水坑,但阻止不了我们一路飙行。这一路,汽车风驰电掣,泥浆溅向两侧,车轮只管向前,向前……
终于到达一处平房处,车停下。这是农场时期遗留下的房屋,一些废弃的农机杂乱地摆放在路旁。我们朝前步行,一条土路通向大草甸。一树桃花纷纷纭纭地飘落,桃花被雨水冲到坡处,雨停后,桃花贴着水迹,现出一条桃花径。我踏着桃花小径来回走了几趟,被琳莉看见,她也要走,但高跟鞋的斜坡与路面的斜坡形成更斜的坡,她试了试不能自由行走便退回去了。
一种不知名的紫色小花极为惹眼,人们拿出相机、手机对准那些紫色小花尽情拍摄。
大草甸吸引着我们,脚步不由自主地踏上那些柔顺如发的碧草甸。我们在草甸里跳跃、奔跑,这巨毯般的草甸给我们很多想象。先是男子们在那里尽情跳跃,后来女子的加入更增添了绿草的内涵。在草甸蹚出一条路径,幸喜草色碧绿,纤尘不染。在草甸上打滚、做睡姿状,无拘无束……
翻上一个高坎,那里停着很多摩托,是附近村民在这里劳作。上了土坎,才发现那面是一道湖汊。碧水清幽,一条船靠岸。船上堆放着一袋袋的藜蒿。采集藜蒿的大多是村妇,她们在搬运这些新采的藜蒿,从船上转运到拖拉机上运回村庄。藜蒿装在编织袋里,在拖拉机斗里码成一座小山……
我问一个村妇,这些藜蒿从哪里采集来的。她手指着远处一片茫茫碧野,说,那里。
我又问藜蒿卖多少钱。她说不卖钱,拿回去分给亲戚和朋友们吃。
藜蒿是鄱阳湖的特产,是一种野生菜,炒腊肉,味道鲜美。
看见撑船的男人,我问他,能渡我们到对岸去吗?船主爽快地答应。七八个人坐上船,他很麻利地撑船、发动,很快便将我们渡到对岸。
对岸是一片更宽阔的草甸——无边无际的水乡草原。我们在草甸里展开想象,男人雄鹰展翅,女人柔曼轻舞。在碧草上,有时躺下,有时奔跑,有时静静地用鼻子去闻草甸的气息……一望无垠的碧草,勾起所有人的童心,就像孩子到了游乐场一样,玩儿得无比尽兴。
看夕阳西下,我们唤船老大渡我们回去。我拿起竹篙撑着,装模作样地俨然一个船夫。我与船夫达成默契,待到打鱼时节,我要来与他一起出湖打鱼,他欣然允诺。
真是回到了少年时啊!我在返回的路上唱歌,唱的是《红星歌》,一些人跟随我唱。他们不知道我是唱给谁听的,歌声似乎与这个场景并不契合。懂我的也许是这些绿草!
这绿洲,这草甸,这水乡大草原,真让人有些无厘头的疯狂呢!
我面朝湖泊,一路奔跑,大声喊:鄱阳湖——我来了——
炮 山
鸦鹊湖有座山叫独山,又名炮山。这个地方的山水名称极讲究,山名有将山、相山、马山、车山、炮山、卒山,水名有士湖……不知是哪位仙人下过的一盘残棋,遗弃在大地上。
大地辽阔,自然可做棋盘,山头、岛屿成为棋子,也是情理之中,但可以拿捏这些棋子的巨手绝非人类。大自然神奇,却难以超越人类的想象。人类赋予大自然许许多多传说,将山水自然变得鲜活灵动,因为传说,山水便有了灵魂,也有了与人类长相厮守的资格。
站在独山制高点,四周都在目力范围内。这几座小山,在围湖造田之前是一片岛屿。我们站在光秃秃的山顶,就像站在一只倒扣的大锅上。大家七嘴八舌,讨论着太阳的温度以及某条象征女性的曲线……有人提议在这里建一个亭子,叫“独山亭”。再有人推而论之,要红许在《信江》期刊上设“独山论坛”。真是一个好名字!我们脚下踏着的这个锅底,试想若能翻转,架起一把大火,将各种原料混合,不煮出一锅热气腾腾的好汤来才怪呢……
这山见着那山高,不远处是一座更高的山峰。我们继续攀登,发现那山长满了苍茫的山芦苇。我们的身子埋在齐腰深的山芦苇里,似乎置身塞外。大家毫无章法的议论,在山芦苇上空飘荡。我很少插话,折着这些清瘦的山芦苇,想象能扎一把笤帚,拿回去清扫那些没有来由的尘埃。
山下一水西来,这是西河。西河又名漳田河,起源于安徽池州,是鄱阳县四大水系之一。西河蜿蜒流经泥溪、沼潭、谢家滩、石门街、中馆、油憞街、银宝湖,经独山注入鄱阳湖。
站在山巅,目光投向远方。但远方之远,到底是何方?是那片浩大的湖泊还是迷迷蒙蒙的远山……或许都不是。是人心还是意念中渺茫一片的海洋……也许,远方就在每个人的内心,在目力无法到达的地方,在辽远广袤的天际……
我们另辟蹊径,朝着西河方向下山。这可难住穿高跟鞋的珺婧、子黎们,她们手牵着手,闯过一道道荆棘封锁的关卡,终于到达峡谷底的一条山径上。
山谷间是一座废弃的战备粮仓。过粮仓,在村子旁,看见一对夫妻在土地庙前烧香求拜。红许问,这附近还有一座庙吧?那男人说,有一座龙王庙。红许征询我道,去看吗?我说好啊!
男人领我们翻过一座山头,他说,刚才那座土地庙是他建的。我们现在去朝拜的龙王庙,也是他一手建造。在面朝西河的山腰,砖瓦垒建的屋子里供奉着龙王塑像。庙虽低矮,可容两三人跪拜。正应了“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庙不在大小,能保一方平安才是真神!
男人指着西河下游一处水域说,一九九八年涨洪水,那里淹死四十多个人,堤上摆满了尸体……一条破船,承载着众多的生命。洪水肆虐,龙王瞌睡间,多少人家惨遭飞来横祸,妻离子散……
离开龙王庙,独山再次擦拭我的目光。返顾静水深流的西河,冥想在历史的渊源里缓缓流淌的这道流水,我们能够做到的也仅是与它相视一笑或者沉默哀怜……唯有独山与它相依为命,遥相守望。
采藜蒿
乘船去采藜蒿,是梦境之中的事。宽阔的湖面,幽深寂静。我们的喧哗声,却超越不了柴油机推动船只的吼叫声。
船在水上飘摇,一行人在漂移的船上观赏风景。白鹭在水草里觅食,也有的在湖面上飞翔。水波荡漾,碧野连天,一幅壮阔与浩大的图册烙印在脑海。
我们行走的路线是西河汇入湖泊的路径,两岸涂抹着喜人的青翠。要说诗情画意,唯有此刻……
船老大是女子,船直行,她只须双腿夹着舵把,优哉游哉地驾驭。机船划开水面,远岸渐渐临近。
船靠岸,船妇将锚抛上岸,我们一个个跳上岸去。这便是藜蒿的生长地,青翠的藜蒿一根根从地层冒出,像诗行排列在绿洲上。我们眼睛放光,各自寻一块地方开始采集。这是一片藜蒿与青草相间的草原,青青葱葱的藜蒿,只要舍得掐,要多少便有多少。一群书生,弯下腰身,手指在藜蒿的嫩茎处掐着,一支一支青翠的茎叶,顿时在另一只手里生出一大把葱茏来。
藜蒿的别名很多,不同地域叫法也不尽相同。芦蒿、香艾蒿、艾蒿、水艾、小艾、水蒿、狭叶蒿等,每一个名字喊出口,似乎都是晶晶莹莹的女子。藜蒿为菊科蒿,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和嫩茎可供食用,营养丰富,是餐桌上一道极鲜美的菜肴。“鄱阳湖中草,南昌盘里菜”,此句道出这佳肴是由南昌人吃出来的。藜蒿生于荒滩、荒坡或岸边、沟边及田间。此时正值早春,是盛产藜蒿的季节。采集藜蒿,于我而言,与采集诗句没有什么分别,采集藜蒿就是采集诗句。
所有人都展开了藜蒿这道美味佳肴的想象,像采集宋词一样采集着藜蒿。唯独明然游手好闲,充当摄影师,拿着相机东拍西照,给采集藜蒿的同仁留下一帧帧精彩瞬间。藜蒿在明然眼中大概已是司空见惯,从小生长在湖区,野蒿原本不是菜,不过是喂猪的草料尔。红许也是湖区长大的,但他掐得特别认真,似乎在掐着少年时的一段心思。我掐这些野蒿,自然想起童年时背着背篓去河洲摘艾叶的情景。艾叶最嫩的那部分,在指甲的掐动下落在手心,随即落入背篓。我知道,采集这些艾叶回家,母亲能够做出一只只香甜可口的“艾叶豆团”来。艾叶有奇香,与糯米掺和做成米粑,翠绿如玉,特别可口。
艾叶与藜蒿的区别在于叶子,艾叶宽,藜蒿叶窄。这个特征极易分别艾叶与藜蒿了。
女子们采集着藜蒿,像线装书里的一首首古词。上溯诗经,“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萧,即是艾蒿。在诗人的想象里,艾蒿是与爱情联系在一起的。原来爱情是有气味的,就是当下鼻子里所闻见的这种香气。
凌 翼: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参加过诗刊社第17届“青春诗会”,毕业于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曾任《十月》杂志编辑、《现代小说》主编、《阳光》杂志执行主编。出版诗集《凌翼诗选》《以魂灵的名义》《灵魂驿站》,散文集《故乡手记》,随笔集《擦亮眼睛》,中短篇小说集《白果青,杨梅红》等著作,在《钟山》杂志发表过长篇小说《狩猎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