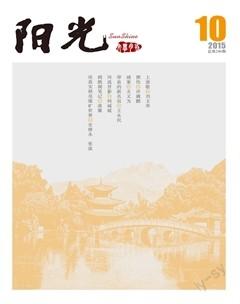矿工兄弟
班长石长争和预算统计员嘀咕了半天,就把这个夜班四个小组三十多个人的当班工资算好了,谁在哪条巷道干了什么活,挣了多少钱,有没有违章,干得工程质量如何,用了多少材料和电费……一一都输入了电脑,再一键就打入了矿结算中心的录入系统。如果哪个矿工去查当班的收入,只要摁三个“6”,查询的电脑屏幕上马上就显示出来。这样的内部市场分配,谁也别想有意见。
忙完了这件事,紧接着就是开班后会。他说了安全情况,这一班还不错,没有“三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犯劳动纪律)。谁有“三违”,要按内部市场定律,“谁制造的谁买”。你想让你的劳动成果都变成货币,最好别制造“三违”。“三违”是有价的,你有“三违”,用自己当班的工资买下了,这钱却到了别人手里——给了查着你的安监员或队长或机关工作人员。班长时常受连带,一旦受罚,石长争这个山东科技大的大学生出口就骂,操你娘的痴狗!
他扫了一眼各人桌子玻璃板底下都有的3户 “全家福” (三个班三个职工)照,只看清了自己在左上角的“全家福”,别人的距离远都看不清。为了安全,每个人上班前都要对着自己的家人照片发誓,绝不“三违”。他家的很特别,一张桌子有这么两张“全家福”,一张是自己的,一张是大哥石长景的。这张照片就是大哥、嫂子加他和侄子,大哥搂着儿子,嫂子搂着他的脖子。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对夫妇有一对儿子呢。实际上叔侄是吃一娘之奶长大的,严格地说,他石长争是吃嫂子的奶长大的。他和大哥一个班,平常大哥依赖他,坐在一张桌子前开会,住一个从农民家租来的院子,哥儿俩开了钱都交给嫂子。石长争扫了一眼“全家福”,想说的什么话就卡在喉管了,眉头拧上了一个疙瘩。
上夜班很劳累、很困乏,一班的工人不知班长又要放什么屁,谁也不想听一句,都想赶快回去睡觉。再说,内部市场化了,你班长买队长的工程,组长买班长的工程,咱工人卖自己的劳动成果,咱的劳动成果就是巷道进尺减去用电用材料和“三违”什么的,你班长放什么屁顶钱吗?多说一句也是纯粹放屁。内部市场就是用买卖代替行政命令,不是矿长管副矿长,副矿长管队长,队长管班长,班长管组长了,而是你卖我买了,谁怕谁呀!工人们也不怕谁了,你们当官的都包工程,都成了大小不同的老板,咱工人也是自己的老板,咱就是卖自己劳动力的钟点,不全卖了,全卖了就成了奴隶,那就不是特色社会主义了。
石长争想了半天,鼓着半天的屁终于放了出来:“今晚八点,班前会早点儿来,没别的事,就是选兵——小组长选自己的兵。自由组合,爱选谁就选谁,挣钱就行。前些日子职工刚选了班长,原则就是谁能领着工人挣钱就选谁。现在倒过来了,谁能让‘第一首长——小组长挣钱就选谁。散会。”这可不是个屁,是一炮,一班人没一个走的,都大眼瞪小眼。最终是他大哥石长景——人称“二当家”的说了话:“你个小狗肏的,是你自己的改革主意,还是矿长他娘的出的馊主意?”石长争苦笑道:“哥,我还改革,这是董事长那滩熊的什么孬主意。”石长景立即抓头皮,觉得选兵的事有来头。这时,有人乱说,“石长景,你和班长都是吃一个女人的奶,班长怎么那么聪明,你怎么那么笨?是不是你光玩不好生吃?”一班人一边散开一边哄笑。其实,班长石长争已经走出了会议室。
班长这个屁非同一般,一屁激起千层浪。
“二当家”石长景多了心眼,有了危机感。他比他兄弟石长争大二十多岁,就像两代人。原来,石长景的儿子石如玉生下时,兄弟石长争也同时出生,可这一天爹死在井下塌方事故中。娘在月子中得了病,一个月不到就呜呼了。从此,老婆许芹就把老弟当儿子养,儿子如玉吃一个奶,小叔子石长争吃一个奶。有时长争吃奶一手抱着一个,一手捂着一个,好像都要占着。许芹常对丈夫长景笑话小叔子:“人小也罢,怎么就知道和侄子争奶?”叔侄一同上学,同吃一个女人的奶,可考大学时,侄子考上了山东大学,兄弟考上了山东科技大学。山东大学是一类大学,山东科技大却是二三类大学——专门为煤矿培养人才的大学。石长景觉得老婆一定是喂奶时偏心,给亲儿子吃得多,给自己的兄弟吃得少。有一回为什么事吵,就计较起来。许芹恼了:“放你娘的什么屁,要是让你兄弟和咱儿子一同吃奶,你兄弟不打死咱儿子才怪哩。”后来,石长景发现,兄弟和儿子聪明不聪明不是吃奶造成的,长争下井后,聪明得很,不光机械样样都通,还很快当了组长,又选成了班长。可儿子上了山大,由于没背景,一直在学校教书,到现在也没买上房子。虽说兄弟长争当了个小萝卜头,就天天护着日渐年迈的哥哥,哥哥逢人就说,哥哥没白养了弟弟。这当哥哥的没读书,机械不能操作,在井下工作就是干些拾拾掇掇的杂活儿,由于兄弟是班长,挣钱也不少,有一些人就有意见。说不准,这次让组长选兵,过去的好景不长了,就没人要他了。长景感到,自己下岗的麻烦来了。
石长争心里也是为大哥担忧:组长一旦选下了大哥,大哥没有收入了,侄子如玉结婚好多年了,还没买房,仅靠嫂子开个理发店,什么时候买上房?虽然自己挣的钱都交给了嫂子,想必嫂子都给自己存着。自己也有了对象,是小侄子的“老板”——班主任。这年头,孩子把老师当老板,老师把校长当老板,校长把教育局长当老板。矿上也一样,似乎人人都是老板。矿上最大的老板是矿长,最小的是工人。工人是自己给自己当老板,一天卖自己八九个小时给矿长,剩下的时间才是自己的。矿长是大大的老板,一年开一百多万元; 副矿长是稍小点儿的老板,一年开六十六万元;队长一年开三十多万元;他当班长这个老板不大不小,一月挣工人二点四倍,大约一万五千元;组长开九万多元;哥哥仅是 “孤家寡人”的老板,一月吃平均数只能开五千元。他时常骂,娘的,内部市场也就是只算计工人!如果大哥不是自己这个班长照顾,最多每月开三千多元。工人和矿长的收入相差太远,工人和董事长的收入差得更远,内部市场就是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读过大学的石长争有时想不通,这时心里特别烦。
大哥被选下来怎么办?石长争的脑子里让这个问题占了全部。他知道,内部市场一实行,一个小组用两个人干了的活绝不用三个人,三个人分两个人的钱谁也不愿意。所以,有的小组长专挑身强力壮的、有技术的。现在打洞子都是机械化,没有文化的,像大哥一样的,没人要。有的工人参加了班前会,但没人要,就又回宿舍歇着;歇着很好,可一分钱也没有。内部市场不讲理,对老、弱、病、残和没文化的很残酷。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特色社会主义,应该人人都有参加劳动、获得收入的均等机会,在实行内部市场的洼里煤矿却没有。
石长争越想越认定,大哥必被选下来。因为内部市场一分一厘都算清了,由上而下层层承包之后,到了班组剩下的已经不多,组长拿平均数的一点二倍,骨干工人拿一点一点倍,一半以上的工人拿平均数的百分之七十或百分之八十。大哥受照顾,只能拿平均数。内部市场本是为了分配向一线偏斜,向公平靠拢,如今是分配公平了,还是更一步拉大了差距?他觉得这样的工资制还是像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石长争心里堵得像胸口有块大石头。
当石长争走出矿大门口时,回头瞅了一眼像鸟又像秤的大门口。这个大门肯定不是梁思成的作品,本来想让“鸟”腾飞,却没建上鸟尾和鸟头,两个翅膀还弄得一样平,弄巧成拙,鸟就变成了一杆秤。秤是公平的,回头看看,矿区似乎哪里也不显示公平。矿上的办公楼,楼顶中间又盖上了一间,两头低中间高;矿区到处是污水处理后改成的小喷泉,一个泉水柱落了另一个才起,此起彼落,总不一样齐;办公楼前两棵迎客树,还是一棵高一棵矮……他琢磨不出,是残缺的美还是对称的美。反过来想,整齐的也许没有美,正如绝对的平均是没有的。美不是整齐划一,平均也不是公平。他有了牢骚,如果中央领导知道自己的工资比矿长差了几十倍,“打老虎”会怎么打?奶奶的,自己是个小班长,上边打不打“老虎”关自己什么事?上边打了多少“老虎”,底下的不打等于个零。
后来他想,既然大哥必然被小组长选下来,就必须先和大哥说明白,必须让嫂子同意。不然大哥发脾气,嫂子恼了,像爹一样的哥、像娘一样的嫂,还不生吃了自己。在矿上自己是哥的老板,在家嫂子是全家的老板。他想想,就往菜市场走,决定买上菜和哥嫂喝一壶。出了门口一拐,就是菜市场,也是每逢五天一次的许长大集。这个集弯弯曲曲三五公里,青菜、萝卜、豆腐、猪肉、羊肉、牛肉……样样都有,就是一个钉子头也有卖的,一直延伸到大运河。不管是卖一棵葱还是卖一棵青菜,人人脸前有一杆秤,你卖一棵葱得一棵葱的钱,你买一棵菜就花一棵菜的钱。本来这市场很公平,也很平等(不是衙门,谁都可以到集上来),可经过矿上的内部市场一折腾,人们挣的钱不一样了,来集上也不平等、不公平了——有人有钱,有人没有钱,买东西有钱的才任性,没有钱的受制约。
他挤在赶集的人流中,一眼看见了一个副矿长,还是管掘进的副矿长,就装作没看见。心里话,你是副矿长有什么了不起,我又不是买的你的工程,是买的队长手里的工程。这位副矿长朝他笑了笑,他就眼皮一翻过去了。内部市场让人人只认一个老板,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不像过去,好像工资是领导给的,哪个领导也不敢得罪,对哪个领导也要求爷爷告奶奶。现在的工资,人人感到是自己挣的,就说他这个班长,就像一个小青菜贩子,买了队长的,又卖给组长,求他个副矿长什么用?从这一点看内部市场,似乎下级不那么“孙子”了,官与兵拉近了。
接着,石长争又看到了自己的真正老板——队长刘波定。刘波定脸上、身上有一百多斤肉,加上骨头、血和毛发有二百多斤。一笑那脸上的肉就像要掉下几块来,没掉下来也哆哆嗦嗦像要掉下来。石长争在全矿的干部中就是不敢惹他,他要是在工程上掉下一点儿肉来,或出一点儿血,兄弟们就大肥肥;他要是拉长了脸,兄弟们就混不出饭来吃。石长争马上就脸带笑容点头哈腰地问好:“老板,你也来赶集。”刘波定半真半假地玩笑,“这集又不是你们班的工程,只准你来,不准咱来。”石长争讨好说:“老板,我买上点儿菜,今儿中午咱弄瓶茅台?”刘波定“嘿”的一声说:“三天后可以。别人约定好了,往后排。”石长争笑着说:“三天,就三天。说话要算数,别到时又让我往后一个劲排,排到年底也轮不上我。”刘波定一边往前走一边说:“我什么时候说话不是钉是钉铆是铆?”石长争说了个“好”,心里话,他妈的“苍蝇”这么多,上边光打“老虎”有什么屌用。
石长争花了一百多元买了牛羊猪肉和鱼,还有大葱和四种青菜。到了村头的家,他不走大门,走并排大门的一个写着“理发店”的小门,迈进一只脚就叫娘,他嫂子就答应了。原来,小的时候侄子叫娘,他也跟着叫娘,就这么叫惯了,长大了,也不改了。老嫂比母,在他这里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他嫂子是一个大高个儿的妇女,略显肥胖,正在给一个矿工老头子理发。石长争说,“娘,我想和哥喝一壶。俺哥呢,没睡吧?”嫂子没好气地说:“他今天是在井下睡觉来,还是干活来?来家就醒了,看到哪里也不顺眼,嫌我放在厨房里的盆盆碗碗乱,在里边乱摔了一气,又试他的‘台钓(一种钓鱼方法),是疯了,还是你惹了他?”石长争不和嫂子说实话:“俺哥想酒喝了,我去炒菜。”
石长争到了厨房,见哥还在水桶里试验“台钓”的铅坠和漂,一见兄弟就黑着脸走了。当兄弟的也不恼,就把牛肉洗净放进高压锅煮,把羊肉切成了片准备吃火锅,一连炒了四个青菜,全部上了桌,打开了一瓶茅台,就喊:“娘,哥,咱吃饭了。”嫂子和哥都来到了北屋。屋里一张小饭桌,桌上的菜和箸放得满满的。哥打了半辈子工,从新疆到广东,从河南到山东济宁,那一年赶上洼里煤矿农民工全部转正,哥才稳定下来,嫂子也带着侄子和自己这个小叔子来靠矿的这个村租了这个院,就靠嫂子理发、哥下井供了两个大学生。如今叔侄都参加了工作,有工资,日子越过越好。可嫂子还是一天到晚理发,就是想给他们叔侄挣两座楼。
一般人家买座楼并不容易,济宁城里的楼房已经到了六千多元一平方。小叔子当班长一月开一万五千元,一月交给她这又当嫂子又当娘的一万元,剩下的五千元打发关系、买菜。丈夫一月五千元,除了钓鱼花几个全部上缴。她理发挣个几千元,几乎全部存上。一年全家存二十多万,已经存了三四年,差不多买一座楼了。她这个当娘的心里偏着小叔子,心里打谱,先给小叔子买上,再给儿子买。石长争心里却打定主意,先给侄子买,侄子已经结婚生子上小学了,自己刚找了个对象,不急。
一家人坐了下来。石长争给哥倒上了一杯酒,哥没好气地说:“你用个大碗,别用小酒盅穷倒倒,洒得到处都是。”嫂子气说:“你看你充什么大酒量的,用个桶还是用个盆?”哥哥石长景没吱声,一口喝了那一盅酒,就往碗里倒上了一碗茅台。石长争笑说:“哥呀,你没看看,这酒是五十二度的,你晚上还上不上班?”石长景又是没好气地说:“上个屌,就在家歇着了。”说着,一口就把一碗酒灌下去了。石长争叫好:“好好好……”这时许芹就夺了丈夫的碗,虎起脸说:“你是钓到了鱼了,还是发了奖金?”石长景还是不依,又从妻子手中夺了碗,又倒上了一碗,一瓶酒就见了底。石长争知道哥心里烦,因下一步要下岗没活儿干了。下岗对有固定工作的人都是考量,可这内部市场就这么逼人,他也保不了哥,一时也没想出办法。他劝说,“哥,你不用急,咱看看今晚这班前会上是不是没人要你了?真走到那一步,我准备请请队长,给你调一下工作。”石长景已经半醉了,骂道:“这个鸟董事长,光想着他那一帮同学亲戚和二奶三奶,都提拔成矿长、厂长和书记,就是不替咱老百姓着想。内部市场不是不好,看站在谁的角度去内部买卖算账……”嫂子插话:“没人替你着想?你就是个草包,鸭子不会浮水别怨那水草挂着。”石长景无言,吃了一碗米碗,就倒下睡了。
嫂子问起来,石长争就把矿上准备“将选兵”的事说了。嫂子想了想说:“长争,你不用着急,你哥五十二岁了,井下工还有三年就退休,他就是在家钓鱼也没关系,有他的五千元咱过日子,没有也过日子。”石长争沉思着说:“娘,矿上不是哥一个会在‘将选兵中下岗,肯定不少。听队长说,下了岗的到培训站培训后再上岗。我看俺哥到不了那地步,有我呢。”嫂子不再说什么,像是心里盘算着什么。长争吃过饭就睡下了,嫂子又去理发店忙活。当兄弟俩一觉睡到了天黑起来,许芹又蒸了饭、热了中午吃剩的菜,兄弟俩狼吞虎咽吃了,就上班去了。
到了班前会上,石长争就把组长选组员的要求说了,也说了自己的观点:“咱是特色社会主义,富的帮穷的,强的帮弱的,有技术的帮没技术的,别让内部市场搞得咱班没人情味了。”
一班人高兴地说:“哪能……”“那才弱智……”
“谁还不知谁,都在一起干活……”
这时说得好听,一开始选举,一组的组长说:“平时跟咱的,现在就走。”几个人齐心,说走就走。二组也是这样,三组、四组都是这样。最后只剩下了班长石长争和“二当家”哥哥石长景,没有一个人讲一点儿情面。兄弟俩沉默了半天,不知当哥哥的中午喝的酒还没醒还是气的,说了一些“棒子”话:“你白当了好几年班长。我下岗了,你管我……反正你吃了你嫂子三年奶,一天算一百元;我还供你上了多少年学,是多少元?你在你嫂子那里存的钱,就甭想要了,我全钓了鱼。”石长争听哥说这气话,立即泪流满面说:“哥,你放心,俺嫂俺都是叫娘,俺再挣上二十年,一分钱也不要。”哥哥想了想,呜呜哭起来:“俺没用,俺倒霉……”石长争心里想,什么改革也是,合脚的鞋有人穿着行,也有人穿着夹脚。
石长争想了想说:“哥,咱下井,我当班长,你就当副班长,还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大哥一下愣了,心里说,班长是职工选的,你说让我当副班长我就是副班长?你是不是耍俺?气说:“我回家睡觉了。”石长争认真地说:“我说的是真的。你下井去管那两个电闸和风闸,原来是我管,现在你替我管,你不开闸,他们就干不了活——你就真成了‘二当家。”石长景愣了愣,觉得是兄弟照顾,别人会说,也显得自己无能,说:“我管不了,我去打扫卫生。”石长争说:“行。打扫卫生也是工作。”于是,兄弟双双下了井。
到了井下,石长争要到每个小组看一遍,检查一番。石长景就在他们班打的巷道里扒水沟、捡破烂。自从实行内部市场后,破烂也捡不到,因为工资等于进尺减去费用和安全等,就是一根铁丝也有人捡,捡到就算进工资,井下有专门的收购人员。并且,谁也不再大手大脚浪费,一块木头楔子也算计着用。扒水沟是有价格的,一般的月工资超不过三千元。石长景想想过去自己吃平均能开五千元,现在最多只开三千元,心里就窝火,干着没劲。怨兄弟,还是怨自己?一时间似乎说不清。最后以为,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自己无能。都是过去家里穷,没读书;后来又养儿子又养兄弟,一辈子捉襟见肘,没进步的“关系”。
第二天上了井,石长景觉得没脸见全班人员,索性没有开班后会就回家睡了大觉。到晚上又上夜班,还是没脸开班前会,自己到点下了井,还是扒水沟。有人讽刺他,“二当家”成了“自当家”。一连几天,他也没脸和兄弟说话,吃了睡,睡了下井扒水沟,像个游魂。他以为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叫当班长的兄弟为难,也让自己没法做人了。
这天他下了夜班,直接找到了队长刘波定:“刘队长,我老了,又没技术,你给我另找个活儿干。”刘波定开玩笑说:“你不是当副班长当得很好吗,还找什么活?想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当个全国劳模?”石长景知道兄弟长争准和队长垫了话或是请了队长,笑说:“队长啊,人总有老呀!我给俺兄弟丢脸,我也不好意思,哪有固定的扒水沟工?”刘波定又笑了:“这样吧,你来办公室干副队长吧,给我当副官。”石长景又愣,心说,副队长就是个大官了,民选的很少,都是矿长任命的,自己怎能当副队长呢!刘波定队长又说了:“你来办公室干,管着五个队长的办公室卫生和会议室的卫生。我是队长,你不就是副队长了。”石长景觉得队长说的是真的了,问:“开多少钱?”刘队长笑说:“五千元,不够有人给你补上。”石长景心里就明白了,一定是兄弟长争为了自己的面子,早就和队长说了“补上”的事。石长景心里很舒坦,也很感激兄弟。
他走出队长办公室时,感到不是兄弟吃了老婆的奶欠他什么,而是他欠兄弟什么。他回到家,脸上很灿烂,也爱说话了,跑到老婆的理发店神采飞扬地说:“我被人家提拔了,由副班长提成了副队长。”老婆头也没抬,问:“挣多少钱?”他不知队长说挣五千元的话是真是假,便吹:“五千大毛。”老婆笑说:“你就烧死了,晚上一准睡不着了。”他是个信奉知恩不报非君子的人,想起昨天晚上小孙子回来说,明天是老板生日的话,马上告诉老婆:“孙子说,他老板的生日来了,想买‘烂苹果。”老婆气说:“他婶子还没进门呢,过生日给人家买‘烂苹果,好苹果还不兴许要呢!”他脾气好了,解释说,“不是咱吃的苹果,是笔记本,叫苹果笔记本。”老婆说:“好哇,一定是你出钱了。”石长景急了,说:“你这不是放下棍子打要饭的吗,我连一分钱也没留都给了你,你贪污了,被窝子里放屁——吃独食。”老婆笑说:“你买个破苹果笔记本,他婶子不稀罕,我倒有一把新楼的钥匙,也是烂苹果牌的。”石长景笑了说:“最终还是你有脸,办了一件人事。”夫妻没话了,都偷着笑。
许芹把没过门的兄弟媳妇请到自己家给她过生日,小孙子脸上最得意,一个劲地叫:“老板,老板,大老板,俺奶奶给你一把烂苹果牌的新楼钥匙。我祝你生日快乐,最最快乐。”没过门的小婶子说:“我先祝你快乐,最最快乐!你小叔说了,就是俺俩住在大运河的桥底下,也得先让你拿上烂苹果牌的新楼钥匙。”石长争马上接话:“孩子,小叔马上就提拔成队长了,队长一年开三十多万元,三年又挣上一把新楼的钥匙。就是不提拔,固定资产开始豋记了,苍蝇和老虎不敢买那么多房了,房价要落了。”
朱兴中:山东淄矿集团退休职工。著有长篇小说《劫难风流》《姜家太一家》《凯旋门》《竞争时代》,长篇报告文学《敬业之歌》《英雄之歌》和若干短篇和散文。《竞争时代》获乌金奖、五一文化奖、旱码头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