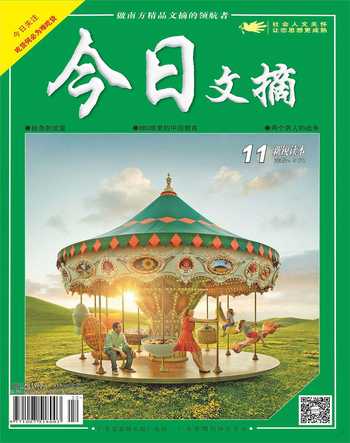“猪头”的爱情
大学室友有四个,睡我上铺的叫“猪头”。
夏天的时候,天气太热,压根儿睡不着。
宿舍的洗手池又宽又长,“猪头”热得受不了,于是跑过去,整个人穿条裤衩横躺在洗手池里。那叫一个凉快,他心满意足地睡着了。
结果同学过来洗衣服,不好意思叫醒他,就偷偷摸摸地洗,冲洗衣服的水一倒,沿着水池差点儿把“猪头”淹没。
“猪头”醒过来之后,呆呆地照着镜子,说:“为什么我这么干净?”
那年放假前一个月,大家全身的钱拼凑起来不超过十元。于是我们饿了三天,睡醒了赶紧到洗手间猛灌自来水,然后躺回床上保持体力,争取尽快睡着。
第四天大家饿哭了。
后半夜,“猪头”猛地跳下床,其他三人震惊地盯着他,问:“你去哪儿?”猪头说:“我不管,我要吃饭。”我说:“你有钱吃饭?”“猪头”擦擦眼泪,步伐坚定地走向门口,扭动身体大喊:“我没有钱,但我不管,我要吃饭。”我们三人顿时骂他,骂得他还没走到门口,就转身回床,哭着说:“吃饭也要被骂,我不吃了。”
清早“猪头”不见了。我饿得头昏眼花,突然有人端着一碗热汤递给我。我一看,是“猪头”,他咧着嘴笑了,说:“我们真傻,食堂的汤是免费的呀。”
全宿舍泪洒当场。“猪头”喃喃地说:“如果有炭烤生蚝吃该多好呀,多加蒜蓉,烤到嗞嗞冒水。”
再后来,“猪头”恋爱了。
他喜欢外系一个师姐。
“猪头”守在开水房,等师姐去打开水。
但他不敢表白。师姐将开水瓶放在墙边,一走远,“猪头”就把她的开水瓶偷回宿舍。一个月下来,“猪头”一共偷了她十九个开水瓶。作为室友,我们非常不理解,但隐约有点儿兴奋,我们可以去卖开水瓶了。
一天深夜,“猪头”说:“其实我在婉转地示爱。”
我大惊,问:“何出此言?”“猪头”说:“我打算在毕业前,偷满她五百二十个开水瓶,她就知道这是520(我爱你)的意思了。”
大家齐齐沉默。
那时候的男生宿舍,熄灯以后,总有人站在门外,光着膀子穿条内裤打电话。每张桌子的抽屉里,打废的IP电话卡日积月累,终于超过了烟盒的高度。
“猪头”很愤怒。他没有人可以打电话。他决定打电话给师姐,师姐叫崔敏。那头是崔敏的室友接的电话,说她已经换宿舍了。
“猪头”失魂落魄了一晚上。
第二天,学校海报栏前人头攒动,围满学生。我路过,发现“猪头”也在人群里面。出于好奇,我也挤了进去。
海报栏贴了张警告:某系某级崔敏,盗窃宿舍同学人民币共计两千元整,给予通告批评,同时已交由公安局处理。
大家议论纷纷。
我去拉“猪头”,发现他攥着拳头,眼睛噙满了泪水。“猪头”扭转头,盯着我说:“崔敏一定是被冤枉的,你相不相信?”
当天夜里,“猪头”破天荒地去操场跑步。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不惜体力地跑。一圈两圈三圈,他累瘫在草地上。
后来,“猪头”白天旷课,举着家教的纸牌,去路边找活儿干。再后来,在人们奇怪的眼光中,“猪头”和师姐崔敏一起上晚自习。到冬天,漫天大雪,“猪头”打着伞,身边依偎着小巧的崔敏。
几年前我回到母校,走进那栋宿舍楼。站在走廊里,总觉得推开308,屋里会团团坐着四个人,他们中间有个脸盆,泡着大家集资购买的几袋方便面,每个人嘴里念念有词。
然后我想起“猪头”狂奔在操场的身影,他跑得精疲力竭,深夜星光洒满年轻的面孔,似乎这样就可以追到自己心爱的姑娘。
我们朗读刚写好的情书,字斟句酌,比之后工作的每次会议都认真,似乎这样就可以站在春天的花丛中永不坠落。
我们没有秘密,没有顾虑,我们像才华横溢的诗人,无须冥思,自由生长,句句押韵,在记忆中铭刻剪影,阳光闪烁,边缘耀眼。
“猪头”结婚前来南京,我们再次相聚。再也不用考虑一顿饭要花多少钱,我们聊着往事,却没有人去聊如今的状况。因为我们还生活在那首诗歌中,它被十年时间埋在泥土内,只有我们自己能看见。
很快他喝多了,趴在酒桌上,小声地说:“张嘉佳,崔敏没有偷那笔钱。”
我点头,我相信。
他说:“那时候,所有人都不相信她,只有我相信她。所以,她也相信我。”
我突然眼角湿润,用力点头。
他说:“那时候,我做家教赚了点钱儿,想去还钱给被偷的女生,让她宣布,钱不是崔敏偷的。结果等我赚到钱,那个女生居然转学了。”
他说:“那天崔敏哭成了泪人。从此她永远都是个偷人家钱的女生。”
我有点儿恍惚。
他举起杯子,笑了,说:“一旦下雨,路上就有肮脏和泥泞,每个人都得踩过去。可是,我有一条命,我愿意努力工作,拼命赚钱,要让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和艰涩,从此再也没有办法伤害到她。”
我大醉,想起自己端着泡面,站在阳台上,看校园的漫天大雪里,“猪头”打着伞,身边依偎着小巧的崔敏,他们互相依靠,一步步穿越青春。
十年醉了太多次,身边换了很多人,桌上换过很多菜,杯里添过很多酒。
那是最骄傲的我们,那是最浪漫的我们,那是最无所顾忌的我们。
那是我们光芒万丈的青春。
如果可以,无论要去哪里,剩下的炭烤生蚝请让我打包。
(邓百涛荐自《文苑》)
责编:水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