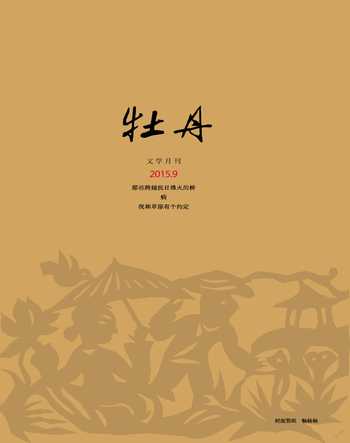桑葚情怀
晓芸
那日细雨,偶然走进窄窄的小巷菜场,见一乡村老太太坐在树边卖桑葚,不多,极新鲜,老人说是山里野桑树结的果子,我蹲下身细细瞧着桑葚,全部买下,打了一回桑葚的劫。
桑葚像一棵微型的桑树。“桑”字若写成甲骨文,就是一棵树的样子,这个字直到现在还是树的样子。“桑”是象形字,形似桑葚,有许多小核果集合而成,本身就很有诗意。古时农桑并重,桑与禾铺展在村庄边的沃野上,千年相沿相守着农耕日子。江南的桑、麻与禾妖娆了唐代,孟浩然走到村边的时候,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他与故人“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有桑麻的陪伴,农人的日子是贴心的安妥,桑与麻朴素得让农人没有过多的欲念。
我也很想在这个初夏的早晨,不经意间地走到一个村子,看到蓊蓊郁郁的桑树上那些桑果红了,树下站着几个孩子在闲等,说:再等等,红得乌紫才好吃呢!“陌上桑”的景象我没有见过,这三个字太美了,美成了一幅诗意的画。诗经《氓》中有“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意思是说桑树成长的时候,叶子沃然,说的极是,几千年后还是这样的,桑叶灵秀而丰腴,经脉青青,叶薄易破,柔媚得很,一如乡间的青衣女子,绿得透润。但民间有门庭不种桑树、桃树、槐树之说,说是这几种树阴气太重,我祖母在门前种的桃树就被祖父砍了,而那棵开着一串串白花的槐树,落花如雪,却长在东面那面土坡上,年年夏初飘散过来一股沁脾的槐香。我想她们一个个都是姣好的小女子。
从前的家门口有一棵白杨,叶子油绿而硬,叶黄枯落,叶柄枯韧,我们一一捡起,撸掉叶肉只剩下叶柄用来玩游戏,两条叶柄拦腰相缠,然后向相反的方向对扯,看谁的强硬,经久不断的就会被叫做“头老”。每每这时,桑只是在远远的林子里遥看着我们做游戏,风过处,传过来的声音是沙沙的,她那么柔弱,那时就有一种让我们小孩子心疼的感觉。蚕是童年的象征物,而桑叶大多用来喂蚕。那时农村的小孩子都养蚕,我当然不会例外,因此那时的桑叶很是难得,桑葚果更是娇贵得很,我的整个童年里似乎都没吃上几粒。
沧海桑田一词使我想到了纯粹的江南,如果我是织女,一定要拥有一件自己的蚕丝上衣,不行的话,背心也成,再不济也得有一块蚕丝手帕——那种绣上一只蝴蝶的丝帕。这不是一桩奢华的心思,我只是想因此可以常常想象着勃勃生机的桑田,让那鲜活过古代的华贵衣服鲜活在我的心中。
儿子没有尝过野生桑葚,好像童年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断了档、打了盹,提不起了精神。现在的孩子都是圈养在家中的,很少在野外撒欢。虽然儿子也想养蚕,可前楼挨着后楼,去哪儿寻找桑树叶呢?奇怪的是儿子能摘到桑叶,他常常跑回家兴冲冲地铺到蚕的身上,稍息一会儿后,蚕就会全部翻到叶子上哧哧地啃起来,后来桑叶不够胖胖的蚕吃了,儿子于是果断地要与我一起去乡下,然后带回满满一大包的桑叶。我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童年,激动地用湿巾给桑叶保温。儿子养的几头蚕顺利地化蛾飞去,收获了十几颗白色蚕丝茧,其中有一颗是金黄色的,我特意将它收藏在一只苏绣的蚕丝荷包中,扎紧绳子,算是收藏起了我与儿子两代人的金色童年。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现如今这是不大可能了,但“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的乡间还是可以看到的。可生活在城市中的下一代,因为没了庭院,没了苍巷,桑树无处安身,诗意的桑葚将会离他们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