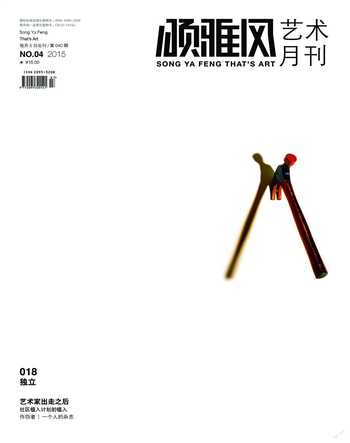园林,雅集的参与者
几乎所有的雅集都发生在园林之中,雅集和园林是一种鱼水关系,甚至更为紧密,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园林是雅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雅集构成了园林的本质活动。
“西园”所具备的深厚的文化内蕴,使这一意象获得古代文人普遍的共鸣,由此而延伸出对文人雅集所处场所的描绘,发展了以园林、庄园、宅园作为主题的雅集图式绘画,它不仅能够满足身居于城市的文人忘怀世情,寻找山林之趣的心理需求,充分体现了文人的雅集清兴、雅致、闲适的场景,并且以园林中的书斋、居室别号的寓意来突出主人的人格品质。
文人在创作“雅集图”的过程中,在视觉上分化出两种不同的审美趣味。一类是画中人物以格式化的坐姿呈现在繁花锦簇、文苑芬芳的园林环境中,这是对参与雅集文人的身份标榜。画家对庭院中的虬松湖石,古木修篁,厅堂水榭,曲水栏杆、四季景色着力刻画,以及对古玩、画册、书籍、古琴、钟鼎、古器等高雅的室内陈设不遗余力地精心描绘,彰显出主人高雅的品质。如沈周《东庄图》册再现了明代名园“东庄”。东庄是吴宽辞官后的栖身之所,无意仕途的文人雅士常聚集于此,沈周取东庄二十四处景点精心描绘,在深幽清雅的庄园环境中穿插文人品茗、观鱼、读书等活动,表现了文人放逸闲适的生活。
文征明于1530年作《东园图》更是精细地描绘的庭园景致,以及活跃在其中的雅集文人是为“东园”即徐申之所作的《别号图》。其中亭内4位文人展卷清议,一人行走在绿荫小路前来赴会,童仆抱琴随后。“东园”主人出院门远迎。亭外童仆端茶恭候;另一处水亭内有两位文人对弈,送水茶童匆匆行于湖岸。文征明情节性交待了发生在“东园”的雅集事件,他既给画中人呈现可以辨识的身姿面容,而不是草草概括;也给园林树、石、亭、楼、雕栏、流水巨细入微的刻画,并且尽量让人物比例与之相协调,有意让画中人与画中景融为一体,观者因此仿佛看见了文人身居城市雅集娱乐的真实。
除此之外,倪云林为如海法师作《狮子林图》和为自己宅园作《容膝斋图》,钱榖为张凤翼作《求志园》,文伯仁为顾广南作《南溪草堂图卷》,王云为郑侠如作《休园图》,焦秉贞为顾文彬作《怡园图》,王石谷为杨兆鲁作《近园图》,沈士充为王时敏作《郊园十二景图册》等都是以名副其实的以庭院为描绘对象,以很大的写实性再现了这些著名园林的景致与文人诗文酬唱的艺术生活景况。
另一类描绘则是没有真实对应的园林实物,而是由画家凭借想象,经过提炼、构思,集合诸多庭院景致较佳者构成幽雅的场所。画中的文人高士置身于美景园林中,借助寓意性的场所和自然景色表现文人理想的隐逸之所。
此类雅集图在文人画家笔下往往表现得较为写意,大多对园林着墨较多。主题人物有的被完全纳入到山水画的主体结构中,虽然人物存形细小如豆,但仍强烈传递出文人雅集所标榜的高蹈清逸等理想境界及追求。
王紱《山亭文会图》即表现了这样的旨趣。图中层峦迭嶂沉郁苍茫、古木茅亭清旷萧疏,墨隽沉厚,布置密集。表现了云水烟霞的山林之景与从容散逸的雅会情境。此图刻画文人雅士聚在山下茅亭中谈诗论文的情景。然而茅亭只据图左下小小一隅带过从容散逸的雅会情境,整幅画面是云水烟霞的山林之景:一峰高耸,群山环绕,山腰白云袅袅,林木葱郁,有亭台楼阁,隐现其间。山脚深处,有溪水潺潺流出。茅亭中已有五人,三人围坐案前,案上有文稿,另两人则凭栏而立。山路上一人策杖而行,溪中一小舟载人而来,亭前坡路上有两人驻足而谈,这些人显然是赴山亭文会而来,共有十二人之多,但每人图绘不过二厘米高,几乎融化于大山之中。但王紱没有画出雅集文人清晰的面容,而只是一类高士清流的象征性身形符号,这类符号的文化意涵对观众而言是如此熟悉,以至于王紱并不需要为画中人作过多修饰,与宫廷画家为“雅集”铺陈的庭园环境不同,王紱图绘山林气象并使其成为文人雅事旨趣表达的主要叙事构件。
同样的例子还可见于沈周《魏园雅集图》,画中人物细小如豆不辨眼目,其中四人坐于一草亭内,一童仆抱琴侧侍。树下一戴帽文人策杖而行。“魏园”即周鼎题记中所谓“魏氏园池”,可能实有其所,但沈周却画了一处与其毫不相干的山林之景,正如在题记中祝颢所言,雅集文人是为逃避“城市多喧”而“抗俗宁忘世,容身且避庐”,他们聚会在“画壁东林”而满足于:“青山归旧隐,白首爱吾庐,花落晚风外,鸟啼春雨余,懒添中后酒,倦掩读残书,门径无尘俗;时来长者车”的田园画境中。
几乎所有的雅集都发生在园林之中,雅集和园林是一种鱼水关系,甚至更为紧密,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园林是雅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雅集构成了园林的本质活动。园林也成为了雅集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