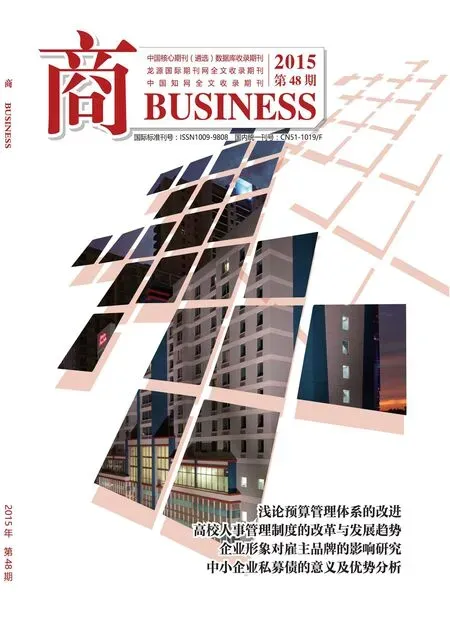从小说到电影
苑竞玮
摘 要:从聊斋小说原著中简单的美与丑、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到新世纪电影《画皮Ⅰ》将原作故事内核转换为对“小三”与“原配”之现代人婚恋观的探讨,再到电影《画皮Ⅱ》所述皮相与心之间的矛盾辩证关系,“画皮”的故事内核依据现代社会人的生活变迁而发生了有趣的变化。
关键词:画皮;小说;新世纪电影
一
作为前现代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学作品,《聊斋志异》以纸质抄本和刻本的传播形式获得了读者广泛的认同,凭借文字所建构的纸上风景激活了人们对鬼狐花妖世界的奇幻想象。然而,小说《画皮》的思想却是复杂的,它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转换。小说讲述了太原王生遇鬼,遭其蛊惑并为其所害最终死而复生的故事。故事的前段讲述了王生在街上遇一身世悲惨的美女,他收留了这位美女并置于密室与其偷欢,作者写到这里将笔锋一转,岂料此女竟是恶鬼所变,她撕裂了王生的心肺。最后,还是在王生妻子的坚持和牺牲下,才让王生起死回生。至此,我们可以发现故事真正的主题可以用两个方面来概括。其一是“人妖对立”,即正邪不两立的哲学思想,这是一种简单的二元思想的划分。其二为美女祸水论,反映的是封建礼教与欲望的二元冲突。美女与丑鬼一体两面的存在形式似乎给色迷心窍的士人以严厉的当头棒喝,印证了以色为戒的陈规古训。在士人心中,“美女”这个符号指代世俗欲望。很显然,从伦理价值层面来看,“欲望”是恶的,读书人的“礼仪”才是善的,正好体现出儒家伦理道德与欲望之间的矛盾,在此更有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为证。欲望是诱惑性的,但欲望又是危险的。《红楼梦》里“风月宝鉴”的一面是美女图,而另一面却是骷髅图,也可以看做是对“画皮”中的美女哲学的总结,即“色”字头上一把刀,贪欲的结果是性命难保。落第才子蒲松龄借奇异故事告诫众人,要警惕異端,尤其是那种以“美好形式”出现的异端。
二
新世纪以来,小说《画皮》的电影改编经历了从小说经验到大片奇观的审美转变,自然在故事内核上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无论是传统小说还是电影,叙述中的“矛盾冲突”总是引人入胜的情节关键,而叙述中的冲突最终依靠的还是故事深层的哲理冲突。陈嘉上导演的《画皮Ⅰ》将“妖与人”的二元对立转换成现代人情感危机中“艳遇”与“家庭”、“现代爱情观念”(生命苦短、只争朝夕)与“传统家庭观念”(白头偕老、天长地久)之间的普遍矛盾,从而更加深刻地引起了现代人的情感共鸣。因此,赵薇扮演的义妻佩蓉作为传统情义观的代表,获得了现代普通女性观众的极大认同。电影中,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佩蓉:忠贞、坚强、果敢、宽容,最后成为婚姻的拯救者,这点倒是与原著小说《画皮》中王生的妻子拯救王生的叙述功能是一致的。同时,电影将小说中的“妖”具象化为狐妖,由充满灵气的演员周迅扮演,既赋予了“妖”美丽的外形(这点与小说相同),同时又赋予了“妖”和人类一样真挚的情感。电影《画皮Ⅰ》故事的哲学矛盾,从简单的善与恶的根本对立,转换成基于不同立场和情感而表现的人性的冲突。可以说《画皮Ⅰ》冲淡了原著小说中的神鬼怪诞色彩,将叙事的重点转向当下的“婚外恋、三角恋”题材,从而与其他题材影片一起加入“男人出轨之后怎么办、妻子的婚姻保卫战、小三的爱情争夺战”之“话题”的探讨中去了。
三
乌尔善导演的电影《画皮Ⅱ》依然离不开邪(狐妖)与正(靖公主)的二元构成关系。在这正与邪当中,还夹杂着一个肉眼凡胎的中间派霍心(谐音“惑心”),他看不清真相,分不清真伪,是一切陷入诱惑又渴望得到救赎的世人的代表。“狐妖”与“靖公主”两个角色分别代表事物的两极,而“霍心”则是“正”、“邪”两股力量要争取的对象。“邪”派的武器是迷人的皮相——世上最美女人的外皮;“正”派的武器是挚热的心——纯正、热情、无私、奉献。
《画皮Ⅱ》最迷人的叙事是“换皮”,最精彩的视觉也是“换皮”。从叙事上说,“换皮”不仅是整个电影叙事的情节核心,也是该故事从视觉表层进入哲学深层的关键。狐妖小唯说:“男人在乎的永远是女人的皮相。”狐妖没有心,也就没有感情,但她有魅惑男人的致命武器——天下最美女性的皮相。光凭这一点,她就能轻易获取世上所有男人的爱情,但唯独得不到的是别人心甘情愿赠与的心。毁容的靖公主拥有一颗火热的心,这颗心挚诚热烈,可以融化冰雪。她全心全意的爱霍心,却因为失去了美丽的皮相而得不到渴望的真爱。
就这样,两名女性角色为了各自的需求做了一笔交易,那就是换皮。靖公主通过拥有狐妖的皮,而得以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的机会,但实际上她是以小唯的名义活在人间,没有人知道她真实的自我。靖公主这种为爱而牺牲自我的形象,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发挥到了极致,也延续了《画皮Ⅰ》中正妻佩蓉的主要性格特征。
对于霍心而言,换皮了的靖公主,拥有了绝世美丽的容颜,虽然没有了血肉之心,但是对霍心的满腔爱意,却并没有因为失去血肉之心而有所减损。就这样,霍心暂时获得了完美的爱情,即既有皮相之美,又有情义之真。而对此时的靖公主而言,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她的现实身份是小唯,她的自我因为失去了血肉之心的支撑,而成为了虚幻的幽灵。即:既非皮相之真,又非非皮相之假。有点类似“无间道”,既非人间,又非地狱。
影片的最后,霍心知道了真相,即懂得了隐藏在美丽皮相之下的灵魂,她虽失去了血肉之心,但依然保持着人的骄傲和尊严,宁愿忍受冰冻皮裂的痛苦,也不愿吃别人的心来挽救自己的形象,这才是真正的靖公主,即使皮相非我,血肉之心非我,但我依然是我,而保持这种自我本色的,既非皮相,也非血肉之心,而是一种可以叫作灵魂或精神的东西,它还有个别名,叫作爱情。
那么至此,影片传达了一种本质主义的爱情观:爱情既非皮相之美,且又超越生命之上(以血肉之心为基础的生命),它是一种类似精神、灵魂之类的东西,我们还可以给它起个别名,叫作信仰。皮相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信仰(爱情)故,两者皆可抛。
霍心最终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他刺瞎了双眼,为的是让心灵解放。因为没有了眼睛,从此不必也不会再为皮相所惑,凭心去感应,听从心的召唤,霍心终于不惑,他获得了一颗澄明的心。如此,他收获了真正的爱情,而当他的内心回归澄澈、真正放下皮相对他的诱惑时,当外在的一切都不重要时,靖公主不仅收回了自己那颗火热的血肉之心,也恢复了最初美丽的容颜。
美在自在,美在无惑。美在你不觉得她美时的模样。美在你肉眼看不见的时候。
四
从故事的“斗争”哲学看,小说《画皮》讲述的是善与恶之间的根本对立,反映出古人思想中简单的天地自然人生观,即“天道好还,因果轮回”;《画皮Ⅱ》通过讲述一个通俗的爱情故事来探讨表象与本质之间的辩证关系。相对而言,《画皮Ⅰ》的哲学意味要相对弱一些,它主要讲述一个关于情感伦理的故事,更符合当下中国人的现实心境。然而总体说来,三者之间又延续了基本的一致,即不管是人还是妖,不管是美丽的妖还是恐怖的鬼,不管是诱惑还是真心,都要守住自己的心。在爱情中,只有用心去感悟,才能分辨出真爱;不要被表象迷惑,也不要贪恋一时的诱惑,在真爱面前,首先得做一个明辨是非、能辨真伪的明白人,才能够拥有真爱。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三者都传递了一种本质主义的价值观。在当今众声喧哗的社会现实面前、纷纷扰扰的世俗镜像面前,在许多人都不知道信仰什么东西的时代下,这样的价值观应该是有建构作用的。(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蒲松龄著《聊斋志异》之“画皮”的故事。
[2] 陈嘉上导演电影《画皮Ⅰ》2008年。
[3] 乌尔善导演电影《画皮Ⅱ》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