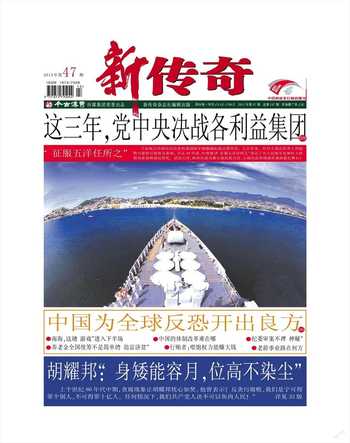土司文化蕴含七百年治国智慧
土司制度节约了大量国家治理成本,如军费、官员俸禄等;土司因俗而治,保留了民族的文化多样性。
2015年7月4日,这是73岁的司城村村民向盛福永远难忘的日子。退休后一直为传播湖南永顺老司城文化辛苦了13年的他,终于等来了这座遗址申遗成功的消息。当天,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土司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决议。这次,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贵州海龙屯三处联合申报成功,成为中国第48处世界遗产。
土司,这一中国独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现象,开始走向世界。
沉寂多年土司城
说到“土司”,不少人乍听之下还以为是“吐司面包”。实际上,这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授权地方少数民族首领治理当地的一种政治制度,同时也是这种制度下少数民族官员与衙署的名称。土司始于元朝,陆续结束于清朝,最后终结于民国。通常认为,土司制度的前身是源自于唐朝的羁縻制度。
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高祖李渊下诏书:“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行政殊于华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羁,即马笼头;縻,即牛缰绳。唐朝的“羁縻”思想是对边远少数民族首领既要给予一定政治、经济利益,又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将这种思想实施于政,体现在“即其部落列置郡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新唐书》记载,当时的羁縻府州多达856个。
元朝时,羁縻制度正式改良为土司制度,目的依然是为了稳定边疆少数民族、巩固中央王朝的统治;也还是实行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其职、世长其民、世领其土”的自治管理模式,宽柔相济、恩威并用。不过,元朝对少数民族认识观发生了彻底改变。羁縻时期的统治者,认为少数民族是蛮夷,不可教化,而元朝统治者本身即是少数民族,他们把少数民族看作国家体系内的人民。同时,羁縻制度下的土官属国家职官体系之外另立的一种体系,而元朝则将土司真正纳入了国家机构统一的职官体系,土司成为中央王朝统辖的地方行政官员。土司制度在明朝进入鼎盛时期,且影响力大的土司集中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土司与中央的纠葛
元朝至清朝,朝廷赋予土司对当地进行自治化管理的权力,如对领地、属民、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武装力量等方面的管理;同时还规定了土司对中央政权的明确义务,如进贡、纳赋、征召等。大多数时候,土司遵循与中央的这种契约,双方和谐共存;然而,土司之间、土司与中央之间也时有摩擦,有时甚至上升至兵戎相见,而海龙屯正是见证了这样一场血战。
历史上有“两广岑黄,思播田杨”四大土司之说,其中又以播州杨氏实力最强,极盛时南北横跨两千余里,除今天遵义市全境,还包括黔东、黔东南、贵阳、铜仁和重庆的部分地区。但是传至杨应龙时,播州土司的实力已大不如前,他一心想要重振雄风,遂对先人所筑海龙屯进行较大规模的修整与加固。
播州土司之前一直效忠明廷。杨应龙统辖期间,重拳打压播州内部的“五司七姓”,依靠收买“苗兵”来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杨应龙的做法,激起了播州百姓、五司七姓及贵州官员的不满,而播州所处位置为四川、贵州交界处,两省的官员都想争夺此处的权益。大族首领和贵州巡按一起联名上书,将他告上朝廷,历数他的24条大罪。此后,朝廷派出要员在重庆三堂会审,认为杨应龙“论罪当斩”。对此,杨应龙提出愿用白银两万两赎罪,并愿意拨付5000名土兵助朝廷平倭。
然而,第二年四川巡抚又要抓他定罪,杨应龙只好又一次来到播州边界,下跪请罪,并答应交出次子杨可栋留在重庆做人质,再交赎金四万两。结果,杨可栋到重庆没多久就患病身亡。杨应龙索要儿子尸体回乡安葬,官府却不给,还催他先交齐赎金再说。悲愤之下,杨应龙遂与朝廷正式决裂,举兵“反叛”。
先期与明军交战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四月十六,杨应龙退回海龙囤,准备坚壁清野,严防死守。一个多月里,明朝的八路大军始终无法攻破海龙屯,尤其是在飞虎关及其前的“三十六步天险”,大炮难以发挥作用,而且一遇进攻,守军就居高临下抛下滚木、礌石,明军死伤惨重。
最后,在其他土司的帮助下,明军从后关攻破海龙屯,杨应龙自杀身亡。明军虽然平复了杨应龙之变,将播州改土归流,但“平播之役”耗费了朝廷百万军饷,使得明王朝元气大伤,和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的朝鲜之役并称“万历三大征”。明朝被这三大征耗尽了气数,不久即灭亡。今人看来,明廷对播州土司的狡诈和反复,是杨应龙“叛变”的重要原因;明廷也因此自食其果。随着中央与土司的势力各自膨胀,中央不妥善处理好与后者的关系,就会导致国家动荡。
七百年智慧文化
申遗成功,“土司文化”一时成为热门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李世愉表示: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创建和推行中特定的一种文化,不能离开土司制度来谈土司文化,不能将其和一般的少数民族文化混为一谈。
在中国建筑设计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申遗文本中,有如下描述:中国土司遗址展现了中央政权与地方族群在民族文化传承和国家认同方面的人类价值观交流,联合申遗的三处遗址是中国西南部地区土司管理制度的特殊见证。13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备了稳固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强大的文化、政治、军事实力,此期西南广大少数族群自身内部社会发展也已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中央政权为深化对这一地理阻隔、文化多样地区的管理,谋求社会的整体平衡与发展,制定并推行了秉承“齐政修教、因俗而治”传统智慧的“土司制度”;同时,对土司管理权力和义务的制度化规定,促进了其管理方式与国家管理体系和文化思想的接轨。
土司制度是一种区域社会管理模式,在成臻铭看来,它具有很强的政治现实意义: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自治制度,从土司制度中吸取了不少有益元素,而且这种研究和借鉴在当下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9月底,老司城博物馆和景点已经正式开放。从申遗开始就一直被变得非常忙碌的向盛福,依然保持着他的高度热情。他说,他已经培养了十几个讲解员学生,还要接着培养更多。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家乡的土司文化为世界了解。在他眼里,土司的故事,永远写不完。
(《新民周刊》2015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