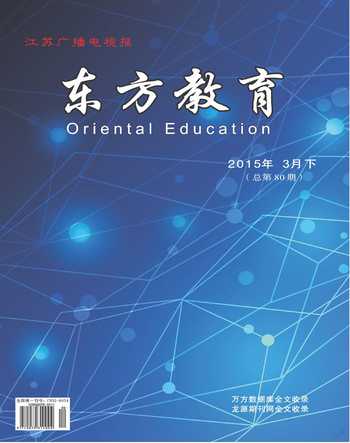从伯克保守主义思想看法国大革命
陈婷
【摘要】柏克被称为政治保守主义思想之父,在《法国革命论》中猛烈地抨击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柏克认为一种绝对的民主制就像是绝对的君主制一样,公民中的多数便能够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压迫,这种对少数人的压迫会扩大到远为更多的人的身上,而且几乎会比我们所能畏俱的单一王权统治更加残暴得多,这就说明从伯克保守主义看法国大革命必然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会更加的残暴。
【关键词】保守主义;传统文明;社会秩序;民主与残暴
一
“保守主义”一词已经出现泛化的趋势,并引起诸多误解。为重新界定该词的内涵与外延,可以借助对保守主义鼻祖——柏克思想的探讨来认清保守主义的本质。从历史渊源看,柏克思想的核心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强调经验,避免蹈入形而上学;第二,强调传统,避免蹈入怀疑主义。因此,保守主义的本质也包括这两个方面:既破除理性的权威(保护个人自由),又树立上帝的权威(维持社会秩序)。由于坚持理性的有限性,柏克在处理上帝与个人之间的中介物———历史或传统时,必定会出现无法分辨的困顿,但这种困顿是基于人的有限,因此是必要的。任何因之对柏克思想的修正都会偏离保守主义的本质。然而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对英国宪法、政治改革尤其对法国革命的态度上。他极力捍卫宪法,表现出了保守主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时政治变革的极度敏感,对法国革命的完全否定却反映了这种保守主义的局限和政治反动。另外,伯克认为传统作为人类悠久的智慧结晶,是不应该彻底砸烂的。相反地,它是人类最可宝贵的财富,是人类健全的进步和发展的唯一保证。但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则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它把一切美好的传统都摧毁了,它以蛊惑人心的口号摧残了人的权利和法制的秩序,使得各种不同的利益再也无法互相调和并且各得其所。大革命中的激进派曾经力图普遍地改造法国人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推行户籍身份非宗教化,在最激进的地区掀起一场毁坏所谓天主教的“外部标志”的风潮,砸烂、焚烧,甚至趁乱打劫。在剧烈动荡的时代,丑恶的东西往往以革命的名义来发泄平时压抑的情绪。伯克的理论不是从某一种哲学体系的观念出发的,故而他所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革命,而只是法国大革命的那样的暴力。现实世界必定是好坏,善恶交相掺杂。如果人们一味追求完美,其结果反而只能成为导入歧途的欺人之谈,甚至产生专制和腐败。因而革命就有可能完全成为以暴易暴,假纯而又纯之名,行其专制腐败之实。
如果说柏克对英国宪法近乎迷信,对改革的谨慎态度近乎神经质,但他对法国大革命却始终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其保守主义的反动也主要表现在对法国革命的攻击、对欧洲中世纪传统和风俗习惯的赞美上。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表明自己的立场,总体说来,此书中抨击法国革命的部分远不如对英国的政治考察、对传统价值的认识更令人信服,这种以英国历史来判断法国革命的方式必定是无力的。法国的革命者确实做了大量如他指责的清除旧制度和依照“理性”建立新制度的工作,如废除所有封建特权,限制国王的权力,实行政教分离,确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制定宪法保障公民的各项“天赋权利”等。但法国革命不是反对路易十六国王,而是反对政府的“专制原则”;与以往的“革命”不同,美国和法国革命使“自然秩序焕然一新”。而英国人已经做并且正在做类似的事情。托克维尔认为,法兰西人的确想摆脱过去的一切束缚,“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些法则明确地体现在《人权宣言》中。但柏克指责革命者完全依靠理性建构社会是不公平的,也是对革命的无知。而柏克的愚蠢在于把英国“光荣革命”看成是“人类活动的终极标准”和所有革命的样板,欲使英国的狭隘经验推广到别处。柏克一方面指责革命的“暴行”,另一方面对旧制度下的罪恶视而不见。事实上,专制制度制造的罪恶大大多于革命,只不过前者大都分散在漫长的时间进程中而不那么引人注目。改良也许少一些暴力,但代价也是巨大的: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不仅长期受到严重的束缚,几代人的生命也在漫长的等待中被自自消耗掉—侯河之清,一次革命也许不能,一般也很少能够实现它设定的目标,但也会使统治者摈弃赤裸裸的独裁专制主义,复辟的欧洲王公们手里不也都挥舞着一部“宪法”吗?很显然,柏克不赞成法国大革命那样过快过激的革命,而是倡导一种在尊重传统基础上的谨慎变革,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反思当然不能认为完全正确,但却可加深我们对暴力革命的认识。
二
法国大革命对于英法两国思想的冲击,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和意义。柏克对大革命原则的批判集中在否定自然权利,否定大众民主,拥护贵族政治的自由。不能简单地说柏克彻底反对自然权利,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认为自然权利在现实政治中不能发挥什么重大的作用,如果承认自然权利,反而可能会导致政治上权力的混乱。人民的权利几乎总是被这些理论家诡辩地和人民的权力混为一谈。如果柏克确实反对自然权利,那么他应该在彻底负面的意义上运用人权、社会契约之类的概念,但柏克自己恰恰说到:“我远远不是在理论上要否定真正的人权”。从理论渊源上说,柏克的社会契约说源于欧洲中古的自然法传统,该理论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限,目标在于维持均衡的社会秩序。在权威与自由之间维护英国宪政秩序,才是柏克心目中真正的“好政治”。“人们不可能同时既享有一个非公民国家的权利,又享受一个公民国家的权利”。真正的政府不是由于天然权利(自然权利)而建立的,“天然权利可以,而且确实是完全独立于它(指政府)而存在的;并且是以更大得多的明晰性和以更大得多的程度上的抽象完美性而存在的;但是它们的抽象完美性却是它们实际上的缺点。由于对一切事物都有权利,它们就需要有一切事物”。由此可见,柏克批判的是自然权利的抽象性。
法国大革命所建立的民族、国家是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由于柏克否认了作为抽象原则的自然权利,因此他同时也就抽调了法国新体制的底座,否定了自然权利在构建国家时的基础地位。反过来说,如果在法国人看来,人可以因为拥有自然权利而推翻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新国家的话;那么,在柏克看来,人与国家的关系远不是法国人所理解的那么简单。柏克一方面肯定了人的权利,同时又否定了每个人对于何者有利于他的自我保全和幸福做出判断的权利。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能理解柏克最为反感的不是自然权利的抽象性,如果只是玄学家们的冥想,那也是无伤大雅的;他反感的是将自然权利加以运用而生发出的人民主权和民主,它们对于现实政治是极端危险的。柏克也认为如果有人能够向他证明法国的国王和王后确实糟糕透顶,是顽固而残酷的暴君,那么对他们的囚禁和惩罚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将某种万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用一种人民主权的理论将其正常化、规范化。伯克认为人民的意志能决定一切,这是彻底错误的。国家绝对不是由大众或者“人民”来统治的,他压根不相信人民的政治能力,千万不要认为人民总是对的。法国大革命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人民主权则要求民主政治的产生,而民主政治必然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多数人的意志和他们的利益往往是有分歧的;而当他们做出一种坏的抉择的时候,分歧就会很大。对于民主制度弊端,柏克很深刻地指出:“完美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因为它是最无耻的,所以它也就是最肆无忌惮的。没有人以为他那种身份会害怕自己可能要受到惩罚。人民整体肯定是绝不用害怕的:因为所有的惩罚都着眼于保护人民整体而作出的范例,人民整体永远也不能成为任何人手下的惩罚对象。关于这一点,我能肯定的是每当一个民主制的政体出现像它所往往要出现的严重分歧时,公民中的多数便能够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压迫;这种对少数人的压迫会扩大到远为更多的人身上,而且几乎会比我们所能畏惧的单一的王权统治更加残暴得多。在这样一种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就处于一种比其他的迫害下都更为可悲的境地。那些在群众之下遭受到伤害的人却被剥夺了一切外界的安慰。他们似乎是被人类所遗弃,在他们整个物种的共谋之下被压跨了。可见,在柏克看来,现实政治是见不得,或者至少是不需要平等存在的。平等不能进入政治领域,也进入不了政治领域。政治说到底是政治精英的事业,政治必须要由充满了责任感和政治智慧的精英来运作。如果如前面所言,平等是现代人拒绝不了的价值,那么柏克是反对这种现代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