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私心”
张宪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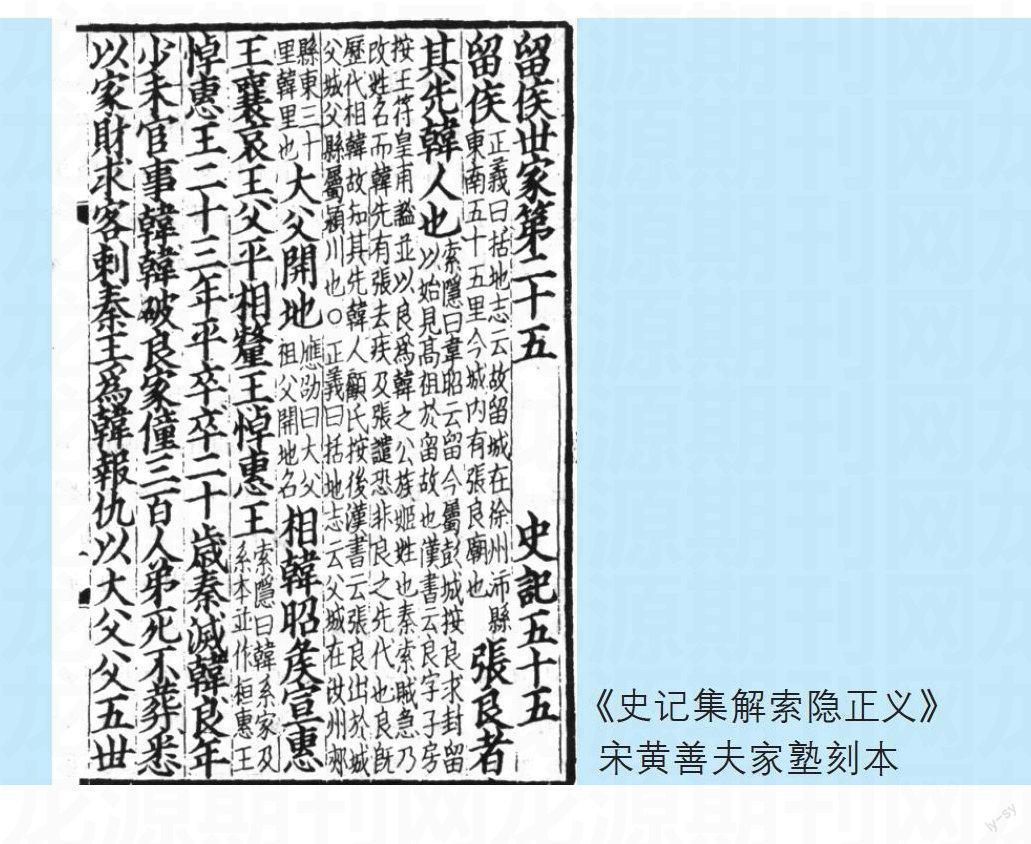

一
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曾三次提到“私心”一词。第一次是针对朝中对李陵的诋毁而发:“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在司马迁眼中,李陵是位奇士,孝信廉义,恭俭礼让,有国士之风,而且“能得人死力”,却遭到那些明哲保身之徒的丑陋攻击,以他的性子,面对皇帝的垂询,仗义执言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司马迁的这一辩护本身有些天真,没有意识到皇帝也许只是装装样子,为自己的刚愎自用、任人唯亲找个台阶下,并不想听什么逆耳忠言,落得一个“沮贰师”、“诬上”的罪名是可以预见的。他本来有机会用赎买的方式免罪,却偏偏家里穷,出不起钱,最终被施以“最下”、“极矣”的宫刑。这一事件在司马迁一生中的意义,也许仅次于司马谈的临终遗命,并且把他和李陵家族的历史叙事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第二次言及“私心”,与他内心的生死煎熬有关:“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透过这些忧愤蟠曲的文字,我们可以想象司马迁戴罪囚室时内心的纠结,自杀也许是保全自己及家族名声的最好选择,可是这样一来,父亲的遗命、数十年来自己对天人关系、古今变迁的思考便化为了泡影,二者相权,他勇敢地“就极刑而无愠色”。以著书的方式来洗雪耻辱,显然是一种更艰难而痛苦的选择。第三次提到“私心”,才与收信人任安有点关系:“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私心”二字,《汉书》作“私指”,意思并无差异。
倘若评选中国历代书信“十强”,我认为《报任少卿书》应荣膺榜首。明人孙矿称之“粗粗卤卤,任意写去,而矫健磊落,笔力真如走蛟龙,挟风雨”,其纵恣奇肆,郁勃沉雄,足以与《离骚》“抗衡千古”。你简直不能说它是一封书信,而是一首写就的激烈诗篇。当这一大捆竹简递进囚牢的时候,想必汉武帝随即就会收到线报,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带有挑战意味的行为:这首“诗”并不只是写给任安的,也许它最重要的读者该是汉武帝。也就是说,司马迁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如此袒露“私心”,也许只是为了使它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借此向汉武帝的“治心”表达抗议。
据学者研究,《报任少卿书》作于太始四年(前93),距司马迁天汉三年被施腐刑过去了六年,这时《史记》已基本完成。但是“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就可以发现在这封接近三千字、字字血泪的信里,六年的时光丝毫没有冲淡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内心的屈辱一直在腐刑后的岁月里翻滚,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虽然我们对这六年之中司马迁生活的细节缺少了解,在担任中书令职务之暇,我们可以想象他把所有时间都交给了《史记》,而这一写作过程则始终伴随着《报任少卿书》所描述的郁怒与纠结。孙执升曾说:“史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此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也。”这话很精辟地指出了《报任少卿书》的“私心”和《史记》的历史叙事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文心雕龙》云:“心生则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一定程度上来说,司马迁这种立根于自身独特生命体验的“私心”,也是一颗“诗心”,激励着他为“天地立心”,迈越往古,遥接方来,为他的历史写作注入了诗意的内核,使他成为历史叙事领域中的屈原、李白。
二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著作,将经济、政治、哲学、人物、天文历法、礼乐制度等历史元素融于一体,体现了西汉中前期对于过去与当下最深刻和复杂的认识论体系。它并非对历史实在不走样的摹写、再现,而是夹带了丰富的“情感私货”。明清以来,颇有一部分文人学士把《史记》当小说、文集来读,近代则有李长之、钱锺书等人从诗性、虚构、修辞等角度对《史记》作出了十分有价值的解读。尤其是李长之,把司马迁视为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认为《史记》浓郁的史诗性“不唯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这一看法跟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海登·怀特有相通之处。怀特特别强调“历史的文学性和诗性”,并曾指出:“历史学家丝毫不逊色于诗人,他们可以将某些意义样式融入到他们的叙事中去,从而获得一种解释效果,它超出了历史学家对特定历史事件的形式解释。”换言之,司马迁既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他把私心骚意和意义样式、历史叙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辖治”了三千年的时空,从而与汉武帝的政治权力和千秋功业构成了一种隐含的对话。
《史记》的私心与骚意,比较醒豁的一点即“知己情结”。李长之曾说《史记》是苦闷象征之一种,而苦闷来自于寂寞,来自于知音的缺乏。他最沉痛的事情之一,就是下狱之后“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一点对司马迁历史叙事的影响不容低估。他在《报任少卿书》、《刺客列传》中两次引用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俗谚,作《管晏列传》、《刺客列传》、《魏公子列传》等篇时时围绕着“知己”二字着笔,显然与其“私心”有一定关联。《管晏列传》对管仲功业仅粗略交代,却将管、鲍之交作为焦点。对晏子功业亦不甚详叙,而点染其出越石父于缧绁之中并延为上客的插曲。越石父言:“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此言及“缧绁”二字均值得关注。这种叙述策略,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上来说,是舍本取末;从司马迁的心理角度而言,却最能暴露其内心渴求。柯维骐云:“管仲仇也,鲍叔谏之;越石父囚也,晏子赎之,迁盖自伤其弗遇也。”张履祥云:“《管晏传》大约此篇著意全于知己处,故于管晏霸显事殊略,而于鲍叔、越石父事殊详。若曰吾于李陵,不啻鲍叔矣;当世而有晏子其人,吾其为越石父乎!”此真善读书、善审音者也。《刺客列传》的精神,也全在“知己”,像聂政、豫让那样为了知遇之恩,竟不惜毁身轻生,写得那样壮烈,真足以振靡起懦。基于对人生困厄的切骨感受,司马迁对那些“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游侠专门立传,予以表彰,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管锥编》析《蒹葭》、《汉广》云:“二诗所赋,皆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之情境也。”企慕之情,乃《史记》诗心之一端,也是基于知己的匮乏。故而司马迁在论赞中写道:“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又说:“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太史公所倾慕的魏公子地位尊贵,却为一个看城门的老头引车执辔,这是何等的胸襟,与刻深猜忌的汉武帝相比,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这种企慕,源于对知己和美德的渴望,唯有跨越时空之河,与令其倾倒的古人心情遥接,才可以一舒忧闷,正如罗马诗人桓吉尔“望对岸而伸手向往”之意。
与“知己情结”相反的,是《史记》中大量有关“市道交”的描写。真知己是应该像管、鲍那样举贤不避仇,超脱了个人利益的素交,而不是利交。可是在司马迁笔下,滔滔者皆是“市道交”,“义同贾鬻”,孟尝君、廉颇、汲黯、主父偃等人与门客之间的关系也不过像一场生意,有权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更让人感叹的是张耳、陈余,由刎颈之交终至于相互攻杀,司马迁论赞曰:“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这些篇章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与司马迁对知己的渴望是一体两面的。
“死亡心结”是太史公私心骚意的另一个体现。《史记》大致描写了三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一是壮烈之死,一是悲愤之死,一是忍辱不死。壮烈之死,以项羽、刺客、田横及其宾客之死为最。项羽之死,本可以数十字一笔带过,但司马迁却以上千字铺排渲染,滔滔滚滚,纵横变化,“成此英雄力量之文”,“精神笔力,直透纸背”。这是《史记》最绚丽的文字之一,写尽了末路英雄的悲壮。刺客之死,悲壮惨烈,直可以夺人魂魄。至于田横及其宾客,秉持高节,慕义而死,尤为太史公所褒美,誉之为“至贤”。至于悲愤之死,当以李广、魏公子为代表,两人一个是“遂引刀自刭”,后面再加上一段李氏家族败亡的余韵;一个是“竟病酒而卒”,再加上魏国灭亡的余韵。一人陨灭,则家族陨灭;一人不存,则国亦不存。他们的郁郁而终,蕴含着多少言外之意。
在太史公的内心深处,有一颗慷慨赴死的“私心”。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写道:“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又说:“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司马迁个人的“死亡心结”与他的历史叙事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他深刻地思考死亡,关注死亡,书写死亡。他认为,把死亡看得轻如鸿毛,就会像刺客那样慨然而死,毫无留恋;把死亡看得像泰山一样,才会隐忍苟活,以成大业。这与他在《悲士不遇赋》中的说法态度相同:“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因此,他并非“好生”而“恶死”,而是主动诠释了另一种不朽的形式。侯生之死,李将军之死,魏公子之死,刺客之死等等,皆蕴藏着司马迁未能即死之心结,故笔端常带着浓烈的情感。可以说,对死亡的书写,已变成了司马迁自身对死亡的一种心灵体验。
《史记》的私心与诗意,当然不止于此。他的复仇心理,他发愤著书的心理,他的利义之辨,都值得探究。纸短不敷用,这里就不再细说。
三
司马迁的“私心”对文本的渗透,不仅体现在上文所述,也体现在他对故事情节结构的选择。海登·怀特的《元史学》指出,小说家“创造”故事,史学家则“发现”故事,史学家的叙述基于已经发生的、存在于作者意识之外的事件进行,但他也要像小说家那样从混乱复杂的史料中去粗取精,然后展开故事,使历史情节化。在此过程中,史学家如何选择、排除、强调、决定故事要素之间的关系,确立自己所特有的叙述框架,就变得十分重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海登·怀特提出了历史故事的四种情节模式: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剧。这一分类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特点,不过对于理解《史记》的情节模式仍有借鉴意义。总的说来,《史记》的情节模式以悲剧最常见,讽刺剧次之,而喜剧以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那样的浪漫剧则较为罕见。
司马迁身上保留着浓郁的战国纵横气、风云气,有一种规矩缚不住的、超越时代的高贵人格。拥有这一切,却身罹“最下腐刑”的遭遇,于是他把目光、笔墨主要留给了那些悲剧性人物。那些最打动人、文学性最强的篇章所描写的历史人物,皆天赋英才,倜傥不群,却几乎无一例外地悲壮或者郁闷地死去。中国文化本缺少悲剧精神,也缺少对悲剧人物的详尽书写,是司马迁第一次刻画了那么多形象各异却璀璨夺目的悲剧形象,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诗学。通过这样的描绘,司马迁给出了一个基本的悲剧性质疑:为什么那些富有美德的杰出人物总是“公正而遇灾害”,而不轨枉法、品行低劣者却安享逸乐?他在《伯夷列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以及天道表示了他的怀疑,并象征性地将它们集中表述在列传的第一篇,其精神内涵像一条细细的红线,将许多并无关联的人物串联起来。这篇传记曾遭到许多责难,刘知幾以为“龌龊之甚”,程颐以为“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蠡测”,明清人才将此文的诗意一一揭发出来:陈仁锡说此篇“通篇是怨”,“彷徨追赏,言外高奇”,“是太史公极得意之文”;清人章学诚则进而指出此篇“为七十列传作叙例”,“窃比于夫子之表幽显微”;李慈铭则誉之为“古今第一文字”。
司马迁所描绘的另一种悲剧式情节模式,通常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即“困厄—成功—死亡”,如《商君列传》、《春申君列传》、《苏秦列传》、《范雎蔡泽列传》、《伍子胥列传》、《李斯列传》、《淮阴侯列传》等。不管这些人物出身闾阎,还是落魄贵族,面对人生的磨难都没有沉沦,而是隐忍负重,致身卿相。对这些叱咤一时的人物,司马迁抱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商君、李斯一类,虽才能过人,一个刻薄寡恩,一个“阿顺苟合,严威酷刑”,都有自身鲜明的道德缺陷,立身处世不能窥见先机、有所保守,落得个俱被诛戮的下场,司马迁并没有多少同情之心。而对于苏秦、伍子胥、范雎等人,则或为之洗刷恶名,或赞其“弃小义,雪大耻”、“隐忍就功名”,或赞美其能在困辱厄运中奋发自激,文笔奥衍闳深,烟波迭起,气脉沉雄,适与他们的奇伟人生相称,也与司马迁“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隐衷恰相呼应。
阅读这些悲剧性故事时,我们感受强烈的不是国家、群体给予了他们勇气和力量,而是个人面对厄运时的所思所为,是与命运抗争的个体的坚韧人格赋予他们卓绝的魅力。在司马迁笔下,几乎没有一个英雄人物成为权力的玩偶,他们可以被毁灭,或者主动走向死亡,可是他们身上始终蕴涵着一种巨大的个人能量场。在司马迁之前的那个时代,个人私义大于公义,甚至高于国家利益,一个人的出处行藏完全以自己所遭受的待遇为准则。豫让恪守的知己准则很有代表性:“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从这一完全基于个人的准则出发,他们追求富贵功名,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活得真实潇洒、淋漓快意。哪怕只活过二三十年的光阴,也让生命迸发出夺目的光焰。
四
《史记》的历史诗学,离不开讽刺。
司马迁喜欢在帝王的脸谱上画上几笔小丑的髭须,进行漫画式的描写,《高祖本纪》、《项羽本纪》中对刘邦流氓嘴脸的描写就是如此。可是更多的时候,他更喜欢不动声色地实录式讽刺,只是将相互矛盾的东西捉置在一起而不加判断。汉文帝以仁慈寡欲称,可是在《佞幸列传》中写他宠信邓通、赵同、北宫伯子,甚至允许邓通铸钱致富。《张释之冯唐列传》还写了文帝的三次怒,一是因为有人惊了他的马,便要将那人处死;二是要将偷盗高祖庙玉环者处死;三是写冯唐批评文帝“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司马迁用互见法,也对文帝滥用佞臣、内心多欲给予了婉讽。与善于纳谏的文帝相比,对景帝、武帝的刻薄猜忌、多欲的讽刺就更厉害了。弗莱曾说,反讽性文学的中心主题就是英雄人物的消失,而《史记》的反讽主要体现在他强烈的“贬天子”倾向。李长之说《史记》“尽了讽刺的能事,也达到了讽刺的巅峰”,讽刺的矛头就是他所身处的朝代,焦点是汉家帝王的刻薄猜忌、外宽内深,尤其是对准了汉武帝,这都是很有道理的;而对于公孙弘、张汤等人揣摩上意以肆其志,田蚡等人靠着皇亲国戚的身份弄权倾轧的行径,司马迁同样是嗤之以鼻。
《史记》中“言此实彼”的辛辣反讽有很多,“赞语若雅若俗,若正若反,若有理,若无理,若有情,若无情,数句之中,极嘻笑怒骂之致,真是神品”(李景星语)的《滑稽列传》就不必说了,“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专门充当帝王爪牙的《酷吏列传》的冷讽刺也不必说了,单说说《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的对比讽刺吧,这与司马迁的第一个“私心”联系最为紧密。就将略而言,李将军似远逊卫、霍。黄淳耀云:“李广非大将才也。行无部伍,人人自便,此以逐利乘便可也,遇大敌则覆矣。太史公叙广得意处,在为上郡以百骑御匈奴数千骑,射杀其将,解鞍纵卧,此固裨将之器也。若夫堂堂固阵,正正之旗,进如风雨,退如山岳,广岂足以乎此哉?卫将军数万骑未尝挫,其将略优于广远矣。”王治皞《史记榷参》亦曰:“两人(卫、霍)固将才,规其辞令布置,则其成功非幸也,一时制胜,必有可观。史特不快武帝穷兵,并没其事,若目为佞幸也者,意亦苛矣。出塞之功数百年来无能继之者,则其功岂不较著哉?”刘愚《读史记卫青霍去病传书后》于《史记》书法,亦有微词:“若徒以和柔自媚,未有以称,余弃粱肉,穿域蹋鞠,而掩其大德,未免刻舟之论矣。”此论甚辩,或近实,亦非不知司马迁诗心骚怨者也,却以成败论英雄,太史公不取焉。武帝时代的人物,《史记》仅为魏其侯、武安侯、韩长孺、卫、霍、平津侯、主父偃、司马相如与李广等数人立传,这些人有的专横跋扈,有的曲学阿世,有的则靠的是裙带攀援,唯有李将军以名将称,相如以文采名,良史褒贬,《春秋》遗意,有足多者。《黄氏日钞》曰:“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两千里,声震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将李将军传与卫、霍传合观,是一种探骊得珠的方法。《卫将军骠骑列传》实在是皮里阳秋之文,而翔实、简洁与朴赡兼而得之。写得最翔实的,无过于“封侯”一事,不厌其烦,竟至三十余次,甚至连卫氏襁褓中婴孩亦得封侯一千三百户。甚矣哉,汉武之滥封!李将军一传,“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而李广却数奇不侯。甚矣哉,汉武之吝封!正反着笔,遵循着司马迁最擅长的对照律笔法。卫霍传又有“天子曰”七次,“匈奴入”四次。蒋彤《书卫将军骠骑列传后》曰:“自古文武材类,生于世禄,选于学校,论定于司马,而乃以一女宠获两大将,但其好兵与色之念相为倚伏者耶!而二将军之功,必至天子亲言之,则天子之意也。纪汉之出,必纪匈奴之入,则兵端启自我,而祸延于无既也。纪汉之出所获,必纪匈奴之入所亡,而凡计两将军及诸裨将之斩捕封邑之数,则获不如亡,而功不足蔽其辜也。”最能照幽烛虚,洞达太史公微旨。一言以蔽之,《卫将军骠骑传》写的是卫、霍的兴盛史,《李将军传》则是李氏的衰败史。一内一外,一贵一贱,犬牙交错,草蛇灰线,司马迁的“私心”有若天机潜伏其间而不露声色。钱锺书《谈艺录》云:“古人有诗心而缺史德。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史德有阙,则不能秉笔直书;为存诗心,或废史德。《太史公书》号曰实录,而私心史德,熔裁一体,圆神兼备,虽有曲笔,而未掩卫、霍之功,别具幽微。
五
诗与历史是一对并不友善的敌人,借助于对古典时代倜傥不群之人的追怀,借助于文学所擅长的想象和修辞,司马迁让它们实现了和解,以一种诗意的、抒情的方式重现既往,表现时代的精神,体现出他对个人命运、天人关系、治乱兴衰以及死亡等大问题的诗意诠释。他站在个人命运的分水岭上,恰巧也站在了历史的分水岭上。他是古史学之终结者,也是新史学之开山。表面上看来,他是一个相信“五百年代有王者兴”的循环论者,实际上却是一个怀疑论者、反讽论者。海登·怀特曾这样评述布克哈特:“布克哈特审视着这样一个世界,它通常会背叛美德,扭曲才华,滥施权力而服务于更卑鄙的目的。他看到自己的时代中少有德行,并且没有什么值得他赋予绝对的忠诚。他唯一的投入便是旧欧洲的文化。”在这个方面,司马迁与布克哈特很相似。诞生《史记》的时代,正是一个新的中央集权臻于鼎盛的冷酷时代,他唯有不停地回望三代以及春秋、战国的历史废墟,从那里寻找美德以及个人本位的励志故事来缅怀个人的黄金时代。要知道,以孔子、伯夷、魏公子、刺客、游侠等人为代表的博学笃行、积仁洁行、不耻下交、赴人急困、重义轻生等种种美德,都似乎要随着旧时代一起逝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