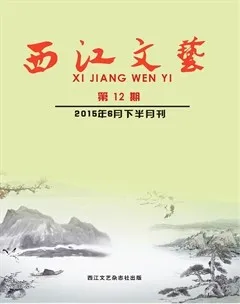从“道不可言”看人类语言表达的困境
李郁瑜
【摘要】:“道”,是老子哲学上的最高范畴,是老子所有思想的核心。《老子》中前后出现了七十三个“道”字,在不同章句的文字脉络中,具有不同的义涵:有时指形而上的实存者,是构成世界的实体;有时是创造宇宙的动力,促使万物运动的规律;有时又是人生的一种指标,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本文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为切入点,从“道不可言”、“意不称物”谈人类语言表达的困境。
【关键词】:老子;道;语言表达;困境
“道”,古已有之,《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有“形而上学谓之道”。“道”是老子哲学上的最高范畴,在道家经典《老子》中前后出现了七十三次。这七十三个“道”字,虽然符号形式是同一的,意义内容却不尽相同:有时指形而上的实存者,是构成世界的实体(如第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有时是创造宇宙的动力,促使万物运动的规律(如第七十三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严而善应);有时又是人生的一种指标,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如第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本文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为切入点,从“道不可言”、“意不称物”的角度,谈谈人类语言表达的困境。
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是通行本《老子》第一章的文字,出现了三个“道”、三个“名”。第一个“道”字是人们习称之道,即今人所谓“道理”;第二个“道”字是动词,言说的意思;第三个“道”字是老子哲学上的专有名词,在本章意指构成宇宙的实体与动力,它是永恒存在的,故而称“常道”。第一个“名”指的是具体事物的名称;第二个“名”字是动词,称谓的意思;第三个“名”字是老子的特用术语,是称“道”之名。“玄者,深远而不可分别之义。”(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玄者,幽昧不可测知之意。”(吴澄,《道德真经注》)这段话是说:可以说出的道,就不是常道;可以称谓的名,就不是常名。无,是形成天地的本始;有,是创生万物的根源。所以常从无中,观照道的奥妙;常从有中,观照道的端倪。无和有这两者,同一来源而不同名称,都可以说是很深刻的。
幽深又幽深,是一切奥妙的门径。[ 1]
在老子看来,“道”这个名称(概念或范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常道”之“道”,“常”者,久常、恒常也,故《老子》帛书本就作“恒道”;另一种是“非常道”之“道”,即非恒久、恒常的道。从认识论上说,“非常道”的道是指那些具体之道,“常道”的道是抽象之道,即“道”的一般或普遍。不论是什么“道”都得用语言去道、去说,但在道说“道”的时候,就有了可道和不可道的问题。具体的道是可说、可道的,用语言能够将其内容、涵义等说明说清,而一般的、抽象的“道”是语言无法说清楚的。“常道”的“道”是个超越了相对的绝对者,它无形无状无象,也就无名了。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有明确的诠释:“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涼,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二十一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第三十二章)。天地的原始并无概念名的存在,天地存在于概念之先,独立于思维之外,这种一般、抽象的“道”是不可用语言来说道的,我们只能强行给之以名。这样,就涉及到了名与实的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二
人类是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来感知外部世界的,通过眼、耳、鼻、舌、身等感觉意识器官将外部世界内化,把看到的、经历的所有信息移入,形成自己的判断、思维,构建出自己的意识世界,也就是从“常无”出发以观照天地万物存在的玄妙性,从“常有”出发以观照天地万物存在的状象和差别性。道,作为一种理性抽象的概念、范畴,它是无形无象无名的,正如《老子》第十四章所言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东西。但另一方面,“道”又是有丰富内涵的,这就是对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的概括和指称。“道”,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我们把握“道”,也必须在抽象与具体、理性与感性、一般与个别、本质与现象的对立统一中来把握。
有了内化,就必定有外化。人作为社会化的动物,在生存斗争中比任何一种其他物种都跟需要协作与交流。语言因其便捷、好用、辨义性强的优势成为人类外化内部精神意识世界的主要手段,也成为人类用来表情达意的最重要的工具。“语言是世界的亮点”,语言到什么程度,世界即展现为什么深度。没有语言,交流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语言不是万能的,“道”和“名”不是言辞所能说得清的,也就是《庄子·知北游》中所谓的“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可名。”
人的内部世界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大脑这个意识器官最初形成并开始工作是在人出生的一刹那,包括由胎教、母体心境等影响下形成的初始性格;其次,在人的一生中,通过感觉意识器官的张开到闭合,由五种感觉意识器官将外部世界移入大脑,直接塑造起由物自体的映像、影像所组成的立体世界,是人的精神世界中的一部分内容;最后,在上述两方面内容的基础上,大脑运用自身处理信息的机制对旧材料进行整合、处理,最终形成的自己的独特的精神意识世界。我们得“道”的方式就只能是“体道”,即与“道”合一,融为一体。这时所表现、呈现出的就是境界,而不是概念的实在。第十五章描述了一个得“道”者,与“道”融为一体后所表现出的境界状态或形象: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
三
前文已经说过,人类用来内化的感觉意识器官包括眼、耳、鼻、舌、身等五种,外化手段有很多,而作为人类表情达意最重要工具的语言,只能通过口来传达,内外化本身不具有对等性。换句话说,语言的体现形式是语音,而人脑中精神意识内容的存储却并不只以语音形式存在,它有可能是以触觉、视觉、嗅觉、味觉等其他形式。用语音形式表达的内容不一定是以语音形式存储的,它有可能是触觉、视觉、嗅觉、味觉,人脑中所存在的精神物质实体远远大于所表现出来的东西。
首先,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在人的内部世界形成的第二阶段由感知的深度、广度所决定。没有感知到的东西,语言是无法表达的。对“道”,这样一个永恒无限的超越绝对实有的东西是无法认识清楚的,因此便不会得到一个明晰的概念。
第二,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是通过意识焦点实现的,而意识焦点的照亮是有条件的。意识焦点是人的内部世界运动变化的主要方式,当声音和声音所表示的精神意识内容被意识焦点同时照亮时,二者就关联起来,这就像一把可以随意转动的“探照灯”。被探照灯照亮的意识内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处理,这样,我们就能快速、精确地找到被注意的事物。大脑的注意系统随着“探照灯”从一点快速移到另一点,如果声音和声音所表示的内容没有被意识焦点同时照亮,我们就无法进行合适的表达。
第三,语言不能表达所有的显意识内容。人类精神意识内容分为两大部分:潜意识和显意识。潜意识的关注点在运动的事物,它把握事物的轨迹;显意识定格在静止,更多的是捕捉事物的静止状态。人类是倾向于孤立、静止、片面的,因此更多趋向于显意识内容的表达。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显意识内容都能被语言表达出来。酸牛奶的滋味只有喝过的人才知道。一些可感受特性问题也是语言无法说清楚的,如怎样解释红的程度和痛的程度。
第四,语言和人的心理意识不是等同的,只能是局部的表达。说出去的话本身就是心理音响的变形,把一个在大脑中以心理音响存放的东西,通过嘴巴转化为存在于外部的物质的音响形式。
第五,语言本身的概括性和模糊性决定了语言不可能充分地表达尽事物所包含的所有意蕴。因为,当人们用语言来表达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内心的情感时,只能采用大致的概括性的语词,在表达中必然舍弃、省略对象本身的许多细微的内涵。正如黑格尔所说:“语言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人类没有足够的语言符号与丰富、复杂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相对应。概括性的语言就像一张巨大但又稀疏的网,它经纬有序地网络了整个世界,但同时也遗漏了许多旨趣和意蕴。[ 2]
四
“混沌”是人的基本状态,当人处于一种状态时往往会祈求另一种状态。人脑有清除“糊”的本能,骨子里倾向于孤立的、静止的表达,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第二十五章)
语言作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这也就使得人类在表情达意的时候不可避免的陷入语言表达的困境,不仅表现在个人外化内部精神意识世界的“言不尽意”上,也突出的反映在个体与他体的沟通交流上。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用相同或相似的感觉意识器官内化外部世界,也就是说,具有脑或类脑的人或物,用相同或相似的处理机制来处理相同或相似的精神意识内容,我们感觉到的、意识到的东西具有相似性,人和非人也有沟通的可能,即《老子》二十五章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只要我们能够“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第十四章),用心去体察万事万物,在外部世界的内化和内部世界的外化中实现物我的合一,语言表达的困境就能够得到超越。
注释:
[1] 参见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譯(参照简帛本最新修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73-78
[2] 纪秀生,关于人类语言局限性问题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2003(1).
[3]这里的“自然”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种本然的状态。这种状态“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是天地万物的本源。
参考文献:
[1]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参照简帛本最新修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贺容一,道德经注释与析解[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3]陈国庆,张养年注译,道德经[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4]康中乾,《老子》第一章新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2010(7).
[5]纪秀生,关于人类语言局限性问题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2003(1).
[6] 曹顺庆,中华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7] 韩宝育.语言与人的意义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 F·克里克.惊人的假说[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10] 李晓寒.浅析有声语言外化人类精神意识内容的局限性[J].西安社会科学,2010(8)
[11]任丽霞.论人的精神世界的外化[A].语文学刊,2010(4).
[12]韩宝育.语言概念的延伸与扩展[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