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的枣子
张宪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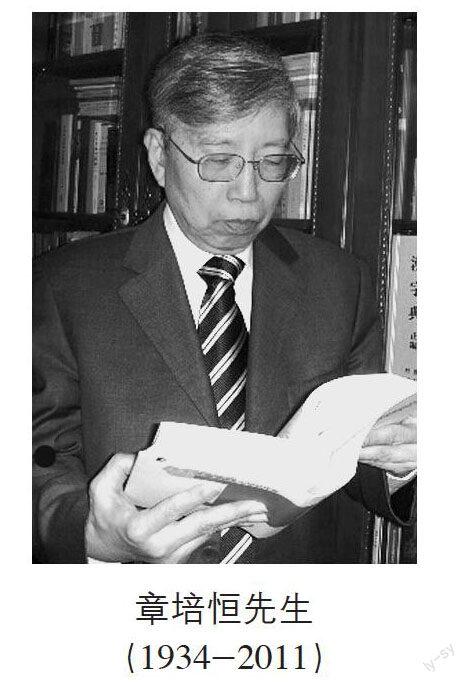


如今的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以是诗人、小说家和文艺批评家,人人都可以自封历史学者,人人都能在网上发表自己混乱不堪且夹杂着谩骂的“见解”,所以人们也越来越不把人文学者当盘菜了。那些老教授再博学多闻,也是盲点多多,怎敌他“谷歌”、“百度”随便一搜?而且人们对于比较深入的学术研究,似乎也渐渐失去了兴味,倒是八卦秘闻更受欢迎,没有了娱乐精神,便不能博得眼球。十五六年前的情形那可是不一样,最好的学者虽说比不上诗人、小说家风光,也比不上那年头随生随灭的商业英雄牛掰,到底还是被不少年轻人奉为偶像的。而今象牙塔里的情形不知怎样,那时人们提到一些老先生,语气神态皆带着敬仰,一副为之牵马坠镫、洗砚磨墨亦心甘情愿的痴愚之态。在我的印象中,章培恒先生(1934-2011)就是其中偶像级的一位。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九九八年秋天第一次听章先生授课的情形。章先生讲“中国文学古今演变”,那天一身银灰色西装,打着淡色领带,带着一瓶乌龙茶上了讲台,有点灰白的头发从侧面盖住了前额,眼神中弥漫着一丝忧郁。没有讲义,也没带书,一口绍兴话不紧不慢地开讲了。那柔柔的音调,很轻,却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说实话,他那身西装很帅,非常惹眼。以后每次上课,他最多带一本书,也常常不翻开,就慢悠悠地开讲了,从《诗经》、《楚辞》一直讲到了《废都》。一边背诵,一边板书,每个字单独看都不太好看,合起来看却很舒服,把笔记完全记下来就是一部书。章先生早年曾受到胡风案的牵连,吃过一些苦头,内中详情非我辈所能知,可是他的脾气、轶事却早有耳闻,学术个性鲜明,甚至有些“好斗”,没想到在课堂上是如此平易近人。原来一个人外表的柔和内里的刚与硬,可以如此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最近在读他的《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边读边生出这么一番感慨来。
厚厚一册《不京不海集》,是章先生生前编定的,包括一九六三年至二○○二年间发表的论文三十九篇,分考证和论述两部分。考证部分二十四篇,以《献疑集》为基础,并增补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所作论文五篇,可以看作文学史实考订的微观研究;论述部分共十五篇,除了两三篇以外,则是关于文学史宏观研究的成果。从这部书的编撰可以看出,在章先生自己眼里,《献疑集》的那些考证文章与那十五篇史论性文学论文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借用王水照先生在该书序言中的说法,章先生的学术品格主要有两点,一是献疑精神和问题意识,“在质疑中坚守精神的自由”;二是“不京不海”、自成一派的风格,“在实证基础上追求理论的突破,自谦亦复自信,胸中自有全局在”。这是很确切的评价。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学术品格,固然与时代有关,与他的师承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和他的绍兴老乡鲁迅有关,和他身上那股强悍韧性的力有关。建国后的三十年,文学成了政治的侍妾,美基本被取消了。而章先生则始终没有被主流观念所左右,而是常常上溯至王国维、鲁迅等人开辟的文学研究之路以及“五四”新文学精神。从高中时代开始,他就熟读鲁迅的著作,《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中国小说史略》等是他征引最为频繁的文献之一,同时自己还写了几篇分量不轻的研究鲁迅的论文。在性格方面他也有鲁迅的影子,硬气、难缠甚至“霸道”,打起笔仗来不依不饶。陈思和先生曾将其概括为“会稽性格”。在具体学术观点上,他一生追求人性解放的义谛,而“人性的解放”一语也来自鲁迅的《草鞋集·小引》。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亦“颇采‘周氏兄弟成说”,“学术统系上,《新著》是对‘五四至三四十年代新文学内部一系列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再发挥”(郜元宝语);另一方面,他非常欣赏王国维的文学史研究,认为王国维不仅在宏观研究的途径与方法上提供了范例,且所持文学观念与鲁迅一样,“都是在那时的中国最接近文学的特征的”。这也可以看出,他虽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文学,却具有强烈的现代精神和贯通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够不局限于古代,提出古今贯通、文学演变的说法。
有人将章先生的学术品格概括为“不媚俗、反旧论、立新说”,征诸实际,确是如此。早期的论文,多属考证之作,往往对主流观点和乡愿之学提出质疑,善于发现新问题,挑战旧观念。这些论文曾结集为《献疑集》。仅印了一千册,却对不少人产生过影响。章先生在自序中曾说:“集中之作,都耗过一番心血,没有一篇是随声附和的;而且我提出的看法,几乎跟眼下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见相左,有些则……是向被公认的见解挑战。”这不是自夸,而是隐隐带着些自傲,他对学生随和,可是对有些学者,他身上始终有一种傲骨在。他的考证文章,往往由细微处入手,又能以小见大,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方法和考证艺术。后期的史论性文学论文,包括关于先秦文学的一篇、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三篇、宋代文学一篇、明清文学的四篇、现代文学的四篇、其他两篇,多从宏观角度论述了某个时代文学演变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立意高远,凸显了他与众不同的文学史观。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一文中,章先生把自己的文学观念概括为四点:第一,肯定文学的本质或其根本职能在于追求和提供美感,至于教育意义之类,则不属于文学价值的范围;第二,对读者通过怎样的途径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美感具有较为通达的认识;第三,充分考虑到作家与读者得以在感情上沟通的基础—共同的人性,同时还要考虑到人性是一直处于发展之中的;第四,正确地认识形式与技巧的重要性。这四个基本观察点,各有其内涵,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观念有诸多差异。借着这些文章,他在向他所钦敬的前辈—王国维、鲁迅致敬,并努力将他们开辟的河流疏浚加宽。
对文学作品的美感考察,章先生从文学本身的特有属性出发,对六朝文学评价很高。他先后撰写了《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再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试论六朝文学的主流》三篇论文,高度肯定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尊重个性、自我意识的加强,认为华美与自然结合、致力于美的创造才是六朝文学的主流。他最爱引用的是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下》的一段文字:“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对萧纲提倡文章华美的看法也非常重视。甚至对一向遭人诟病、被闻一多称为“人人眼角里是淫荡、心中怀着鬼胎、发妻也就成了倡家”的宫体诗,也从文学之美的角度给予了肯定。例如萧纲的《咏内人昼眠》,一向颇多恶评,而章先生则认为诗句“比较真切地传达了一种美的印象,因而是一种进步。至于所谓色情的成分,实在很难感觉到”。郜元宝先生曾说:“章先生论文,极其推重刘勰,但批评刘勰‘原道、‘征圣、‘崇经的儒家保守思想,兼及后世一切载道观念,而肯定‘言志、‘缘情与‘性灵诸说。他反复赞扬萧纲的‘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也再三征引萧绎的‘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情灵摇荡。”(《当思古鼎初造时》,《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郜文又说:“清楚地记得,他是那么绘声绘色为诸生解释梁简文帝萧纲《咏内人昼眠》的‘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两句诗,盛赞其描写细腻,观察真切,虽然香艳得很,但章先生端然授之,诸生也俨然听之。”我也很幸运,曾在课堂上听他背诵过这一段文字。
以人性的发展作为考量文学发展历史的重要指标,是章先生较早形成而又几经波折的一个重要观点。当初一心要考进复旦,就是因为读了一九九六年版《中国文学史》的导言而十分心折,那是人性论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次集中表达。章先生曾在一次学术访谈中说,将人性发展纳入中国文学的演进研究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最初得益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以及胡风等人的思想。“文革”结束后,读了《神圣家族》等马、恩原著后,重新印证了原先的观点;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关于《金瓶梅》、“二拍”的学术论文中这一观点已经初步呈现出来。(以上参见章培恒、马世年《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章培恒先生学术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这表明人性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章先生一以贯之的看法,它的第一个思想渊源是鲁迅、胡风等人的相关论述。他对鲁迅关于“人性的解放”的思想非常重视,为此专门撰写了《鲁迅的前期和后期—以“人性的解放”为中心》一文,并且把鲁迅的思想和他人性论的另一个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结合点。他个人或许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却常常把它用来为自己的所谓“疑端异说”张目,反对用群体意志压迫个体自由。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与这一人性论紧密联系的,是章先生对文学作品中重货好色的“人欲”、个性、个人意识的肯定,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考察。早在一九八三年发表的《试论凌濛初的“两拍”》一文中,他就以李贽的思想为基础,对“两拍”重货好色、个性自由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发表于同一年的《论〈金瓶梅词话〉》,则对《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描写作出了重新评价。这些在今天或许已成为常识,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在那个社会风气开始转变而思想仍显刻板守旧的时代,却是相当大胆的看法。它们虽没有明确提出人性发展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但思想的萌芽已经开始生长。到了一九八九年的《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别》,则从群体与个体的关系的角度对《诗经》、《楚辞》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诗经》中占支配地位的是集体意识,而在《楚辞》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则是个人意识,两者的差异导致了南北文学发展的不同走向。对这个问题的阐释,仍然得益于鲁迅的相关论述。陈建华先生曾精辟地指出,章先生关于人性的具体论述离不开“个人”、“个性”、“自我”、“自我意识”等充满活力的关键概念,并围绕着它们建构了一个富有特色的批评体系:“简言之,以和谐社会‘联合体为终极关怀,在古今演变、中西参照的视域中,坚持语义为基础的实学,运用宏观与微观、理性与激情相结合的辩证方法,从文学传统中挖掘与诠释‘人性的解放、‘美的创造的民族感情与精神的历史,与世界人文价值接轨,使文学史与时代的脉搏息息相通……”以此为出发点,他对古代文学中张扬个体精神的作家—如屈原、阮籍、李白、杨维桢、唐寅、李贽、龚自珍等人—给予了很高评价。有学者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回答如何改变社会文化与个人思想时,采取了一种以个人为单位的个人主义改造方略”,“不仅倡导以个人自治为基础的自由和独立,并辅之以历史进化的乐观信念,深信自由民主是历史进化的胜利与未来,历史进化的动力在于自由和独立的个人”。(杨贞德《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个人》第6、7页,三联书店2012)梁启超、鲁迅、胡适、梁漱溟等人都采取了这样的思想路径。章先生的这些概念链条,既是对五四前后这一思想资源和方法的确认(其中尤为倾心的是鲁迅的思想,而对其他人很少涉及),同时又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融入了自己的思想和人生感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时代感。
史论性文学论文所体现的另一个重点是古今贯通的文学理念。基于文学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割裂开来的现状,他最早提出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术命题加以纠偏。他不仅对古代文学演变过程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阶段做过深入的研究,而且尤为关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贯通问题。发表于一九九九年的《不应存在的鸿沟》一文认为,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分为两家以来,就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只有填平它才能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树立准确的坐标,准确地探究中国文学整体演化的趋势。《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是《不京不海集》的压卷之作,也是最能体现他打通古今文学理念的论文之一,文中提出把二十世纪初期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应视为新文学的酝酿期,并以人性的解放为例作了自己独出心裁的论证。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先前都曾在我们的课堂上讲过。比如,他认为俞平伯的《花匠》源于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就写进了《不应存在的鸿沟》。再如,他讲课时提出“《玉梨魂》这类小说是从《红楼梦》到新文学的比较自然的演变,已经包含了西方文学的特点”,是追求人性解放的一个例子,后来被写入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与对文学美感、古今文学演变的强调相比,对“人性解放”内涵的解释以及运用此一解释对古代文学的重释在章先生的批评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所谓“人性的解放”,包含了个人本位、肯定自我意识、反对各种各样的群体对个体及其自由的压制与束缚等内涵,与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息息相通,并贯穿在几乎全部的史论性论文中,成为他重释古代文学发展的根本出发点。西人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章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是本着人性解放的精神,从现代出发,以现代文学为坐标,去追溯古代文学中具有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东西,以揭示被主流话语所排斥和遮蔽的东西,从而参与到当下精神话语的探索之中。
章先生有一本随笔、论文集,叫《灾枣集》,刚出版我就买了一本,至今还摆在我的书架上。这书的书名非“灾枣祸梨”之意,而是“灾难的枣子”。我觉着《不京不海集》中的很多文章,其实也是灾难的枣子,留存着很深的语境痕迹,留给人酸涩的回味。而今,这些枣子表面上也有点“已陈之刍狗”的意思了,“文学是美的”已成了共识,“重货好色”人人皆已肯定并实行之,“人性的解放”似乎也已有了重大进展,然而群体对个体的压抑还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如何重新认识现实和文学写作中的“重货好色”仍然有待探索,“人性的解放”恐怕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些年,我们见证了时代的巨大变迁,见识过不少偶像的崩塌,然而《不京不海集》还是有它独特的地位,不仅仅是一个界碑而已。我们未必赞同章先生的全部观点,尤其是晚年的一些具体观点,也未必完全赞同他这个人,我们也可以尝试发展、补充他的观点,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不媚俗、立新说的勇气,他卓异不群的声音和现实关怀。他从来都是一个独唱者,而不是合唱团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