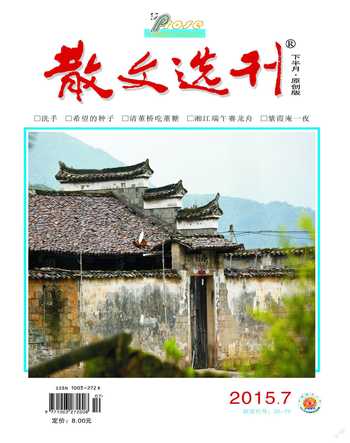祖母的歌谣
辰湄

我的奶奶八十多岁了,耳聋眼花,赶场都走不动了,但精神头还不错,没事就爱唱歌,唱老歌。
奶奶唱歌不择地儿,不摆谱,只要一哼曲子,奶奶仿佛换了一个人,声音温和,满脸堆着笑。奶奶的声音沙哑,语调缓慢,像一把破了的二胡。有时吐字不清,有时忘了词,前言不接后语,支离破碎,但我对这歌声充满了喜爱,说不出的陶醉,我听了30多年,还没听够呢!
“每一首歌背后都有个故事,都有一些人。”摆龙门阵就是必不可少的,像曲子的过门。奶奶总是从她的身世说起,从她的亲娘说起。亲娘高高大大,人才好,是百里挑一的能人,在乡场上租房子开食店,卖炒菜、炖菜,生意红火得很,一到赶场天,好几个帮工忙得团团转。可亲娘一死,生意做不下去,爸爸脾气变坏,后来娶了后娘……奶奶没说后娘对她不好,却唱起了《小白菜》:
小白菜儿真可怜,
七岁八岁木(莫)有娘。
又怕爹爹讨后娘,
一来二晃(去)三年载,
生个弟娃比我强。
她原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亲娘生的,可只长到十几岁就没了。遭遇这场大难的,还有一个弟弟,后娘生的。姐姐那年18岁,眼看就要出阁了,却一病不起。母亲般疼爱自己的姐姐啊,奶奶永生难忘:“姐姐要是不得病,该嫁个好人家……”奶奶又唱起了歌:
姜打铁,李打铁,
打起剪刀送姐姐。
姐姐留我歇,我不歇,
我要回去割大麦。
大麦没有黄,
我守着大麦哭一场。
一个月家里抬出三口棺材,奶奶幼小的心灵填充了极度的恐惧,阴影像一条大蟒蛇潜到梦里梦外,纠缠一生。
像许多乡间女子一样,奶奶这个旧社会过来的人,没有进过学堂,大字不识一个。日本侵略者入侵,国家衰败,民不聊生,能保住一条小命已属不易。可奶奶天生爱唱歌,家务农活之余她悄悄跑到学堂外去偷听:
手提竹篮,
卖哟卖花生,
顺路来到垫江城,
咿得呀得咿得喂。
大姐,你的花生多少钱一斤?
我卖的花生两毛钱一斤,
咿得呀得咿得喂,
进城卖花生。
大姐,日本的飞机怎么样?
日本飞机嗡嗡嗡嗡叫,
洋房子炸成灰,
同胞炸成堆,
咿得呀得咿得喂。
奶奶怕鬼,怕强盗。为了防盗,她想了很多办法:用毛线、稻草,把纸币一圈圈缠起来,再分成几个地方藏,柜子、箱子、米缸、枕头、床板间。奶奶是要把后人们平日的孝敬,留到走的时候递给大家。当年爷爷病逝得突然,手头又紧,她得弥补这个遗憾。爷爷走后,奶奶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卧室睡觉。问她,是怕爷爷吗?她说,不是怕他本人,是怕鬼。但奶奶还是栽种着爷爷坟茔周边的地,三天两头去拔草、锄地、浇水。一边劳作,一边自言自语,一会儿又唱歌:
油菜开花片片黄,
结个媳妇真在行。
堂屋扫得亮堂堂,
灶屋扫得溜溜光。
豆腐划得二面光,
豆腐煎得二面黄。
煮饭煮得喷喷香,
双手抱到桌子上。
公公吃了去赶场.
婆婆吃了进佛堂。
丈夫吃了进学堂,
妹妹吃了进绣房。
这首《油菜花》犹如奶奶年轻时的生活写照。奶奶嫁给爷爷时二十岁,爷爷十七岁。奶奶作为长媳,自然就挑起了照顾公婆、扶持弟弟妹妹的重担。奶奶说:“旧社会的儿媳妇,老的说十句,小的不敢答应一句……”新社会的变化,奶奶始终没弄明白家里好好的怎么年轻人还急着往城里的道路上挤,而孙女月薪三千块怎么还不够用。而她的这一生,也许只有躺在坟里的人真正懂得吧。奶奶对着爷爷的坟头一遍遍地唱:
丈夫吃了进学堂,
妹妹吃了进绣房。
大伯子吃了烂牙巴,
长年吃了打标枪(拉稀)。
唱到最后一句不乏民间幽默的歌词,奶奶忍不住哈哈大笑,眼泪都要笑出来了。我很少见到她如此开怀,一张八十岁老人的脸苍老松弛呆板,却因发白内心地大笑,满脸生动起来一荡一漾的,好像早晨的花儿在一下一下绽放。
都说奶奶本是街上人,却下嫁到乡里来,划不来噢!奶奶不言不语,至于包办婚姻的滋味只有自己心里清楚。有一首讽刺媒人的歌,奶奶爱唱:
胡豆开花青又黑,
好吃媒鬼我认得。
喊声喝酒杯杯干,
喊声拈菜连二三。
世人做媒不要天良,
一进屋把诳话讲,
东拉西扯人光前。
爷爷走了十多年了,奶奶似乎已记不得他的好了,提起他时老是说:“你爷爷啊,就是脾气大,爱凶人!”对于奶奶而言,也许结婚就是和一个男人过日子,就是养儿抚女,至于恋爱她没去想过。
人生多苦厄,片刻得欢娱。所幸奶奶老有所乐,歌声将伴随她度过孤寂的晚年生活。守着老屋,躺在床上,奶奶仰望窗外璀璨的星空,嘴里呢喃:
月亮在哪里?
月亮在哪下?
月亮照进我的房,
月亮照上我的床。
它照着那坡催,
它照着那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