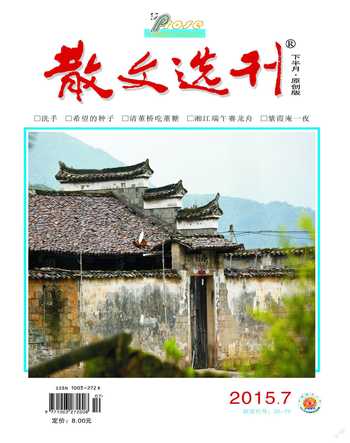欢喜冤家
王俊

“王曼青,我在网上给你买了两件针织衫,这两日你注意查收一下。”隔着屏幕,你敲打出来的字如你平日说话的语气,咋咋呼呼的。
我比你大两岁,从小到大,你一直都这么连名带姓地叫我,却从未听过你叫我一声“姐姐”。二十三岁那年,我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以为你会有所收敛。没想到,你依然我行我素,即便是称呼你唯一的姐夫,你也是随着我一起直呼其名。若是妈妈私底下责怪你不懂规矩,你大眼一瞪,呛过去说:“我叫他们的名字,并不等于我不尊重他们。”
我属虎,你属龙。我们两人还真属有其相,应验了“龙虎相斗”。小时候,我和你被妈妈安排睡一张床。每天早上,我们两个睁开眼就吵架。轮到我叠被子,总是意外地在你的枕头底下找到几个小石子,或是几块小瓦片。每次放学,你跑出去和村里的野孩子玩跳房子、抓小石子。你害怕妈妈发现你“不务学业”的罪证,便将石子和瓦片藏起来。当然,为这事我们争吵,你免不了受到妈妈的一顿数落。晚上睡觉,不爱洗脚的你,胡乱用毛巾擦拭一把脸,偷偷地上床躲在被子里脱袜子。不消说,我们两个若不吵一顿架,谁也不会安心地入梦,但每次吵完架,我们谁也不搭理谁,誓有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
从小学升到初中,你的学习成绩不好不坏,家里墙壁上贴着我和弟弟的奖状,像爬山虎蔓延了整块墙面,唯独找不到属于你的一张奖状。有时,连妈妈都不愿相信,一个肚子爬出来的孩子,怎么就你上课听讲会打瞌睡呢?
老实说,我小时候对你的好远不如对弟弟好。你好斗又喜欢黏着我,我要是独自出去玩,不带着你去,你准要赖在地上哭半个时辰。你不像弟弟那么听话,我说什么他都乖乖地点头称是。在学校里,你的好斗是出了名的,你疯起来的时候,根本就是一个蛮横不讲理的野孩子。
记得有一年中秋,你逛了庙会买回来一条塑料项链,项链的珠子一颗颗晶莹剔透,像珍珠。最巧妙的是它的挂坠,形如一朵含苞待放的玉兰,凑近能闻到细细密密的兰花香味。你把项链递给我看,炫耀地说:“王曼青,你的书能散发香气吗?”我怔了怔,摇头不语。我很想知道,挂坠散发的香气到底是什么东西?趁你不备,我打开了挂坠,里面的液体顿时流淌了一地。见此景,你愤然地将项链扔进了水沟,不依不饶地拽着我袖子推搡着,嘴里直囔囔:“你赔项链,赔我项链!”我自知理亏,一声不吭地站在你面前,任凭你拉扯我衣衫。半晌,你似乎不解气,猛地朝我啐了一口唾沫。我躲闪不及,正中左颊。陡然间,我的火气腾地自丹田冒到头顶,我怒不可遏地推你倒地,骑在你的身上,抡起巴掌责问你:“够了没有,你要是再追究,我就揍你。”你躺在地上,嘴巴一点都不服软,示威地说:“有本事你就打我,谁怕你。”我仅犹豫了片刻,巴掌终于还是落在了你的脸上。其实,在某些遗传基因方面,我和你暗合了父亲暴躁的脾性。只不过,自小我被“乖孩子,好学生”的光环罩着,我的坏被自己掩藏得极其深而已。你气急败坏地与我厮打,我依仗自己比你有力气,死死地钳住你的双手。在你挣扎之际,我跳着落荒而逃,留你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地上无助地号哭。
我躲到稻草堆里,看天边的日头在山峰的掌纹间游戏,尔后藏到了山峦的腹地,方才拖着沉重的脚步慢腾腾地向家走去。
刚溜进院子,迎面遇到了妈妈。她劈头问我哪里玩去了,又问我知不知道妹妹摔了一跤。我模糊地回应一句,自己也不清楚怎么避开了妈妈的问话。走进厅堂,抬头看见你坐在饭桌上正大口地嚼着妈妈炖的排骨。我瞅了瞅你的脸色,一点儿察觉不到你之前伤心的痕迹。你似乎忘记我之前对你恶劣的行为,举着排骨,如同往常般兴奋地喊道:“王曼青,快点,妈妈今天开荤,排骨好鲜。”那一刻,我愧疚得想立即找个地洞钻进去。
小学时,我和你的个头相仿,别人都误以为我们是双生子,分不清谁是谁。等上中学,你的优点显山露水出来。首先是你的个子,一个劲地往上蹿,很快高出我半个头。接着,你的相貌发生了变化,原来蜡黄的皮肤一下子白嫩得像刚剥壳的鸡蛋。大眼睛看人的时候,波光流转。叫人不由得想起《诗经》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出落水灵灵的你,证实了江南果真是出美女的胜地。你勤快而善良,村里的老人几乎都得到过你的帮助。你帮助他们洗衣服,烧火,担水。老人们每次见到爸爸妈妈提及你都会竖起大拇指。妈妈一反常态,对你特别地关心呵护,甚至超越了对我和弟弟的爱。你小时候的种种,全部被你迟来的成长遮掩了。倒是你开朗的个性一直没变,说话的嗓门儿依然大,做事依然风风火火,脾气依然火爆,像一串鞭炮,一点就着。而这时的我,沉溺于席慕蓉和三毛的文字中,与你相处渐渐地没了话题,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婚后的第一年,我的儿子出生了。你比谁都高兴,抱着他问我:“我是不是当姨了?还有啊,我要不要包一个红包给我外甥。”你初中毕业就不再继续升学,选择跟镇里的裁缝师学手艺。你酷爱裁剪,尤其喜欢设计服装。手艺出师后,你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店。因为你年轻,店里的生意并不是很好。可是,你节衣缩食,为你的外甥缝制了许多衣服。偶尔,你还会缝制衣服送给我的婆婆。我诧异地问你缘故,你说:“说你是书呆子,你老是不承认。这人情世故比你书本上学的东西更深奥。我送你婆婆衣服,你婆婆就不得不对我外甥好,是不是这个理?”你的为人处世老到得令我怀疑你这些年必定吃了不少苦,经历了许多挫折。你咧嘴笑了,说:“生活又不是小说,哪有那么多跌宕起伏的情节。”
第二年,你和邻村的一个小伙子谈恋爱。所有人都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凭你的条件,嫁给一个拿铁饭碗的男人绰绰有余。因为你的事,一辈子意见分歧的爸爸妈妈,头一次统一了战线,他们一致反对你的草率。孙子兵法的三十六计,他们软硬兼施,全部使用上。你却以不变应万变,傻乎乎地说:“既然我是鲜花,自然离不开大粪的滋润。我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我只图他对我好。总之,这辈子我嫁定了他。”
也是,罅隙中的草,泥土越是想压住它,它越是破土而出。
结婚后,你生下女儿便随打工的潮流去了浙江。
2004年,在你的资助下,我们买下了一套房子。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而你仍然辗转在外打工,只有过年了才能回一次家。
那年住进新房不久,儿子油漆过敏诱发血液病,住进了市医院。在医院里,儿子的病治疗了一个星期,反反复复不见好。一个前去探望的同事对我们说,与其这么耗着,小孩备受折磨,不如去大城市的医院。
我和丈夫商议,丈夫面露难色道:“说得轻巧,去大城市,钱呢?”
是呀,钱呢?我暗自垂泪。一方面为丈夫的态度失望,一方面为我们的无能感到悲哀。鬼使神差地,我拨打了你的电话。在我们姐妹之间,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对父母向来是报喜不报忧。我内心的忧伤,只能向你倾诉,尽管你从来没和我抱怨过什么。
你朝我大声吼叫:“早就该去上海看病,孩子要是有什么闪失,我绝对饶不了你们两个。”你似乎忘记了我们才是孩子的生身父母。“钱,我来想办法,你发一个账号给我,我明天就去邮局汇给你们。”说着,你在电话里哭得稀里哗啦的。
事隔三年后,我从妈妈的嘴中才得知你当时正失业,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妹夫一人打工勉强支撑着。为了筹集钱,你哭天抹泪地找亲戚朋友打了一个上午的电话。我不敢想象,轻易不肯求人的你,是如何觍着脸向人低头哀求借钱的样子。
前年,妈妈过六十岁生日。碰巧你们办厂赚了钱。你对我说,“你们就几个死工资,大钱我出,你出小钱,表示心意即可。”
晚上,我无意瞥见礼簿上记着我们俩礼金的数目是一模一样的。我明白,你这是帮我们做脸面,不让村人因为我们的寒酸,而质疑我们对父母的一片孝心。
有一天,我向你表达自己的谢意。你的脸红红的,略微羞涩地说:“姐,以前你老是帮我,送我东西。现在我有钱,轮到我帮衬你了。”
你终于叫我一声“姐”了,可我心里堵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