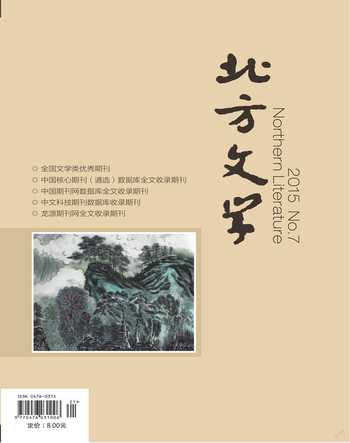《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中的第一人称叙事与成长叙事
刘思畅
摘 要: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既是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处女座也是成名作,其中八个看似迥异的青春故事都从不同成长阶段的男性视角出发,多为第一人称叙事,对青春期的爱、性与死等母题进行了独到的描绘。本文试图从第一人称叙事与成长叙事两大方面来探讨这部小说集的中麦克尤恩的叙事特点。
关键词:麦克尤恩;第一人称叙事;成长叙事;《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
伊恩·麦克尤恩是当代英国著名作家,被认为是英国文坛当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以长篇小说《赎罪》闻名于世。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就是麦克尤恩的成名作——1975年发表的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并获得当年的毛姆奖。这部小说集共收入了八个短篇小说,它们都从成长中不同阶段的男性视角出发,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以意识和潜意识交接地带的经验为解释对象”,在幽暗的主题之下,诉说着多重的人类情感。余华读过这部小说集后这样说:“麦克尤恩的这些短篇小说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精神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精神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他的叙述行走在一条条界线上,他的‘刀刃分隔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温暖、荒诞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的边界”①,张悦然也曾对他的小说做过类似的评价:“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有一条明晰的界线,它锋利地辟出两个对立的世界,少年与成人,暧昧与清晰,天真与世故,孱弱与茁壮”②。麦克尤恩的这种讲述似乎在走钢丝一样,把握着一双双对立情感间的微妙平衡,小心翼翼,却胸有成竹。本文试图从第一人称叙事和成长叙事两个方面来讨论麦克尤恩这八个故事的讲述。
一、第一人称叙事
第一人称叙事是一种以当事人口吻来进行叙述的笔法,作者以“我”或“我们”的身份在文章中出现,所述的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感。一般情况下,第一人称叙述会增加叙事的亲历性,但有时也会因读者对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信任,将读者带入叙述者的思维模式,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带来出人意表的效果。在《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的几个第一人称视角叙事的短篇中,中心叙述者都属于非正常类型的主人公,甚至在心理上有着或多或少的畸形,《与橱中人的对话》中直到十七岁都被当做婴儿喂养的橱中人,《立体几何》中用奇特方式使妻子离开的弑妻者,《家庭制造》中为了找到男性气质而哄骗妹妹进行乱伦的迷茫少年。
《立体几何》讲述的男主人公整日沉迷于曾祖父的日记,对妻子却并不关心,“基本上我只是几下梅西对我说过的话而我又跟她说了些什么”,他在日记中无意发现并破解了“无表面平面”的秘密,并用这个方法将妻子折叠,使其消失。整个故事采用的是男主人公第一人称的回顾性叙述,妻子的一切都通过“我”的话语来传达给读者,在他的眼中,妻子梅西常常会在梦中大喊大叫,并在白天不断讲起她关于婴儿的噩梦;埋伏在厕所门口,用拖鞋将他的头敲破流血;想用塔罗牌这样没有道理的东西矫直自己的头脑,并认为“我”“如此狭隘如此平庸”;摔碎了对于“我”和曾祖父极为珍贵的尼克尔斯船长的身体。而在这样的妻子身边,“我”却似乎表现得十分包容和理性,“下午梅茜往往会风尚茶水,并跟我讲她的噩梦。通常我都在翻阅旧报纸,汇编索引,分列主题,一卷放下另一卷又拿起“,在处理被摔坏的尼克尔斯船长的身体时,“我努力不让自己对梅西的怨恨充斥内心”,这样的叙述声音和细节的铺垫使读者倾向于叙述者一边,但事实上小说里的这位看似理性而有节制的叙述者却是对妻子实施杀害的人,第一人称的叙事使叙述者与叙述文本间的不可靠叙事张力得以体现,男主人公令人恐怖的无情直到小说的结尾才暴露出来,在假装对妻子表示爱意之后,在妻子的愉快与欣慰中,他实施了谋害,在妻子消失的过程中,他这样形容“此刻她的肢体展现出惊人的美丽和人体结构的高贵”,“它的对称具有一种令人神魂颠倒的魔力”,如此不动声色的谋害让人毛骨悚然。费伦将不可靠叙述分为: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③在《立体几何》中,作为谋害妻子元凶的“我”,就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他本身在对自己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上就存在问题,在事件轴上,“我”的回顾性叙事有着严重的偏向,而从“我”的叙述中也不难看出在价值判断上,“我”对自己处于婚姻中弱势一方的角色想象也是一种错误的判断,最后将无辜的妻子谋害时,“我”感到的不是愧疚或害怕,而是一种“魔力”,这种叙感知揭露了“我”的冷漠与变态。
二、成长叙事
“成长”一词总是和青少年联系在一起,个体的成长与发展始终是麦克尤恩小说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里的八个故事,基本上都以成长中的青少年为主人公。成长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少年时代,对于迥异的两个人,却似乎是相通的,有一种属于青春期的特殊语言”,一个人的成长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发育成熟,更是心理上的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甚至贯穿了人的一生,因此,成长具有很强的文化隐喻性,在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中,人们压抑自己的需要以适应社会的客观存在,逐步认知自己的身份与价值,调整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莫迪凯·马科斯对成长小说这样定义:“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事件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了引向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在成长小说中,仪式本身可有可无,但是必须有证据显示这种变化对主人公会产生永久的影响。”④麦克尤恩在《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中对这种像成人世界的蜕变的表现着重体现在母性专制对男性成长造成的悲剧上。
在《化装》中,男孩亨利失去了母亲,由姨妈敏娜接手抚养,姨妈敏娜在这个故事中就是一个有着专制母性的角色,亨利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母亲,“可敏娜是一个超现实的母亲”。她有着强烈的控制欲,因为对舞台的热情无处发泄,她把被压抑的表演欲望倾泻到对亨利的训练上,基于对舞台与观众的幻想,她制定了一套为晚餐着装的规则,并强行让亨利遵守,甚至丧失了理性。起初,这个超现实的世界和现实世界并没有太大冲突,亨利并无察觉地接受着姨妈敏娜的驯化,“他不是敏感而善于内省的一类,只是把这样的新生活和自恋情结看成现实的一部分,毫无意见地接受”,对于心智尚不成熟的孩子来说,这甚至成为了他的一种每日的必需,“亨利接受了这种生活规律,喜欢上了漫长的饮茶仪式和固定的私密时段”,“放学路上他就好奇今天她准备了什么给他穿,希望在床上发现新东西”。但这种带有强制意味的戏剧化场面和真实之间的和谐终究会被敏娜越来越强的控制欲所打破,两种截然不同状态的交错引发了心智尚不成熟的孩子的焦虑与恐惧。一些“可怕的东西”破坏了亨利的穿衣仪式,一套女孩的衣服使亨利产生了强烈的抵触,他甚至不敢去触碰那套对他来说有生命一般的女孩套装,这使亨利第一次感到了性别错位带来的恐怖,并开始认识到自己所处的被姨妈的规则驯化和控制的地位,在专制母性的面前,弱小的男孩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在敏娜的强行逼迫下,他从镜子里看到了“一个令人作呕的漂亮小姑娘”。此时,亨利已经对曾经顺从和适应的敏娜营造的换装世界感到强烈的不适,他的恐惧一方面来自于被敏娜所强制的对不理性规则的遵守,另一方面来自于自身的性别认同挑战——敏娜的强制,使亨利的服装和妆容呈现了和主体相异的性别,同时在这种并非游戏的游戏规则中,迫使他表现出与自身性别相异的行为和语言模式,即迫使他对于自身相异的性别进行认同。这形成了亨利成长过程中的双重认同焦虑,敏娜的强制性换装规则对亨利的驯化代替了亨利成长中本应接受的社会化进程,亨利对拒绝和摆脱这种伤害进行了尝试,但疼痛的消失只是一种暂时。班级里新同学琳达的出现被亨利视为了一种救赎,他试图利用对女生琳达的好感去逃避和克服对敏娜姨妈的女性恐惧,在对琳达产生好感之后 亨利再一次穿上了曾令他失禁和作呕的女孩套装,但这一次他感受到的震撼和上一次不一样,在一瞬间,他感到“亨利和琳达合二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压迫不再,他从敏娜的怒气中解脱出来,隐身在这个女孩里面”,他甚至学着琳达的样子梳理他的女孩假发,并看着镜中的自己翩翩起舞,在这样的瞬间中,在这种和琳达合二为一的错觉中亨利似乎找到了一种解脱,其后亨利和琳达美好而纯洁的亲密接触也使亨利试图通过对琳达身份的认同而逃避另一方面姨妈带来的伤害,但这种尝试以失败告终。亨利最终在化装舞会上明白了自己这番挣扎的无力,他在喝醉之后仿佛看到了琳达正在遭受着自己曾经遭受的伤害,这使通过对琳达身份的认同来进行的自我救赎的希望也彻底破灭,成长的伤痕无法治愈。
《与橱中人的对话》一文是以第一人称为视角的一篇自我陈述,陈述者有着一段畸形的成长历程。他没有出生前父亲就过世,他的母亲同《化装》中的姨妈敏娜一样,有着一种失去理智的控制欲,敏娜的控制欲是为了发泄离开舞台后的表演欲望,而橱中人的母亲则是为了倾泻被压抑的“母爱”,这种母爱的过分发泄形成对橱中人的母性专制。这种母性专制的程度畸形而夸张,橱中人从婴儿开始便被迫充当“她所憧憬过的所有孩子”,直到橱中人十七岁,她仍然像照料婴儿一样地照料他,当这个孩子长大到睡不下婴儿摇床时,这位母亲“跑去一个医院拍卖会上买了张护栏床”,这个孩子十四岁时,这位母亲仍然试图使他坐在婴儿高椅里吃饭,并仍旧喂他糊类的婴儿食物,就这样,橱中人没有选择权利地承受着一种专制而没有理智的母爱,“重复过着生命中的头两年”。这个过程不仅造成了主人公生理成长上的缺陷:无法在正常的床上睡觉,有严重的胃病,直到十八岁才会正常说话,同时更为严重的是对他心理成长的损害,他的心理既非幼儿期,也非成年人,而是偏向了一种扭曲。在“我”十七岁时,母亲无法释放的情感与精力找到了新的寄托,转移到了恋爱上面,这使她对“我”的态度瞬间转变,“十七年里一直罩着你的人,现在却处处和你针锋相对”,为了尽快摆脱“我”这个累赘,她开始迫使“我”在两个月里完成一生的成长,甚至使用暴力来对“我”进行“成长”的训练。这使得“我”没有成长成为一个成年人,而是伪装成了一个成年人,“我怎么长大成人的?我告诉你,我从来没学会过。我得伪装。所有你感到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却必须刻意去做。”在尝试走向社会之后,“我”屡屡碰壁,受到歧视与欺侮,在反抗和希望重回母亲身边的努力无果后,橱中人最终躲到了一间阁楼的壁橱里,从此足不出户。拉康在解释独立自主个体的发展过程时认为,“婴儿最初在想象中将母亲与自己视作一体,并与之情感交融,但父亲以权威的姿态介入二者,强行将他们分开,儿童只有压抑住对母亲的迷恋同时接受父亲的权威才能成为正常人”⑤,而《与橱中人的对话》中的主人公作为一个“婴儿”一直成长到十七岁才经历到了介于自己与母亲之间的权威,但此时他已经失去了生长和发展的能力,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父亲形象的缺失主要来自于母亲的母性专制,这种母性专制是她控制欲的唯一发泄口,和《化装》中的敏娜姨妈一样,这为母亲为“我”制定了本质上和换装游戏规则相同的一套规则和权威,一种母性规则或者说女性规则,这种规则取代了正常成长过程中社会规则的存在,在一开始就逐渐以一种缓慢的方式剥夺和否定了个体的主体性,阻碍了个体自我意识的形成,橱中人一直成长到十七岁仍“不知道自己有其他样子”,也不知道自己的与众不同,甚至他过得很开心,“我现在听起来恨恨的是吧,但告诉你一件滑稽的事,我那时并没有不快乐,你知道。她真的不错。”他甚至希望可以一直这样下去,但由于母亲对自己制定规则的背叛,“我”不得不开始接触社会规则,这使得成长缺失的他遭遇悲惨,而不得不躲进壁橱。
可见,橱中人和亨利的成长都受到了来自母性专制和女性控制欲的压迫,橱中人的母亲用自己制定的母性准则代替了“我”本应接受的社会规则,而敏娜姨妈用一套戏剧化的游戏取代了亨利本应承受的社会化,这两个故事中的悲剧成长角色都试图从其他女性身上寻找解脱,但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因此橱中人和亨利面临着同样的自我身份认同困难,他们缺乏正常的社会互动,女性的专制给他们的成长造成了持久的伤害。因此,麦克尤恩在这样的故事中诉说出了一种由女性的非理性专制而引起的男性成长畸形与自我认同困难,这种母性控制欲造成了他们无可挽回的成长悲剧。
以上即是笔者对麦克尤恩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在第一人称叙事和成长叙事上的一点想法,但理论与阐释终究滞后于创作,这部小说集在叙述上的魅力与灵思远非这两个方面所能道尽。
注释:
①余华,《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作家》,2008,8,1.
②张悦然,《长大就发生在那一刻》,《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2(1).
③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④莫迪凯·马科斯《什么是成长小说》,转引自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⑤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三联书店,2001.
参考文献:
[1]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潘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莫迪凯·马科斯《什么是成长小说》.转引自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余华.《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作家》,2008,8,1.
[5]张悦然.《长大就发生在那一刻》.《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