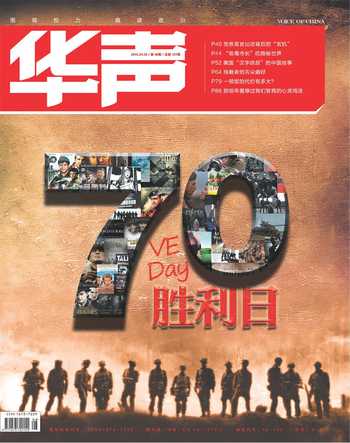代驾:酒精与夜色浸泡的世界
易萱
坐过他车的人都有种穿越的感觉。
即便一身便装时,他也会一上车就报上和尚的身份。
几位客人曾扒着他的脑袋仔细看过他头顶的香疤。
中国的汽车拥有量已超1.3亿,自从“醉驾入刑”规定出台后,代驾行业发展迅猛,他们被认为从事着都市深夜中最有“前景”的职业。
欲望都市
33岁的代驾师傅王樊钢照例在晚上8点开始工作。和大多数代驾司机一样,王樊钢也习惯在家门口接第一单生意。手机发出“滴滴”的提醒声,软件显示,距离他500米的簋街有客人叫了代驾。
簋街曾是北京的深夜菜市。如今这条北京最负盛名的餐饮一条街却总给食客们“日不落”的错觉。一千多米的街道两旁,分布着120多家口味各异的餐馆,空气中游离的酒精与烟火味一样浓。
到达约定地方,王樊钢看到一位斜披着外套、三十来岁的男人正扶在一辆并不干净的银灰色大众车前盖上。他正等着王樊钢开车送他回位于望京的家。
“我不差钱啊……”酒喝得意识模糊的男客人瘫坐在后座,反复强调。话题毫无逻辑地转了又转,从脚上那双价值3000多元的金棕色定制皮鞋,到他正在跟进的融资上亿的项目。“啪,啪,啪”,说到激动时,他猛拍前排座椅。
付钱时,他聊到了与长相近似明星佟丽娅的女友畅游大理的旅行。“我还给她买了条四千多块的金链子,可回来就分了。”男人一边说一边伸手等着王樊钢找零。王樊钢十分恭敬地递给他一元纸币,赶紧离开。对他而言,与醉酒的客户攀谈,是最不划算的事情。
即使在运气好的时候,代驾者通常一晚也只能接七八单生意。晚上9点到凌晨1点是代驾的黄金时间,有经验的代驾者在这期间会不断折返,将上一单客人送到后即刻返回餐厅和酒吧集中的商圈。
王樊钢觉得,具有在人群中随时隐匿的模糊面容,是他作为代驾司机的独特优势。工作中他总是沉默寡言,开口时也始终保持克制,极少使用上扬声调。如果客人不主动攀谈,他更愿意让人觉得车子在自动驾驶,让那些醉意朦胧的人们放心地彻底释放自我。
不过有时,代驾者不得不跳出来阻止一些举止出格的客人。辞去高级安保工作的李龙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和许多师傅一样,收入高、工作时间自由是代驾工作最吸引李龙的地方。每晚从8点半工作到凌晨4点,月收入从当高级安保时的四千多元涨到了一万三四千元。他的女儿出生刚三个多月,每次和客人结账时,他都忍不住想:“今晚要给女儿赚两桶喜宝(奶粉)。”有的钱却是他不赚的。比如,前年一位因醉酒在车上对老婆实施家暴的男客人就让他被迫停车报警。而在深夜,他更会对醉酒男女的互动持审慎态度。“一夜情是一回事,”李龙说,“而迷奸和强奸又是另一回事了。”
代驾“公主”
在北京,每天晚上有数千名代驾者穿行于城中。他们大部分是男性。作为代驾司机中的“异类”,45岁的女司机沈桂莲正尽力以最快速度从西三环航天桥奔向5公里外的西直门。她所在公司登记的代驾者近两万,许多是兼职,其中女司机只有130多位,号称千里挑一。
代驾是沈桂莲最近才开始的副业。一个多月间,她成功服务了147位客人。沈桂莲遭遇过几次拒单,仅仅因为她是女性。她懒得告诉那些人,自己是B照(小货车驾照)持有者,驾龄已近十六年。
而年轻姑娘关玉珍兼职代驾才两个月,却感受到了自己性别的独特竞争力。有时客户见到她时会惊呼:“捡到宝了!”她能拿到比一般男司机更丰厚的小费。曾有客人为了和她多聊会儿天,凌晨让她驾车在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路上绕了一圈又一圈。
关玉珍原本是辽宁电视台一档周播节目的化妆师,如今兼职代驾却占用了她更多精力和时间。在电视台她只是庞大机器上一颗平凡无奇的“小螺丝”,但在代驾圈,却一下成了备受关注的“公主”。
有些人只会在半醉半醒间吐露内心。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坐在属于自己的车上,和一位受雇于自己的司机聊着最想说的话题,这正是一整天中他对生活最有掌控力的时刻。无论是哪种人,他们都相信正在替自己开车的这位,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都远不及自己。
他们很难想象,在西安的夜晚,当90后美女乐乐代驾送客时,她的妈妈正驾驶着乐乐的宝马车紧随其后,作为保镖。一位北京某中央部委的现职公务员,每周也有两三天以代驾司机的身份在街头揽活儿,相较那些说话滴水不漏的同事,他更愿意和酒后的乘客零负担聊天。在代驾群里人们称他“局长”。去年,上海某电视台做关于代驾者的报道,曾苦于找不到愿意接受拍摄的豪车,结果,一位代驾司机主动提供帮助,在他家别墅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路虎和车门设计宛如伸展翅膀的百万级超跑一应俱全。在司机微信群里,一位师傅晒出了自己两年中利用空余时间代驾的收入单——账户余额199872元。
深夜治疗师
一些代驾者所做的,远不止护送喝多的客人回家。
晚上11点20分,北京42岁的光头司机张师傅怀揣着自己的宝贝——一只大肚蝈蝈上了客人的车。虽然在夏季,路边草丛里满是这种喧闹的昆虫,可老张却偏要在冬季花280块钱买一只来养。
每一趟穿城之旅里,这只蝈蝈都是老张最好的谈资。“夏天叫多烦。冬天养(蝈蝈)才有意思,叫得多脆啊。大雪纷飞,我怀揣着它,一边在后海吃铜锅涮肉,一边听它给我唱,那意境,让人心里可太美了。”他给不下二十个客人勾勒过这样的生活片段,劝人家:活着不易,要给自己找乐子。
有客人曾出价2000元想收了它,被婉拒了。老张略带调侃:“我可得给它养老送终。”
那晚的客人——一位身着金色短款羽绒服,职场失意的年轻人——对这套“人生哲学”大为佩服,停车后,他多给了老张几十元小费,毕竟他接受了师傅一次“心灵的点化”。
如果有缘,在上海闸北区,你还可能碰到一位穿着黄色袈裟,法号妙智的“代驾僧”。妙智自幼在苏州万佛寺出家,后来在云门寺受菩萨戒,至今已有几十个春秋,平日里他超度亡者,看家宅风水,招魂驱鬼,忙于各种法事,空闲时则做代驾,有意无意地给醉酒客人“指点迷津”。
坐过他车的人都有种穿越的感觉。即便一身便装时,他也会一上车就报上和尚的身份。几位客人曾扒着他的脑袋仔细看过他头顶的香疤。“有香疤的是和尚,没有香疤的不一定不是和尚,不会诵经的一定不是和尚。”妙智一次次在路上为客人介绍鉴别真假僧人的方法。有时,他们也会讨论一下为什么如今佛门子弟也能用苹果手机、电脑,也会开着豪车出门。甚至有一次,他在车上当场为客人诵了一段经。
人们乐于在车里对他倾诉,或是事业受挫,或是情感失落,或是亲友生灾。即使客人表现得歇斯底里,妙智也只是笑笑,慢条斯理地回应。“待人真诚”、“多做善事”和“心态平和”是他经常给出的建议。当这些寻常话语,在深夜的幽闭车厢内,从一个和尚口中说出,便仿佛附带了法力,常能使听者深受触动,有人抚掌大笑,有人痛哭流涕。
代驾也是一些人自我治疗的方法。一位患有睡眠障碍的女孩在朋友建议下开始代驾,凌晨三四点钟回家后,她竟能轻松地睡着了。一位被诊断为焦虑症的中年人,通过一年代驾,减轻了自己的抑郁倾向,他发现原来大多数人活得都和自己一样艰难。一个有酗酒问题的男子通过一有空就帮人开车成功戒掉了酒瘾。还有一个超重者,通过代驾,半年减掉了40斤。
零点变形记
每个代驾者脑子里都藏着本故事集。
代驾者几乎每天都能遇到酒醉后沉溺于自我幻想的人。一个瘦小、满脸痘印的男律师,感叹自己连续辜负了两个貌美又知书达理的女孩和她们的父母,才落得如今单身的处境。一个操着京片子的中年人,声称自己是中国最早一批世界五百强企业员工,临下车前他愤愤不平:沃尔玛这种美国企业太小气,员工拿了点熟食就被劝退了!另一位喝高了的处长,精神亢奋地表示要给中央领导提意见,甚至当即拿出了手机。
“人呐,就是越缺什么越要说有什么,越怕什么越说自己能什么。”一位师傅如此总结。
也有人找代驾并不是因为喝了酒。他们可能是刚在凌晨与美国总公司开了五六个小时视频会议的外企金领,可能是连续三四天都没回过家的投行员工,也有懒得自己开车的政府官员。一个开奥迪A8,手持VERTU手机的客人让王樊钢印象深刻,他一路闭目养神,却在到家后慷慨地递给司机1000块钱。
按照规定,代驾者不能无故爽约,客户叫单后还必须在25秒内接单,10至15分钟后出现在约定地点。去年夏天,北京一位公司高管深夜回家途中突发心脏病,他机智地打了两个电话求助——一个是120,另一个则是给自己找了位代驾。结果,当代驾司机赶到时,急救车还没来。
喝得不省人事联系不上,或早就被别人接走却不能及时取消订单的客人,代驾者司空见惯。各家代驾公司的激烈竞争中,不时有司机遭遇“假客人”恶意骗单——随口说一个地点就能把抢生意的人支开,让别人傻等半天。
进入后半夜,代驾师傅进入了一个机会与风险并存的时段。朝阳公园西门,农展馆路甲一号的苏西黄俱乐部,店名源自1963年的好莱坞同名电影,如今是贵宾包房最低消费5800元的奢华夜场。凌晨两三点还在这里纵情玩乐的客人,很多已习惯了下午才见到当天的第一抹阳光。
为这些客人代驾往往是获利丰厚的“大单”,因为他们喜欢用小费来宣告自己的身份。
他们习惯在晚上转场两三家夜店,有时代驾者只需要帮其把车子开出来,停在距离不超过500米的另一家店门口。每次挪车,司机都能拿到至少一两百元报酬。李龙接过距离最短的单子是将车从工体院里的一家夜店,停到院外马路正对面的小区楼下。“大概只有二三百米,客人在夜店门口都能指明车子应该停在哪儿。”
每晚,为争夺这些豪车车主的生意,高消费的酒店、夜店、会所门口常常硝烟四起。有时,夜场保安会拿着铁棍,将单独等活儿的代驾司机赶出两三百米远。同一位客人的代驾要求,夜店保安的报价有时是网上接单的司机收费的八倍。
有时候,一个人慷慨与否跟他的座驾有多“豪”也并不直接相关。一个开宝马的男人曾因李龙没有一块钱找零大骂他坑钱;而一位刚被送回家的金杯车主不忍关玉珍冬天里骑车,坚持要再把她送回城区。
凌晨四点,当夜色开始悄悄隐退,代驾群也归于平静。司机们陆续下班补觉。又冷又饿的薛师傅却正在经历自己从业以来最漫长的等待。这并非自我挑战,而是出于职业敏感,他意识到这是单大买卖。从凌晨两点开始,他已守在北京西边一家会所门口。
十个小时后,太阳已划过头顶,他最终见到了自己的客户,一位叫了代驾后又继续在会所里吃喝了一整夜的银行行长,并得到了一份极为丰厚的等候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