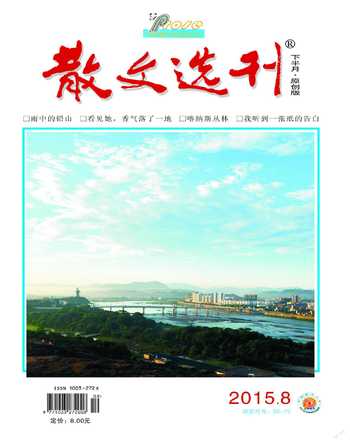亲爱的,我会在二堡街378号等你
张丽琴

雨后
在南方,二堡街是一个隐喻,是一个女人枯瘦的嘴唇,面对生命的絮叨。
所有一个人的旅程,我都不抗拒。孤单的还有古道上,一路呈现的古韵繁体字,它们悄无声息地立在老式牌楼上。白天古典在人们视野,夜晚被现代街灯映照,默然诉说老街背后的辉煌。
风从九弄十三街的方向袭来,我听到了春天里的鸟鸣,看见了童年在风中疾走。而我的灵感,有时坐在工整的丹楹里,有时落在低矮门槛上。
每一个春天
这是一个族谱,是几百年前燕子归来的春巢,是西风里瘦马伊人的路标,是古镇最后一本经卷,在复兴街口默默为你打开。
可否记得,厅堂内有许多雕花的红色木匣子,住着三七、紫苏、雷公藤、蛇胆和马钱子?细细碎碎的中药,在古镇曾止住了多少个夜的疼痛。厅内的白发郎中,仍在镇静白若地为每个病人号脉,日日夜夜从笔尖潦草出多少植物的芳香。他循着清时的处方望闻问切,然后用炭火细细熬出明代的酸甜苦辣,将几代祖传技艺,传承给现代人幸福与安康。
拱形大门之外,人们匆匆地来又忙忙地走,他们有的抱守残缺,有的脱胎换骨。而小小的木匣,它容纳天空大地,日月精华,让我们尝遍世间百味,又归隐于方寸之间。只是每次路过,我都能听见体内传来一声骨骼的脆响,那是我在每一个春天,路过老字号药铺的一道重要程序。
亲爱的,立在百年店铺屋檐下,我紧紧怀揣本草十六大纲,记下一些神奇中药名,如何图解世间的真情?
巷道人家
青石板上,流动着茶马古道的气息。一列列古旧的商号,像一只只陶罐,向我倾倒出碎玉般的传说。
青衫的小贩担着满满的童趣,悠悠地晃过了二堡街的落寞。他手里的银色铃铛、红色拨浪鼓,纷呈响过一道道雕梁画栋,响过勾栏与瓦肆,响彻长长的古巷。那一串干净而绵长的吆喝,将巷道喊穿。人们陆陆续续探出头来,掀开一些不景气的窗帘,嘈嘈,杂杂,切切。
老屋门口,有老大爷的二郎腿,跷在久已失修台阶旁边,时不时搕下一袋陈年烟灰;有被岁月吹弯了腰的老妪,提着扫帚清理门楣上一些力不从心的往事。女人们忙着汲水煮茶,濯衣洗菜,一弯斑驳的石桥静静地横卧于身后,一切是那么的处变不惊,那么的故乡。
夜色像一层糊,缓缓地将他们与老屋黏在了一起。
亲爱的,你是否也在异乡怀抱清风朗月,侧身,聆听那一串绵长的乡音……
天井的光
一束天井的光,险些将我绊倒。我的怀巾盈满了半亩篱笆、一荒疏草的气息。
绿杨庭院,暖风帘幕中已寻不见羞赧挑帘人。而我很想在沟渠边就地打坐,那长短不一的黑,会让我找不到一丝欲念吗?我的忧伤变得古体,这深深的庭院,已将繁衍的空无植入我的体内。
当我缓慢行走,变成了尺椽片瓦的同谋,衍化为岁月成长的一部分,便止不住从雕窗向外眺望,说出屋后那一口永不溢满的欲望之井,说出锯齿形的视角里命定的河山。装满往事的土陶,仍然静止在楼台,注满了瑶台琼室的气息。飘落的花瓣,是否早已飘落在掌心?
我想象着你南极般的童音,如何穿透古陶里的冷,让我呵出胸中一大片废墟般的爱意,然后让心根植于心。
像一只燕子,落在我柔弱的肩上,日夜觊觎我,对思念的不堪与重负。
窗口
河滩上,飘来许多熟悉的乳名。
儿时的窗口,能否把一个翩翩少年,从记忆里轻易喊出来?老人坐在石阶上用古井般的眼神,打量着一切。唯有我和你越来越清晰地走在一首七律或五绝里,试图永久地藏好心灵那一瓢故乡水,藏好我们随时可能在黑夜溜走的思念。天一亮,我就把未完待续的思念,一粒粒孵化成鸟语,放飞在378号的门前……
亲爱的,我愿意把一生记忆的指南针,朝向你,不是只为要一个初见,而是憧憬着又一个重逢。
霞光轻浅,当我成为老街最后一个暮归之人,你会不会牵我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