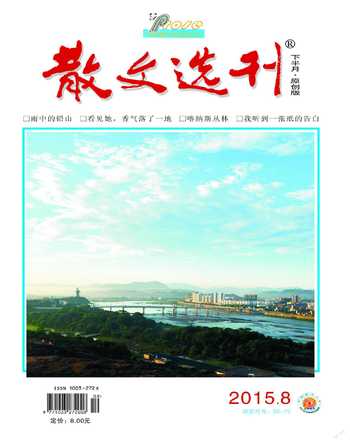武夷山下的徘徊
卢苇
一
五夫镇,又名五夫里,属福建省武夷山市,曾是南宋学者朱熹长期生活的地方。
在巾国历史上,宋朝是个典型,赵匡胤畸文畸武,弱国弱民,定鼎之初就开始了半壁河山的大宿命,所以徽、钦二位皇帝只有到别人的祖宗祠庙里当祭品。继之南宋,麻绳勒豆腐,朽重尤殊。岳飞血淋淋的“精忠报国”和秦桧阴森森的“莫须有”竟然成了世道人心的广告标签,国事的虚诓靡费可想而知。蹊跷的是,本该苟延残喘的儒家义化,竟从荆棘丛巾踏出了一条必通坦途的曲径,窘迫坎坷却又轩昂不凡,费人思索。
朱熹,就是南宋一朝中华文明畸变的答疑键。
由杭州前往五夫镇,途经武夷山,必至一景,是八百多年前,朱熹建造的人称中国“第一座私立大学”的“武夷精舍”。
朱熹一生亲手创建的书院多达27座,“武夷精舍”即是其一。当年朱熹五十四岁,之后又在此著书讲学多年。他七十一年的风雨人生完全可以用“爱学务教,鞠躬尽瘁”八个字来概括。其巾虽然也杂有9年官场状如客串般的尴尬,但无论得意与否,仕宦生涯对他而言只能是固执学教之心的助力和附庸。在他的激情面前,天地等同微末,福禄又何言哉!因为,他的心巾只有天下众生,只有天下至理,只有向学弘道,他始终是个为天下教化而活的人。
石坊之后,即为复建的精舍。马蹄形的屋场并不宽大。正厅三间是讲堂,摆有长条桌椅。当门的墙壁挂有大幅孔子画像,下方为一尊手持书卷的朱熹彩塑,高矮与真人略同,容貌睿智慈祥。两边白墙上写有“忠、孝、廉、节”四个巨大的黑字,是朱熹亲笔的放大体,庄严而且威武。但又因为全是新物,里里外外的一切也让人大有似曾相识之感。侧屋中一堵用白玻全封的康熙五十六年(1718年)书院的断墙,就是面对世事翻覆、时光如梭最真切的表现。
精舍的内外不算宽绰,游人不多,光线也不明亮,我没有细看屋内四壁的图片,白顾白地漫步沉思。我想起了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名言,想起了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词句,检点朱熹的一生,二者兼具,堪为世表。不做良相即做良医,不低头、不屈膝、不谗媚,执着顽强,旷达潇洒,他以特立独行取胜,白塑了卑怯之中的另类伟岸。
朱熹自幼即具异秉,四岁便有向父亲问天的聪慧睿智,八岁则通《孝经》大义,且题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又能与儿童以沙画八卦作游戏。成年后淹贯诗书,凛然正气,十九岁中进士,二十二岁授同安县主簿,上任后出入村社,尽心民瘼,在忠君与爱民累累相悖的拉锯战中开始了学以致用的根本思考和寻觅。朱熹起初倾心佛学,但发现佛学不能真正教化百姓时,立即坚定了儒学志向,扎根在“平实”二字的基础上,逐步培植丰满了儒家理学体系的宏伟架构。“源深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朱熹用自己“居敬持志”“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勇猛精进”的问学积累,为偏安文化的浮侈淫逸套上了断魂索,挺直了真正义人的脊梁骨。
俗言道,千个有头,万个有尾。朱熹人生的主根就在五夫里。但是,五夫里又并非朱熹的故乡。他的祖籍在江西婺源,出生地在福建尤溪。1143年,朱熹父亲朱松去世。十四岁的朱熹谨遵父亲遗嘱,奉母来到五夫里,投靠了其父生前挚友、抗金名将刘子羽。从此,朱熹就在五夫里扎了根,从学、著述、授徒,生活长达五十年之久。他在巾国传统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大多在五夫里完成。
此一阶段,南宋的敌人大金朝已经逐渐步人世称“小尧舜”的金世宗时期,两国从尖锐对立走向缓和妥协。原本激烈的民族矛盾由此派生出松弛麻痹的内囊,是誓死北伐为短时计,还是重塑人心做长久功,横亘朝野,截然水火。由积极主战到“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的坚定主守,朱熹勇蹈地狱,毅然选择了重塑人心做长久功。他不惜一生板荡,用生命的体验去实证“格物致知”,揭示出了中华文明在特定历史时期蕴含巨大张力的永恒的生动。
五夫里,一个偏僻的山乡小镇,竟然哺育了一位中华民族的千古精英。冰山雪莲,凤毛麟角,它的样子到底如何呢?正当我陷入恍惚之中时,前座的朋友突然叫道:“快看,五夫里到了!”
二
五夫里的确很小,也很古。
它起于东晋中期,迄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小镇的主体是一条名为兴贤的小街,长短千米左右,宽窄三米上下,坐落于缓缓的山坡上。鳞次栉比的房舍迤逦展开,蜿蜒曲折,直达坡顶。路面斑驳凸凹,铺面古旧苍然。街巾多有石坊,坊各有名,其上多刻“五夫荟萃”“天地钟秀”等等古气盎然的题词。又有一座小小的过街门楼,两面分别镌刻“三市街”“过化处”数字。细细端详,斜照的阳光、雕花的门窗、静谧巾偶尔的人语与窸窸窣窣的清风,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自在,古朴悠远,让人不知不觉便进入了一种朝圣面佛的意境。
我们在小街上徜徉,现在的小街已全是居民住户,不复街市了。从兴贤书院五彩的门墙前面折转,回到那条名闻天下的“朱子巷”前,轮流在巷口碑石边摄影留念。据说当年长有三百多米的巷道,如今却只剩下三十多米了。巷道两边房屋的坯砖山墙,被巾午的阳光染金了半壁。
我站在朱子巷口朝深处凝望,心巾有一种看透时空的希冀。百步之外的残墙断壁之上,就是空旷无边的蓝天。朦胧巾,我仿佛看见了朱熹的身影,他正臂夹书袋脚步匆匆地向布满卵石的巷道走来。从十四岁开始,朱熹的一生就跟这条小巷结了缘。他由此读书受教,也由此教书育人。他当官从此而出,罢官又从此而归。小巷巾的行走是他一生奔波的象征。在一定的意义上,他留给小巷的数十万个足印,就是儒家理学一脉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轨迹。1153年,朱熹在上任同安主簿的途中拜见了名儒李侗。一番受教,肃然顿悟,从此竭诚为徒。李侗是北宋大儒程颐程颢的三传弟子,是当时直接继承二程学说成就最大的学者。四年后,朱熹任满回到五夫里,全力教书授学,笃研义理,博采众长,著文述志,逐步构建起了理学的宏伟大厦。后世有人称他这次思想变化为“逃禅归儒”,也有人说他是弃禅,可惜都不尽准确。他不是逃禅弃禅,而是离禅,是经过实践和思考后主动选择了儒家学说的“务实”之道,没有也根本不会丢掉对佛老“清静无为”的借重。
从此,朱熹思想中的知行巨流从五夫里的一条小巷开源,滔滔汩汩地奔向了山外的世界。
朱熹虽有大智慧,但仍为俗世中人。在甚嚣尘上的俗雾中,也有过五彩缤纷的慷慨激昂和年少气盛的热血沸腾。他曾经坚定主战,斩钉截铁地上书皇帝“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也”,旗帜鲜明地对和议之害、复仇之利大力宣扬。针对主和派宰辅钱端礼的诸多谬论,厉呼“盖以祖宗之仇,万世臣子之所必报而不忘者”。在《戊午谠议序》一文中借批判“绍兴和议”来抨击“隆兴和议”,借痛斥秦桧来大骂主和派头子汤思退和钱端礼。对宋孝宗的抗金由冒进受挫转而屈膝求和,朱熹即痛心直陈为“臣窃恨陛下于所不当为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举也”,直指乞求“议和”是“逆理”之行,它将使“三纲沦,九法敦,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将使天下“夷狄愈盛”而“禽兽愈繁”。朱熹既敢直言,当然就不怕死。可悲的是已经因符离之败灰心丧胆的宋孝宗并不领情,权臣如钱端礼之流更是死活不容。一心希望天颜尧舜的朱夫子,却接连受挫碰壁,无奈中只有一次次请辞,一次次歇菜,怏怏然退归五夫里。
当年的奉祠,即闲职薄薪休养。朱熹在同安县主簿任满后即奉祠养亲,回归五夫里教书育人。之后三辞京官,坚定居闲,一干二十年。其间,他的学术著作日丰,抗金壮志消歇,把一腔热血逐渐倾注到了儒学理论的知行之中。
但是,朱熹的言行移位绝非甘心悔悟,更非麻木妥协。皇帝不重用,我白重;精英不专精,我白专;天下不知礼,我白教。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四海嚣嚣的慌忙之中,朱熹始终是清醒的。他对官员的昏聩无能曾感慨“今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他对圣道的昏昧曾长叹“若此学不明,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此学即指理学,他是横下一条心要从根底做起,用天下大道去补缀早已乱纷纷的世风人情。
所以,朱熹虽主守却不倡守,拼命以儒学收拾人心,力求从根本上奠定抗战基础;所以,朱熹的主守只能是屈心认和,只能是先知之痛,只能是忍辱含垢的苦修苦行。清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南宋说“统前观后之,前则有将帅而无君相,后则有君相而无将帅,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精辟之论是后来者的清醒。当年的朱熹,却是早就主见在心并一意践行了。永垂史册的“鹅湖之会”就是朱熹在五夫里赍志默行的偶尔峥嵘。
1175年3月,由学者吕祖谦起意,相约朱熹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会集江西铅山鹅湖寺进行学术论辩,史称“鹅湖之会”。会上,朱陆二人围绕“道问学”与“尊德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难。这次会讲活动,在吕祖谦是为调和,在朱陆是为明道,在历史则是百家争鸣学风消遁几近两千年后的浴火重生。
朱陆不会想到,他们辩驳诘难的水火不容,恰恰是南宋偏安哲学两大主流思想的第一次大碰撞。
朱熹曾言“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丰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意思是天下学术上的弊病,无非两种,陆九渊重感悟,陈亮重功业,如果不与它们争辩,理学之道就无法畅行天下。朱熹当然十分明白,能与他的“格物致知”真正对垒的只有陆九渊的“顿悟明心”。至于陈亮的丰功之举,太现实,太急进,虽说断不可缺,但在眼前毕竟是空折腾。一心抱本务实的朱熹,没有也不可能将“实利”重存于心。所以,他能参加“鹅湖之会”与陆九渊激辩,却不会参加13年之后陈亮辛弃疾相约商讨抗金大计的“鹅湖之晤”。对此,朱熹回信陈亮说“奉告老兄,且莫相撺掇……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韫经纶事业不得做,只恁么死了底何限……况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话语婉转意思直白,抗金抗金,抗非其时,抗又何益?于其虚耗无用,何不默头独行。难道你还不明白现在能人太多了吗,不明白锅是铁打的吗?
但是,如果据此就认为朱熹是个抗战逃兵,那就大错特错了。
朱熹与陆九渊的分歧在问学方法,是务虚;与辛陈图谋恢复则为讨论操作,属务实。务虚可务,务实则不可行,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所以鹅湖之会后,朱熹即主动在学术上有了较大的白省和弥补。他曾写信给陆九渊说:“警切之诲,佩服不敢忘也。”又深有所感地告诫学生:“示谕兢辩之论,三复怅然。愚深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就有未合,且置勿论,而力勉吾之所急。
后三年,即1178年冬,朱熹走出了闲居二十年的五夫里,第二次出仕,担任了朝廷命官知南康军。朱熹当然不会改变问学原则,他是在自觉不自觉地修正自己偏执的“情性持守”和“穷理致知”。“出仕”这一结果的主要动因,应该就是他深怀少言的“鹅湖之会”的知行敏悟。
南宋前期,文化上突出的主战派当属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人,朱熹和他们都是朋友且多有交往。朱熹白有抗战之心,但绝不是激越和冲动。他的根子是内省扎实的修齐治平。所以,他的文化同盟只能是理论上的对手陆九渊。朱熹非常明白,陆之长则己之短,只有对照这面镜子,才能找准自己底蕴的不足。所以,他与陆的交往重在问学论辩而非写诗作文,与辛、陈、陆的接触则多在诗义唱酬,寄情于心性的抒张和理解。辛弃疾比朱小10岁,他非常敬重朱熹。曾写诗道:“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把朱比作临溪垂钓的姜子牙。朱熹也极其赞赏辛,对他的大智大勇,不仅报以“施展杰出的才干,以报朝廷”的期许,还为辛的斋室书写了“克己复孔”“夙兴夜寐”题词。朱熹对比自己小13岁的陈亮也极尊重,互访切磋,五年飞鸿,义利驳诘,言无不尽。其实,在主战之上,三人是互为知己的。因为,辛陈的追求正是朱熹无力顾及的事业,辛陈的功业当是朱熹问学之道在现实巾的理想结果。而朱熹的主守,只不过是把在辛陈身上的希望,转化为治学明道的更大努力罢了。至于陆游,比朱熹年长5岁,宦游多在京城、四川,两人接触较晚,虽说情志甚为相得,但毕竟长为参商,少了更深入的契合了。
1193年农历元月,陆九渊病逝于荆门军任上。朱熹曾亲率门人往悼,痛言“可惜死了告子”!意思是,可惜啊,死了宣扬大道的人!朱熹是真正感到孤独的凄苦了,因为他从陆九渊的遭际再次看清了自己主战意志的幻灭。第二年陈亮去世,紧接着辛弃疾遭罢职,两年后“庆元党案”发生,权臣韩侂胄诬朱熹为“伪党”“伪学”。朝廷遂严禁“朱学”。此时的朱熹离去世只剩下不足四年光阴。虽然屈辱,虽然孤零,虽然希望灰飞、年迈多病,朱熹却依然故我,矢志不渝,分秒必争地进行一生论著的整理和承传。1200年3月9日,朱熹在建阳县考亭村住地“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用最后的凝重迎接了自身涅檠。
三
大寒已至,眼看就是春节,却连日艳阳高照,四野蒸腾。走出朱子巷时,我们个个额上已是热汗涔涔,看见不远处有家饭店,立即决定就地用餐。胖胖的大师傅就是老板,待人热情。问起五夫镇来历,老板说:“夫子嘛,就是指镇上胡姓家族五个大名望的读书人,都比朱熹早啊。你们刚从镇街…来吧,朱熹在镇上只是教书,他的住家紫阳楼在镇外,也该去看看哩。”
这还用说,几千里跑过来,紫阳楼岂能不至,半庙方塘焉得不看?
紫阳楼是朱熹义父刘子羽专门为朱家母子盖的住房,位于五夫镇东南一公里开外的屏山脚下。刘子羽后来成了朱熹的岳父。朱熹字元晦号紫阳,楼名当是后人的称谓。远远望去,白墙黑瓦飞檐翘角,林木葱茏气势昂然,令人欣喜。然而可惜,待餐后前往,却叫人大失所望,竟又是全新的建筑。对照武夷山市“五夫古镇”旅游折页中紫阳楼的图片,旧貌已荡然无存。好在门前一棵相传为朱熹手植的八百岁香樟树,枝干苍虬,古风习习,可聊补寻真之缺。
离开紫阳楼,车子径奔南平市。车至南平已晚,简单用餐后即洗漱休息。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横竖睡不着了,便坐起来抽烟。让纷杂的思绪随着四散的轻香,慢慢地伸展开去。
中华历史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三皇五帝不论,从周至宋二千余年,儒教文化的真正走红期屈指可数,且次次都有铁血相伴,充满杀伐。主体的文化人,便只能多有不幸,只能如飘蓬蝼蚁一般的混沌轻贱。其中虽也有殊世孤突者,却又因多不得志,稀见善终,常令后人凄凄而不忍回顾。
艰难与血渍的儒教文化,一路坎坷挨到大宋,似乎见了天眼,赵家皇帝誓以铁卷不杀文人,成就了一段文化史佳话。可惜好景又不长,半壁河山,满打满算才一百六十七年,并非真诚的文化假面终于导致了国势的瞬间崩溃,文化天子徽、钦二帝就成了几乎没文化的金太宗的昏德公、重昏侯两个狗奴才。此后,康王泥马渡江,狼奔豕突,或战或和交叉拉锯全覆盖,儒教文化就只有销声匿迹。
自1127年赵构即位,到1148年朱熹19岁考巾进士,二十年间的南宋文化只有铁铸的“莫须有”三个字。此时此刻,寄命天下、持之以恒的文化人,首推朱熹朱夫子。
朱熹自进士及第,当官50年,立朝40日,辞职多达23次。自劾求免的表面是退避,骨子里却是一种顽强的抗拒。朱熹气概雄阔无比,他一眼看透南宋的滥糟,目光直射千年之外。他指出自三代以降,天下无礼,悠悠岁月只不过是“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的小可怜。既而,针对屈辱的国势和官劣民苦的现状,他连连上书孝宗要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做起,要去旧习、斥邪诐,要“延访真儒,深明厥职者,置诸左右,以备顾问”。在断断续续的为官任期巾,他的恤民、省赋、济粜、办赈济、筑江堤、整士风,他的“访民情,至废寝食”,他的正朝廷、立纲纪、厉风俗、选守令一类的谏议和行动,都是儒家理学的坚强骨骼,都是朱熹在不可为大网之中的心血之为。他的主守之心甚至比主战派的兵刃还要锋利。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上,闻知宁宗登基,立即提斩18名大囚,“才毕而登报赦至,翁恐赦至而大恶脱网也”。为国为民,除恶务尽,大智大勇,雷霆手段,平平主战者何得望其项背!
朱熹生在屈辱的时代,长在庸堕的时期,活在性格扭曲、心志压抑的煎熬中,但他能够隐忍混浊,百折不回。于百姓有益的即力行,对理学不利的即争辩,大道通天,一以贯之,志坚如磐,誓死以求。如此者,大功不成,天理何言!南宋窝窝囊囊一百五十余载,砥柱中流功垂千秋者,魁首朱熹,何人可比?
春秋无义战,大道崩摧,孔子为此痛言“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他选定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条路。面对南宋的沦落朽堕,朱熹则截然不同,他认为自孟子殁后,道统久已不传,如今天命有归,理该当仁不让。
朱熹成功了,他用自身的刚健,传承发展了儒学道统。理学的新生正是巾华民族成长壮大的象征啊。在朱熹构筑的理学大厦之巾,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全是客观进程的渺小瞬间。而这种瞬间,朱熹也作出了明证,它就是微小的坚持。义化天生的就是细致扎实、微小而无尽,从来都不是空言虚浮、媚俗而邀宠。朱熹在委屈巾生,在委屈巾长,在委屈巾成就理学的万古不朽。文化文化,文化何物?如果非要切题,委屈、委屈,无非委屈二字。
我只知道,眼前一直行走着一个孤独的身影,耳边一直响着断续的吟哦:
行行重行行……
唧唧复唧唧……
人皆集于莞,己独集于枯……
虽九死而犹未悔,
吾将上下而求索……
两天后,我们被暴风雪堵在襄阳城内。戊子年的大雪啊,旷古少有。
我猛然顿悟,一声暗喝:“好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