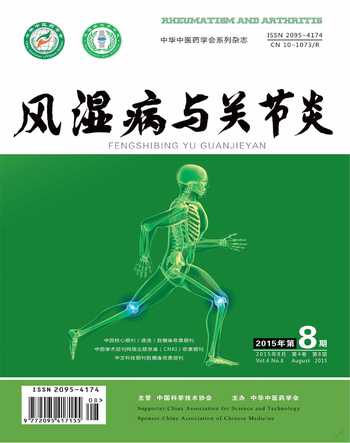中医药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进展
武敏 黄传兵 杨小静 贾建云 杨秀丽 李明 徐友霞 陈瑞莲
【摘 要】 从病因病机、分型、分期论治、单方验方、自拟方,以及外治法等方面对近年来中医药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进行综述,指出中医药在治疗本病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具有一定优势和特色,同时提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关键词】 红斑狼疮,系统性;中医药治疗;综述
doi:10.3969/j.issn.2095-4174.2015.08.017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累及全身多系统多脏器、病程迁延反复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属结缔组织病范畴,多发于育龄期女性,男女发病之比约为1∶5~10[1],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其临床表现复杂,以发热、面部蝶形红斑为主,除有皮肤、黏膜,及关节损害病变外,常累及内脏,尤以心、肺、肝、肾及血液系统损害较为多见,最终导致多系统损害。现代医学多采用糖皮质激素、非甾体类抗炎药、免疫抑制剂、抗疟药和生物制剂等治疗。尤其是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一直居于首位;但因本病病程长,长期用药不良反应较多,其毒副作用不可避免。中医药对本病早有记载,且治疗上颇具特色和优势,恰当的治疗方法,及时合理的治疗,可使SLE预后得到较大改观。
1 中医病因病机
SLE在古代中医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及相对应的病名,古代医家多根据其临床表现及特征将其命名为“痹证”“阴阳毒”“面游风”“茱萸丹”“马缨丹”等。由于本病症状较多,病机、病情复杂多变,常易累及多脏腑和组织器官,虽治法颇多,但病变却难以控制,治疗上反复难愈,故历代医家对其病因病机的认识不尽相同。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说明本虚是导致SLE发病的根本。《医宗金鉴》云:“阴阳毒无常也。”由于阴阳失衡交错,邪毒内阻,气滞血瘀而致病情反复多变,病候复杂,难以痊愈。可见,邪毒壅盛而正气虚惫贯穿疾病终始。《诸病源候论·瘟病发斑候》曰:“表证未罢,毒气不散,故发斑疮,至夏遇热,温毒始发于肌肤,斑烂隐疹如锦纹也。”其中,面部红斑、咽喉疼痛等临床表现为一派邪气亢而为害,热毒炽盛、气营两燔之象。明·申洪良《外科启玄》中有“日晒疮”的记载,认为其发病与日光暴晒有关,最终导致脏腑功能失调,再加上先天禀赋不同,对某些药物耐受程度不同,就会导致五脏气血阴阳受损而诱发本病。
随着SLE的发展及演变,现代不同医家对其病因病机的认识亦有不同。周荣双等[2]以三焦气化失常、气血津液精微物质运化障碍为契机,动态阐释SLE各阶段病机特点,从而进一步对病势转归做出合理的推断。邓志恭[3]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认为,本病是内外合邪,又以正虚为本,是发病之关键,脏腑气血的亏虚是外邪入侵的基本条件。因人体阴阳有盛衰不同,对病邪的反应亦有差异,因而出现不同的病机转化。从脏腑来看,五脏皆能累及,尤以肝、脾、肾三脏功能失调最为常见;从气血阴阳来辨,又以阴虚血热者多见;从标本虚实来看,以本虚标实为多。裴正学[4]则认为,本虚标实为SLE根本病机,以肝肾亏虚为本,风湿热毒为标;发病时则以寒热错杂为主,内外因相互胶结,流注脏腑、关节、四肢而出现各种临床表现。朱方石等[5]认为,肾虚毒瘀为本病主要病机所在,肾虚为本,肾虚不足,百病由生;毒瘀为标,毒瘀内阻,毒邪浸淫,阻遏气机而出现一系列临床表现。夏嘉等[6]认为,“瘀”在SLE诸多致病因素中最为关键,瘀血是贯穿疾病始终的病理因素,是导致本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关键因素之一。
总之,SLE的病因病机复杂多变,不同医家有不同观点;但对本病本虚标实的认识是一致的。其基本病机为先天不足,又以肾阴亏虚为本,或后天失养,导致湿热、瘀毒的产生,而出现不同的临床表现。
2 辨证论治
2.1 分型论治 SLE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历代医家对本病虽有较深入的研究;但到目前为止,仍未有统一的中医辨证分型。2002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首次将SLE统一分为以下6种证型:热毒炽盛型、肝肾阴虚型、脾肾阳虚型、阴虚内热型、瘀热痹阻型和气血两虚型[7]。临床上许多医家常根据临床经验并结合患者的具体病情来辨证选方。
闫秀侠[8]根据SLE在治疗中的表现及特点将其分为4种基本证型:①热毒炽盛型,药用水牛角、生地黄、牡丹皮、赤芍、栀子、黄柏等;②阴虚火旺型,药用枸杞子、熟地黄、山药、墨旱莲、女贞子、茯苓、牡丹皮、泽泻等;③脾肾阳虚型,药用熟地黄、熟附子、山茱萸、白术、山药等为主;
④气阴两虚型,药用黄芪、生地黄、党参、当归、麦冬、玉竹、五味子等为主。
杨坤宁等[9]承孟如诊疗思路,根据SLE临床表现将其分为6型:①热毒炽盛型,治宜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方用犀角地黄汤合化斑汤加减;②阴虚内热型,治宜益气养阴、清虚热,方用知柏地黄丸合二至丸加味;③气阴两伤型,治宜益气养阴、滋补肝肾,方用黄芪生脉饮合二至丸、酸枣仁汤加减;④风湿热痹型,治宜疏风清热、化湿通络,方用木防己汤合四妙散化裁;⑤热邪伤肝型,治宜疏肝健脾、清热利湿,方用强肝汤化裁;⑥脾肾两虚型,治宜补肾健脾,方用《济生》肾气丸合防己黄芪汤加减。
许勇章等[10]根据SLE的临床表现,将其分为以下5型进行辨证论治:①热毒炽盛、气血两燔型,治宜清热解毒,药用水牛角粉、金银花炭、生地黄炭、板蓝根、白茅根、玄参等;②脾肾两虚、气血郁结型,治宜健脾益肾、温阳利水,药用黄芪、党参、太子参、白术、茯苓、女贞子、菟丝子、车前子、淫羊藿等;③气阴两伤、血脉瘀滞型,治宜养阴益气、活血通络,药用南沙参、北沙参、石斛、玄参、生黄芪、当归、丹参、鸡血藤、秦艽等;④脾虚肝郁、气血瘀滞型,治宜健脾疏肝、理气活血,药用白术、茯苓、柴胡、枳壳、陈皮、薏苡仁、赤芍、丹参等;⑤风湿痹阻、气血瘀滞型,治宜祛风宣痹、活血通络,药用黄芪、桂枝、秦艽、鸡血藤、丹参、桑寄生等。
孙海燕等[11]在临床中根据实践,同时参照《中医内科学》及《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将SLE辨证分为气虚、血虚和肾虚3型,治疗以益气养血补肾为法,药用炙黄芪、党参、茯苓、白术、川芎、白芍、当归、生地黄、熟地黄、川续断、杜仲、桑寄生等,在减少西药副作用方面取得满意疗效。
王俊志[12]通过总结临床经验,认为SLE可分为以下4型:①热毒炽盛证,治宜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方用清瘟败毒饮合升麻鳖甲汤加减;②气阴两伤型,治宜益气养阴,佐以清热,方用生脉饮合升麻鳖甲汤加减;③阴虚内热型,治宜滋肾养阴、凉血清热为主,方用升麻鳖甲汤合六味地黄汤加减;④风湿痹阻型,治宜祛风化湿、通络止痛,方用独活寄生汤加减。
综上可见,不同医家对其论治有不同见解;但必须强调的是SLE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病情复杂多变,故临床上应遵循“辨证论治”的原则,“因人施治”,不必拘泥。
2.2 分期论治 SLE临床表现复杂,中医药治疗要明确具体病因病机和证候并非易事,因此,在中医药治疗上除了辨证论治外,依据病情活动度分期治疗往往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陶筱娟[13]认为,在治疗SLE的过程中,从肺论治应贯穿始终,并提出分期论治,活动期主要呈现热毒炽盛、气营两燔,或阴虚内热;缓解期为肺肾两虚,可夹脉络瘀阻及湿毒之邪。
李光宇[14]介绍王萍治疗SLE经验,依据本病病因病机将其分为急性期或活动期、亚急性期及慢性期。急性期或活动期以热毒炽盛、气血两燔为主,治宜气血两清、解毒护阴,方选王萍自拟凉血解毒方加减;亚急性期以气阴两伤夹瘀为主,治宜养阴益气、清热解毒、活血通络,方选自拟益气养阴汤加减;慢性期以脏腑虚损,多见于脾肾不足夹瘀证,治宜健脾益肾、调和阴阳、活血通络,方选自拟经验方益肾健脾汤加减。
高雪华[15]跟随其导师钱先临证学习,认为SLE病程长、易反复,病情迁延不愈,日久便见瘀血之征象,故活血化瘀法贯穿本病始终。急性发作期常以气营两燔为主,治宜清热解毒、凉血消斑,以清瘟败毒饮、清营汤等化裁治疗;稳定期以肝肾阴虚为本、热毒伏于营阴为标,治宜益气养血、滋补肝肾,方选补中益气汤或左归饮加减;后期多以肾虚为主,常累及肝脾肾等脏腑,治宜健脾益气、补肾填精、养肝运脾,方用归脾汤、六味地黄汤、逍遥散、归芍六君子汤加减。
于慧敏等[16]通过对张凤山治疗SLE经验的总结,根据其临床表现将SLE分为活动期和缓解期。急性期以爆发型和急性型、亚急性型、慢性型多见,其中爆发型和急性型多见热毒炽盛表现,治疗除使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外,辅以中医辨证论治;亚急性期以关节肌肉疼痛为主,治宜清热除湿、活血通络;慢性型则以气阴两伤、脉络瘀阻型多见,治以补气养阴、活血通络为主;缓解期可用补气养阴药以巩固疗效。张凤山认为,本病证情复杂多变,要注意随症加减,在邪气衰减时当注意补气养阴以扶正祛邪,当病情好转进入缓解期时继续扶正培本以防再发。
总之,SLE的中医辨证应首分病期,明确病位。由于本病基本病机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故治疗时需分清不同时期祛邪、补虚之主次,通常急性期以邪实为主,应以祛邪为先;慢性期多虚证,又以脾肾亏虚为主,应以补脾固肾为重,辅以清热化瘀等。
3 其他治法
由于SLE病情复杂、变化多端,及病程缠绵难愈的特点,许多医家治疗此病有其独到的见解,在治疗上采用单方验方、自拟方,及特殊的治疗方法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3.1 单方验方 卢桂玲等[17]观察狼疮?号方对SLE患者外周血T细胞免疫调节作用机制,采用狼疮Ⅰ号方治疗,观察转录因子Foxp3基因相对表达水平和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10、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的变化,结果表明,狼疮Ⅰ号方通过上调Foxp3 mRNA的表达,增加了调节性T细胞的数量,平衡了SLE的自身免疫。
雷旭杰[18]结合SLE患者临床使用糖皮质激素易影响人之阴阳,其副作用多表现为虚证的情况,认为SLE在早期大量使用激素时,出现以阴虚燥热为主,可以滋阴降火为法,方选如酸枣仁汤、知柏地黄丸加减;后期激素减量过程中,出现脾肾亏虚为主要表现,可用金匮肾气丸、大小建中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加减进行治疗,在临床减少糖皮质激素副作用中取得满意疗效。
黄煌[19]认为,SLE患者或因先天禀赋不足,或因后天失于调养而成机体亏虚之状,继而外感风湿热毒,内蕴致体内气机紊乱,气血阴阳失调,人体免疫系统功能紊乱,从而致其发病。因此,从体质辨证入手,把小柴胡汤称为天然的免疫调节剂,用当归芍药散同调血水,运用小柴胡汤合当归芍药散(简称柴归汤)及其加味方治疗SLE,疗效显著。
何聘[20]从临床观察的方向探讨导师的临床经验方熟地二至汤对SLE合并血小板减少的治疗效果,治疗组选用熟地二至汤+醋酸泼尼松,对照组选用醋酸泼尼松,结果治疗后中医症状积分、SLEDAI积分的改变,及红细胞沉降率(ESR)、C-反应蛋白、补体C3、血小板计数指标的改变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
3.2 自拟方 何桂娟等[21]针对反复发生口腔黏膜损伤的SLE患者,将范永升根据金匮方调整的可宁汤制成可宁汤Ⅰ号-湿热型、Ⅱ号-虚热型口腔护理液,以观察可宁汤口腔护理液用于SLE并发口腔黏膜损伤辨证施护的效果,患者辨证后在日常口腔清洁基础上分别予常规漱口液口腔护理及可宁汤Ⅰ号、Ⅱ号口腔护理,结果显示,可宁汤Ⅰ号、Ⅱ号口腔护理液施护具有益气养阴、标本兼治之功,对复发性口腔溃疡有确切的治疗作用。
李上云等[22]为了探究血瘦素、IL-10、TNF-α与女性SLE的关系,采用测定糖皮质激素或糖皮质激素联合狼疮汤治疗前后患者血瘦素、IL-10、TNF-α含量,结果显示,糖皮质激素联合狼疮汤降低患者IL-10、TNF-α、血瘦素水平更显著,表明狼疮汤可能是通过降低血瘦素水平,从而调节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对SLE起到治疗作用。
黄钢花等[23]观察清养透解法对MRL/lpr小鼠Th1/Th2细胞因子平衡的影响,结果显示,中药组、西药组、中西医结合组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均能显著降低血清IL-10、IL-4水平,提高血清IFN-γ/IL-4比值,中西医结合组能显著升高血清IL-12/IL-10比值;各治疗组均能不同程度改善肾组织病理形态变化,表明清养透解法对SLE的治疗作用与其能调节Th1/Th2细胞因子平衡,改善肾组织炎性病理改变有关。
张志芳[24]通过观察健脾益肾汤联合泼尼松序贯疗法治疗SLE蛋白尿的临床效果,在现代医学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健脾益肾汤对SLE进行治疗,结果临床效果显著。
3.3 外治法 临床上SLE的治疗主要以口服药物为主,随着疾病的发展及现代医家研究的不断深入,外治法治疗时所发挥的作用亦不容忽视。
刘屹等[25]通过观察六味地黄汤加减联合针刺治疗SLE的临床疗效,将60例SLE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治疗组采用六味地黄汤加减联合针刺治疗,对照组采用单纯针刺治疗,结果治疗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说明六味地黄汤加减联合针刺治疗SLE临床疗效显著,安全性高。
张玉桂等[26]将80例SLE患者分为两组,有规律中医按摩组40例,无规律中医按摩组(对照组)40例,采用SF-36进行问卷调查,同时测量血常规、尿常规、ESR、免疫指标等实验室指标,结果有规律中医按摩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1),说明中医推拿按摩能提高SLE患者的生活质量。
林友燕[27]为了观察五倍子粉贴敷神阙穴治疗SLE运用激素治疗后出现盗汗症状的临床疗效,将40例SLE运用激素治疗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2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辅以五倍子粉贴敷神阙穴,3 d为1个疗程,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表明五倍子粉贴敷神阙穴治疗SLE运用激素治疗后出现盗汗的临床疗效显著,方便安全,且患者容易接受。
卢桂芳等[28]通过对112例SLE伴发不寐患者进行耳穴压豆治疗的临床疗效观察,针对不同患者进行辨证取穴,实证、虚证均取神门、皮质下、心、枕、垂前,心脾两虚加脾、垂前,阴虚火旺加肾、内生殖器,肝火上扰加肝、胆、交感、耳尖,胃腑不和加脾、胃、胰胆、三焦,入睡难而早醒加重用垂前,心跳加快加十二指肠、小肠、耳迷根,每次贴压后保持3 d,10 d为1个疗程,连续治疗1~2个疗程,结果治愈率、有效率显著,说明耳穴压豆治疗不寐有效率高,无副作用,而且其操作简便,费用低廉,易于患者接受。
4 讨 论
SLE属终身性疾病,病情复杂多变,可累及全身多系统、多脏器,且病程长、缠绵难愈,目前治疗上尚无有效的方法,因此,积极寻求有效、方便、安全的治疗方法极为重要。中医学对本病的认识历史悠久,中医治疗不仅能提高疗效,还能减少激素用量,减轻西药的毒副作用,这是中医中药的优势[29]。同时中药治疗在缓解临床症状、延缓病情进展、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等方面,疗效确切、作用明显。目前中医药治疗SLE的研究虽有一定的优势,但仍存在以下问题:①SLE的辨证分型难、方法弥散,缺乏规范性,因此应制订统一、标准的分型方案,应针对SLE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
②中医对SLE发病机制实验研究不够深入,临床研究样本量不够大、资料不够完善,数据缺乏科学性和可信度,今后应加大力度完善;③目前,对于从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不同层次的深入研究较少,今后应从细胞分子学、遗传学和中药药理学等层面探讨中药治疗SLE的疗效、机制,为全面提高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SLE的总体水平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使中医药治疗SLE的优势进一步得到凸显。
5 参考文献
[1] 葛均波,徐永健.内科学[M].8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815.
[2] 周荣双,刘德要,范美丽.“三焦气化失常—系统性红斑狼疮”相关论[J].中国医学创新,2014,11(18):148-150.
[3] 方乃青.邓志恭主任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心得[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18(5):308-309.
[4] 单金妹,张红梅,杨中高.裴正学教授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经验介绍[J].四川中医,2011,29(2):11-12.
[5] 朱方石,金实,汪悦.从肾虚毒瘀论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理论机制探讨[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0,7(11):9-10.
[6] 夏嘉,苏晓.从“瘀”论治系统性红斑狼疮[J].河北中医,2014,36(5):791-793.
[7]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111-115.
[8] 闫秀侠.中医辨证分型联合西药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对照观察[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2,20(10):54-56.
[9] 杨坤宁,郑德勇.孟如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诊疗思路[J].中医文献杂志,2009,54(5):45-46.
[10] 许勇章,韦雄.中医药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效果观察及对部分指标的影响[J].中医中药,2013,11(20):298-300.
[11] 孙海燕,王志清,丁晓庆,等.益气养血补肾法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疗效观察[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医临床版,2010,17(3):4-7.
[12] 王文生,赵玉娟.王俊志治疗红斑狼疮经验[J].实用中医药杂志,2014,30(2):158-159.
[13] 张雯.陶筱娟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经验[J].中医杂志,2009,50(1):22-23.
[14] 李光宇.王萍中医辨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经验[J].环球中医药,2014,7(7):552-554.
[15] 高雪华.中医药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体会[J].江苏中医药,2011,44(1):33-34.
[16] 于慧敏,王晓东.张凤山教授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经验总结[J].中医药信息,2012,29(2):66-67.
[17] 卢桂玲,李群燕.狼疮Ⅰ号方对SLE患者外周血T细胞免疫调节作用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31(11):1573-1574.
[18] 雷旭杰.经方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西药副作用[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3,11(17):109-110.
[19] 王鹤,徐伟楠.黄煌教授运用柴归汤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经验[J].四川中医,2013,31(5):2-3.
[20] 何聘.熟地二至汤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并血小板减少的临床研究[D].武汉:湖北中医药大学,2012.
[21] 何桂娟,卢桂芳,金瑛,等.自制可宁汤口腔护理液用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并发口腔黏膜损伤的辨证施护效果研究[J].护理与康复杂志,2014,13(1):10-12.
[22] 李上云,李海权.狼疮汤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女性患者血瘦素、IL-10、TNF-α的影响[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2,30(3):670-672.
[23] 黄钢花,陈银环,刘叶,等.清养透解法干预MRL/lpr小鼠Th1/Th2细胞因子失衡的研究[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29(4):420-423.
[24] 张志芳.健脾益肾汤联合泼尼松序贯疗法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蛋白尿的临床效果观察[J].社区医学杂志,2014,12(19):46-47.
[25] 刘屹,李澎.六味地黄汤加减联合针刺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30例[J].山东中医药,2014,33(10):809-811.
[26] 张玉桂,陈玉凤,彭成清.中医推拿按摩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3,22(3):263-264.
[27] 林友燕.五倍子贴敷神阙穴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盗汗症状疗效观察[J].上海针灸杂志,2013,33(5):398-399.
[28] 卢桂芳,陆岑娣,史亮亮,等.耳穴压豆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伴发不寐的应用体会[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36(10):1150-1151.
[29] 江春春,苏晓.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中医药治疗研究进展[J].风湿病与关节炎,2013,2(5):50-53.
收稿日期:2015-03-05;修回日期:2015-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