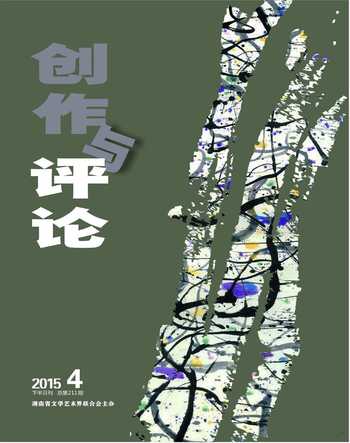不即不离 不偏不倚
李德南
最初知道蔡东,是因为她的《下一站,城市文学》。在这篇仅是两千余字的短文里,她先是以孟繁华教授那引起广泛争议的《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引出话题,认为它“不圆滑,不和气,不点名表扬”,是“一篇坦诚、敏锐而前瞻的力作”,后又顺理成章地揭橥深圳城市文学的困境,不留情面地指出它所存在的问题:“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其格局的狭窄、艺术性的不足、题材和文体的单调也令人忧虑。”①此文写得干脆利落,锋芒毕露,因此,我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并把她视为一位值得留意的批评家。直到后来陆续读到《无岸》《往生》《净尘山》等中短篇小说,我才知道,蔡东更多是一位城市文学的书写者。
迄今为止,蔡东的作品数量不多,清凉店、留州、深圳是其主要的叙事空间,尤其是深圳,在蔡东作品中的位置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她笔下的人物则主要是两种。一是有着传统面影的知识分子,如《毕业生》里的郁金、谭苑山,《木兰辞》里的陈江流,《净尘山》中的张亭轩。他们都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可惜生而为现代人,不得不背负着沉重的枷锁,为现代性的种种幻象所连累。还有一类是城市中的小资或中产阶层,比如《无岸》里的刘萍,《净尘山》里的张倩女。她们也为现代的种种价值观念所塑造,深陷在各式各样的分裂、冲突和困境之中不能自拔。两种形象有时又合而为一,如刘萍和张倩女。写作时的蔡东似乎具有作家和社会学家的双重视力,特别注重社会现实对人物的型构和改写,尤其是人物的职业或生计问题在小说中往往成为一个结构性的要素。
一、 过时落后的人及其生活
我们不妨从《毕业生》谈起。这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名字叫郁金,是一位即将毕业的中文系研究生。因为男朋友在深圳工作的缘故,郁金也跟着南下,希望能在那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名正言顺地扎下根来然后结婚生子,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要想真正融入深圳并非易事。虽然有着古典文学硕士的学位,有着很不错的学术功底和文化修养,但是郁金刚到深圳便已遭受了各种的磨难:到一所旅游学校面试,被告知获得了实习机会却又莫名其妙地被取消。阴差阳错地被公司的老总认可,有机会成为公司的文员,却又因为脸上有麻眼而再次被拒。在努力寻找工作而不得的情形下,郁金不得不将档案暂时交给学校托管,寄希望于下一年能顺利找到工作,同时瞒着远在清凉店的家里人,告知已在深圳找到工作,“留在了深圳的一家公司,跨国的,在一栋六十几层高的大楼上办公。”为了让美丽的谎言显得可信,她还得从男朋友申安那有限的工资中想办法节省钱寄回家里。然而所有的这些,都不过是重重困境中很小的一部分,郁金的重担并未能就此卸下。“还有几天就要给家里汇钱。晚上郁金总做一个梦,她不停数钱,一沓百元人民币,怎么数都不够八张,不是七张,就是六张。数着数着惊醒了……”
虽然“数着数着惊醒了”可能只是郁金个人的恶梦,但是她所遭遇的就业难、学历贬值、向往城市而难以融入城市、深孚众望而又只能卑微地活着等种种困境,在她所属的这一世代和时代中都是非常普遍的。困境的存在,有着明显的社会根源。自然,以貌取人的身体政治古而有之,从来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却尤其发达。蔡东在小说里就不无讽刺地说道,这是一个连男色都要消费的时代。抛开长相的因素,郁金在就业上所遭受的磨难也来自于她所读的专业。从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在中国便已全盘铺开。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逐渐退隐和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大学教育的功能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如今,“对社会来说,教育被具体地看作是培养有某种技能、受过职业规范训练的人力资源的地方。对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来说,受教育也不是为了培养个人的修养而是为了掌握谋生的技能。受教育的根本含义在于就业之前的必要的职业和技能培训。在个人和社会的心目中,某种教育资历和未来的某种职业之间的对应关系成了一种规范。至少,专业资格是具体的职业资格的一个前提条件。”②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古典文学和历史、哲学等经典学科一样,成了“过时的人文学科”,成了“无用之学”。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人往往又是通过职位来获得相应的社会归属的,尤其是像郁金这样缺乏良好出身和家庭背景的年轻人,只能通过职业上的奋斗来获得存在的确定性,进入特定的价值序列。如果一个人丧失了或从来就不具备从事某种职业能力,往往就失去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只能在社会价值金字塔的末端存在。当教育的专业化和经济社会的职业化严密接轨时,过时落后的人文学科所培养出的,往往便是过时落后的人,是时代的失败者或多余人——有很多这些专业出身的学生,甚至一度戏称自己拥有屠龙术,所处的却是一个没有龙的时代。郁金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毕业离开校园之前,郁金从未怀疑过自己拥有的知识,而是认为她所研究的诗词曲赋“历经千年而风华依旧”,“高尚、洁净、关乎心灵、不容践踏”。她本以为,凭着自己的才情和学识将会获得安稳的生活。直到迎头撞上更广阔也更复杂的社会世界以后,郁金才意识到,她所学到的一切,那已经成为个人精神生命之重要构成的一切,在这个时代早已“变得无用、冷僻、蒙尘已久,受到轻视和嫌厌”。作为一个寒门学子,她多年来的努力,似乎就是为了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成为一个过时落后的人。这不能不令她觉得茫然,恐惧,难堪。
这种因时代变化所导致的特定知识与文化的贬值,是蔡东在写作中所特别重视的。她的写作,一开始就接通了广阔的社会世界。除了郁金,蔡东还塑造了好些类似的带有传统面影的知识分子形象,持续地书写他们在现代社会里所面临的各种困局。同样是在《毕业生》里面,蔡东还写到了一个名叫谭苑山的人物。他和郁金是大学同学,年纪比郁金大,入学时已三十五岁。谭苑山读书时曾把乡下的妻儿接到省城,以低廉的价格在大明湖边租了一处房子,过了几年短暂的诗书生活。郁金和同学前往拜访老谭时,也一度为诗意的环境所触动,“都恍然化作古人,说话也文绉绉的”。这种充满诗意、古典而又浪漫的生活场景,一度让郁金觉得十分美好,生出向往之意。然而,当她和老谭同时毕业,都不得不直面严峻的生计问题时,郁金才明白,这种诗意和情调的内里是贫乏的。在这时代,老谭的存在,比郁金还要不合时宜。
《净尘山》里的张亭轩又是一个很好的个案。在小说的开篇,蔡东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他唱昆曲的诗意场景。他原来在一所高中教音乐,出于对高中教育体制的不满而选择了辞职。“那会儿,时代还未突然加速,人们还不上蹿下跳”,然而如今,“世界变了”。一旦新时代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张亭轩便发现,他根本没有抵御这个世界的能力。他后来依然没有找工作,而是潜心学习书法和国画,但这已经不是为了解决个人修养的问题,而是希望重新确立个人在现时代里的地位、意义和价值。吊诡的是,他所做的一切,最后都走向了一个可笑的境地:“欲以润格致富,结果只能过年时为亲友免费写挥春。他专门钻研过演说技巧,期盼跃升到有识之士听他白话还给他钱的完美境界,结果只吸引了小城的一批珍禽异兽。”这种种困境是小说行将结束时才揭开的,张亭轩的形象也由此发生了倒转。他不再是一个值得敬仰的形象,而是一个落拓者的形象。《净尘山》的开篇带有浓厚的抒情气息,故事终了时,抒情却变成了反讽。这当然不只是文本内部的修辞学的转换,而是对时代风气变化的隐喻。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人物形象的塑造、颠倒和文风的转换中,带有传统面影的知识者的尴尬处境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二、中产阶层的多重困境
城市里小资或中产阶层的存在困境,在蔡东的小说创作中也占有特殊的位置。这种选择,与蔡东近几年一直生活在深圳这个城市不无关系。在以往的写作的中,蔡东用了不少笔墨去书写小县城的生活,但是如今,她敏感地意识到城市空间中的广大人群也值得关注,甚至更值得书写。
差不多是在和《毕业生》相同的时候,蔡东还写过一篇名为《天堂口》的小说。它有一个爱情小说的架构,主要是写叙述者“我”因为爱情而前往深圳,希望和男朋友铁帅在衣食住行的朝夕相处中弥合两人的感情。“我”的身份依然是一位文科大学生,铁帅还有他身边的朋友则都是工科出身。铁帅本身的形象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出身工科却文采斐然。“我”之所以和他相恋,不乏文科生对理工科的崇拜在内,小说里甚至不无夸张地写道:“我向来对‘电子‘信息‘工程等字眼肃然起敬,当它们三个鱼贯出现时,简直就称得上光芒万丈了。”由于高校扩招等原因,铁帅和他的同学并没有一开始就受到市场的青睐。然而,他们所读的毕竟不是“过时的人文学科”,比之于郁金、谭苑山等人,他们的职业生涯还是显得相对有生机。小说中有一个场景,写到深圳不久的增贵起身致辞:“今天这种场面,让我开眼界了。看看,冠松和大崔在华为,铁帅在长城,小吴在电信,高波刚跳槽去了惠普,今天跟我吃饭的,全是技术骨干、营销奇才、管理精英啊。他又搂住刘乐的肩膀,说,还有我们的小刘乐,现在他不是小刘乐了,得叫他刘老板,乐——爷!”这一番话不乏调侃的成分,却也喻示了他们就业前景中光明的一面。大概是因为《天堂口》更关注的是爱情话题,所以蔡东在里面并没有对这群理科男的奋斗过程作更多的展开。这一环节的缺失,多少让她的文学世界显得不那么完整。然而读完《净尘山》以后我又觉得,这些痛并快乐着的青年都进入了小说中那位于深圳西北角的华跃技术有限公司。这是一个庞大的高科技商业帝国,每年都大批量地吸纳各种人才,大批量制造出城市中产乃至于富裕阶层。这时候,他们都已经为独特的企业文化所锻造,形成了以下的习性:“熬夜,不运动,亚健康,性格偏内向,信仰埋头苦干和不请假,习得的麻木忍耐,适应高强度工作,以加班为核心价值观。”
在《净尘山》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张倩女。她可视为郁金形象的延续和变形。她和郁金一样,从小就喜欢古典文化,对父亲张亭轩心怀敬佩和崇拜,即使和母亲劳玉一起来到深圳这样的现代城市生活,也仍旧喜欢听母亲讲那带有古朴诗意的昨日往事。不同于郁金的是,她所接受的是工科教育,如今在华跃这家全球著名的通信公司担任项目经理,年收入三十多万,是这家公司所生产的中产阶层中的一员。从职业和收入的角度来说,张倩女谈不上是失败者。然而,职业上的成功,和她在生活上的失败差不多相反相成的。在高强度、高压的工作中,张倩女患上了情绪性的暴食症,急剧增加的体重给她的恋爱、婚姻乃至于所有生活环节都带来了极多的麻烦。和郁金相比较,我们很难确定谁的处境更好一些。
《净尘山》在刻画人物形象时也很注意为人物的困境找到相应的社会根源,在追根溯源的程度上又远远要超过《毕业生》,抵达了反思现代性、反思新文明的层面。《净尘山》里的深圳,尤其是华跃生活圈,是新文明密集之地。张倩女和她的同事们在这里过着一种很典型的现代生活。这里讲求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回报,一切按能力行事。好像所有的一切都符合逻辑,完全具有合理性。然而,不管是在张倩女还是她的同事身上,异化都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实。不错,他们都有着过得去的甚至是令人羡慕的职位、薪水和生活,但他们也因为过于繁重的工作而早衰,在重复劳动中对工作对生活感到厌倦。他们生活富足,却很难感受到自由。在这里,一切的事物似乎都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张倩女的心理感受或许具有典型意义:“她刚站起来,就察觉到一股压迫的力量形成合围之势,渐渐逼近她。十面埋伏。她瑟缩着重新坐下去。毫无疑问,她的敌人更加阴沉强大,那是一个裹挟着整整一代人的庞大而严密的系统,像一个深深的坑洞,让她怎么爬都爬不出来。”这个“庞大而严密的系统”,或许就是海德格尔在其后期著作中一再提到的“座架”。它是现代技术的本质,它席卷一切,操纵一切,把所有人所有事物都纳入可计算、可控制、可利用的范围。在这里面,好像一切都是可以把握的,然而一切又都像是在一种脱序的状态中,个体既无法看清自身,也无法看清自己所置身其中的世界。
除了努力对现代性予以反思,在《净尘山》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形象产生了,那就是张倩女式的城市中产阶级。她有着过得去的职位和生活,却依然不快乐,甚至很无助很绝望。或许是考虑到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数量日益庞大的新阶层,他们的故事如此繁多,所遭遇的问题如此复杂,不是一两个故事便能讲完的,因此,在最近两年的写作中,蔡东总是在持续地书写这一主题。《无岸》中的柳萍就是这一阶层中的成员。她是深圳一所学校的讲师,家里的经济条件还算不错,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女儿童小童那张来自美国普渡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还有随之而来的昂贵学费,瞬间便把柳萍投到了失败者的行列。为了解决女儿的学费问题,她不得不考虑卖房。想着争取单位的周转房,尚未评上高级职称的心病也跟着浮现。对于刘萍这样的中产阶层而言,他们的生活不乏优雅和闲适,看起来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生活状态。然而,这种生活又是易碎的,非常脆弱。仿佛只需一点点外力,他们那精致的生活世界便会崩塌,化为一座绚烂的废墟。小说后半部分还写道,柳萍为了更好地应对眼前的问题,和丈夫开始定期进行“受辱训练”。这个讽刺性的细节,让柳萍的困境昭然若揭,令人过目难忘。
《福地》则是关注城市中产阶层如何落叶归根的问题。小说里写道,傅源的老乡吕端在临终前曾有一个心愿,希望去世后能埋在乡下的老坟里,理由是:“活着,老坟地让我知道我从哪里来,走了,老坟地让我知道我往哪里去。”然而最终,吕端还是带着遗憾“住”进了深圳西北角那毫无特色的公墓。虽然吕端家里不缺钱,为吕端“买的那块地平整阔大,似乎死人活人都差可告慰了”,但是傅源依然觉得吕瑞所遭遇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一个精神性的问题。这也是傅源必然得面对的。他于是开始有意识地重新和那个名叫傅屯——它是留州的一部分——的乡土世界恢复联系,以便在将来为终有一死的自己找到一个更有人情味的“福地”。小说里写道,当傅源挡在祖坟面前时,“他变得开阔,浩大,有来历”。他的生命在这一刻有了依托。然而,小说里又写道,这乡土世界里的一切,也正在发生微妙的改变。懂得传统礼仪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少,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机会以一种庄严的方式回归故土的人也越来越少。这也意味着,困境本身依然处于悬临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三、写作技艺、叙事伦理及其它
除了人物形象和主题上的特点,蔡东的小说还有不少值得注意之处。她的作品有一种“务实”的气质,基本不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恒常的写作主题。尤其是人物的生计,一直为她所念兹在兹。这种从生活的基础地基出发,步步为营的写法是值得赞许的,如王安忆所言,如果小说是在“一个过于干净的环境进行,干净到孤立”,那么小说不会产生真正的说服力。“如果你不能把你的生计问题合理地向我解释清楚,你的所有的精神的追求,无论是落后的也好,现代的也好,都不能说服我,我无法相信你告诉我的。”③于写实之外,蔡东的小说,又有空灵的、虚的一面。在对现实予以正面强攻的同时,她注意到,每个俗世中的个体,都有他们的梦想和秘密,有他们的精神与灵魂。虽然她笔下的许多人物,都被闷在时代里,但是他们也大都在努力地寻找精神出口,试图突围。这种不断寻找的努力,使得她的小说在立足俗世的同时,也有相对超越的一面。
读蔡东的小说,还时常能感觉到,她有一种建构个人文学世界的抱负。蔡东对人的境况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把深圳当作一个角色来经营。深圳之于她的写作意义,不是背景,而和人一样具有同等地位的角色。就像她笔下的人生有着复杂的构成一样,蔡东笔下的深圳,也不乏复杂、多样。她深谙城市的精神,倾向于把城市看作是一个多样不同的实体。这就意味着,对于城市,我们“不是在好对坏的意义上来理解它,而是在好和坏的意义上来理解它。城市会分离人们,也会凝聚人们,会产生压力,也会创造机会……城市对有些人是天堂,对有些人却是地狱;有时更好些,有时糟糕些;对某些目标有益,对另一些却不十分有利。两种极端——以及某些灰色地带——比肩而立。”④
蔡东对深圳的书写,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繁复的过程。《毕业生》《天堂口》是她较早涉足“深圳叙事”的作品。那个时期的蔡东对深圳的理解还多少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比如在《毕业生》里面,她借用了木棉这一意象来隐喻深圳的气质。深圳是一个如此现代的城市,充满了时间的紧迫感,新旧更替的速度,正与木棉的花期一样,是快节奏的。深圳正如木棉,带着“俗套的繁华,还有几丝惊悚。”这一观察,不可谓不准确,却还没有把认识对象更多地转变为审美形象。在《天堂口》中,蔡东对深圳的书写,则多了一重知性的气质,深圳被看作是“天堂的入口”。较之木棉,“天堂口”这一意象的选取和确立,要略胜一筹。而在刚刚完成不久的《净尘山》里面,蔡东所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事实而存在的深圳,还包括想象的深圳。她试图形成一种个人的想象深圳、书写深圳的方法,通过文学叙事的形式来赋予深圳以魅力。现实中的深圳,其实是一座快速成型的政策型城市,不过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建成的,是一座绝对现代的移民城市。比之于北京、南京这样的城市,它的历史线条如此简单,谈不上有多深厚的文化积累。在《净尘山》中,蔡东却试图通过写个人的身世和记忆,移花接木地让这座城市变得有历史感,有厚重感。借此,现实和想象,认识和审美,再现和创造,在小说中有了更高意义上的融合。这是语言的幻术,也是文学的魔力。记得朱光潜曾把诗视为“人生世相的返照”,主张:“诗对于人生世相必有取舍,有剪裁,有取舍有剪裁就必有创造,必有创造者的性格和情趣的浸润渗透。诗必有所本,本于自然;亦必有所创,创为艺术。自然和艺术媾和,结果乃是实际的人生世相之上,另建一个宇宙,正犹如织丝缕为锦绣,凿顽石为雕刻,非全是空中楼阁,亦非全是依样画葫芦。诗与实际的人生世相之关系,妙处惟在不即不离。惟其‘不离,所以有真实感;惟其‘不即,所以新鲜有趣。”⑤蔡东对深圳的书写,似乎也越来越追求这种“不即不离”的效果。尽管面对的是同质化的深圳经验,但是她正在尝试写出不一样的深圳。从《净尘山》《无岸》等作品来看,我觉得她的尝试是可行的,相信随着写作实践的扩展,她笔下的深圳定会有更丰富的面相。
蔡东小说的叙事伦理和叙事美学也值得注意。在语言的经营上,她似乎对张爱玲、白先勇等作家有所借鉴,讲求“新旧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却又不似张爱玲那般以冷眼看热闹人生。对于人生世相,蔡东态度清醒而不清冷。她和传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依然重视文学抱慰灵魂的功能。她好像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视点和视距,以便看清这时代的全部事实,尤其是要发现社会和人生中那些否定性的力量,那些隐藏在生活和人性深处的恶,但是,她又不把这种对恶和否定性力量的揭橥,视为对个人才智的证明。她试图不偏不倚地看待我们的时代,对所有人都能有持平之论。另外,蔡东小说中的人物,通常是没有出路的。或许是因为意识到问题总是处于待解的状态,在人物遭遇困境时,蔡东多少有些心慈手软,在面对那些“阴沉强大的敌人”时,不忘给他们增加一个精神的或灵魂的伴侣,或是某种精神的寄托,以免让他们过于孤单过于绝望,一路沉到底。她还将小说中一个很重要的叙事空间命名为“留州”,似乎是在努力地留住什么,让笔下的人物在受伤时有一个退守之地。这就使得,她笔下的人世既充满困苦,又是可堪珍重的。因此也可以说,在面对社会世界的时候,蔡东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然而,在面对人的时候,她终归是一个有悲悯情怀的人文主义者。这就不难明白,在她的笔下,为什么从来没有所谓的恶人,充其量只是有缺点的坏人;在她的笔下,人世总是冷热交织,绝望与希望同在,充满困苦,却可堪珍重。蔡东不是那种以极致取胜的作家,而是试图在所有层面谋求一种平衡。由于这种辩证过于复杂,难度过大,有时候,她笔下某些情节的经营也会稍显刻意,甚至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逻辑也未能充分展开,比如《木兰辞》里的李燕。蔡东在面对这个人物时,就有些摇摆不定。她既想把李燕塑造成一个在学术体制中如鱼得水的强势知识分子,又希望她身上具有传统的伦理之美:顾家,守孝道,能容忍能牺牲。这一“既”与“又”,在小说中还是显得有些分裂。诸如此类的问题,是蔡东在写作中需要尽力予以克服的。但这里所谓的克服,不是对蔡东的叙事伦理立场的根本否定。相反,如果我们将她的写作放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演变历史中来考量,就会发现,她的这种努力是非常值得珍视的。从1949年建国以来一直到新时期以前,中国当代小说多是为一种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所笼罩,集体的声音遮蔽了个人的声音,激进掩盖了常态。进入新时期以后,以自由伦理为核心的个体叙事则开始逐渐兴起,矛头直指以往的国族叙事,以个人的“小我”来否定外在的“大我”。这种写作策略,使得中国当代小说在时间上形成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式的递进关系,然而,后起的作家在解构以往的叙事伦理,成功地发动“文学革命”的同时,却未能形成一种整全的小说观和健全的精神视野。很多人并未能清醒地意识到,过于强烈的反叛意识,在瓦解以往的叙事法则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也有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神衰败,或始终带着不可克服的局限。因此,在大多数的作家都追求剑走偏锋、以“片面的深刻”为旨归时,我想蔡东不妨继续强调“三观”的正确,坚持这种大方大正的写法。
注释:
①蔡东:《下一站,城市文学》,《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17日。
②耿占春:《过时的人文学科?》,《叙事与抒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③王安忆:《小说的当下处境》,《文学报》2005年9月15日。
④[美]克鲁帕特著,陆伟芳译:《城市人:环境及其影响》,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页。
⑤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7页。
(作者单位: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
责任编辑 杨晓澜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