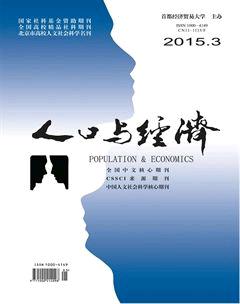为什么流向大城市?
田相辉 徐小靓



摘 要: (中)摘要 城市集聚经济显著影响劳动力工资水平。文章综合利用城市宏观数据和劳动力微观个体数据,通过控制微观个体效应和运用工具变量法等手段,实现了中国城市集聚经济的有效估计。实证结果发现,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显著的集聚经济效应,就业密度更高的城市有能力支付给劳动力更高的工资,从而揭示了生产要素纷纷流向大城市和较发达地区的主要原因。因此,要科学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足够重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显著集聚经济效应,深化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开放程度,逐步消除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
关键词: (中)关键词 集聚经济;就业密度;工资方程;内生性
中图分类号: (中)中图分类号 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3-0023-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3.003
Abstract: (英)摘要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significantly affect labor wage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uses city macro data and individual data of labor to effectively estimate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China through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noticeabl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ffec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in China.The wages of the cities with greater employment density are higher.These results reveal the main reason that the labor force flows into big cities and more advanced regions.Thus, in order to promote urbanization scientifically in China, we should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significant agglomeration economy effects during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deepen the openness of developed regions and big cities gradually eliminate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Keywords: (英)关键词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mployment density; wage equation; endogeneity
一、引言
工资水平较高是大量劳动力流向大城市就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克拉克(Clark)等认为劳动力被吸引到大城市是由于城市集聚经济提高了劳动力的收益[1]。由于城市集聚经济的不可观测性,一般采用比较不同地区的要素价格的方法来识别城市集聚经济,如不同城市规模的劳动力工资水平[2-5]。西科恩(Ciccone)和霍尔(Hall)认为经济要素密集可以提高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企业分享技术外溢和专业化生产,并基于美国数据分析发现劳动生产率对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为0.06[6]。格莱泽(Glaeser)等指出城市就业密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有助于知识外溢,从而使劳动力更容易彼此学习,所以大城市容易吸引更多有技术的劳动力[7]。
近年来,随着微观数据的完善,为了实现集聚经济的稳健估计和集聚经济微观机制的有效探索,利用微观数据从而控制微观个体的异质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具体的实证分析过程中,通过控制微观个体的自我选择效应[8-11],可以有效避免“劳动力质量内生性”[12]。鉴于此,本文将综合利用中国城市宏观数据和微观劳动力个体数据,通过控制微观个体异质性和工具变量法来解决集聚经济识别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这是对单纯用城市宏观数据的既有文献的有益补充。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劳动力个体的工资水平与就业密度显著正相关,集聚经济让进入该区域的劳动力变得更有竞争力。这表明中国劳动力在就业密度更高的城市会获得更高的能力,或者说是就业密度更高的城市有能力支付给劳动力更高的工资,从而揭示了生产要素纷纷流向大城市和较发达地区的主要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实证文献所识别与估计的集聚经济大多属于净效应本文主要是处理集聚经济的有效识别问题,估计就业密度作用于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净效应。就业密度通过分享机制、匹配机制和学习机制作用于经济发展,研究和区分这些作用机制不属于本文所探讨的主题范畴。。而在理论上,经济集聚程度和城市规模是“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两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作为城市扩张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可谓一体两面,相伴而生。但在现实城市发展过程中,相比于城市扩张所带来的各种负外部性,城市规模扩大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正外部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定[13-15],如因担心“城市病”而通过户籍制度等政策限制大城市规模。本文的实证结果从城市经济学视角回应了有关“中国经济是否已经集聚过度”和“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优先发展中小城镇”等有关争论。
二、 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框架
为了实现对城市集聚经济的有效估计,必须有效处理有关内生性问题。除了引言中所提到的“劳动力质量内生性”,“劳动力数量内生性”是集聚经济有效识别的另外一个难题[17]。这主要表现为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就业密度和工资水平同时决定,城市集聚经济可能是高工资水平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对此,西科恩等最早使用历史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6]。基于中国微观劳动力数据(CHIPS 2007),库姆斯等采用了1990年各个城市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所表示的产业结构变量、医生人数占比和城市土地面积等工具变量,来识别城市集聚经济对于劳动力个体生产率的影响[18]。就国内相关文献来看,范剑勇将土地面积作为就业密度的工具变量,运用城市截面数据考察了城市集聚经济对于地区生产率的集聚效应,发现国内城市集聚效应要高于同期欧美发达国家[19]。根据研究问题和数据的特征,本文主要通过控制微观个体异质性和工具变量法来消除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误,以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有两个互补的数据来源:一个是劳动力个体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2008年所收集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Survey,CHIPS)。本文使用其中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库。调查样本有9个省份15个城市,包括上海,广东的广州、深圳和东莞(东部地区),江苏的南京和无锡(东部地区),浙江的杭州和宁波(东部地区),湖北的武汉(中部地区),安徽的合肥和蚌埠(中部地区),河南的郑州和洛阳(中部地区),重庆(西部地区),四川的成都(西部地区)。另一个是城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除了模型重点关注的核心变量以外,本文根据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框架的具体情况来选择尽可能多的控制变量。所有变量的界定如下所示。
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CHIPS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库中的工资(Wage)变量,除此之外,小时工资(Wageh)和收入(Income,除了工资外,还包括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这些也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四、实证分析
1.OLS回归分析
在第二部分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依次引入个体效应变量、企业行业效应变量和城市效应变量来控制模型的内生性偏误,如表3(以城市市辖区为地理单元)所示:模型1为控制劳动力个体效应的回归结果,模型2为控制企业行业效应的回归结果,模型3为控制微观个体效应和企业行业效应的回归结果,模型4为控制城市效应的回归结果,模型5为同时控制三个层面效应的回归结果。由表3可见,本文关注的集聚经济核心变量——就业密度与劳动力工资水平呈正相关,而且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统计显著,但弹性系数略有差别,在控制微观个体效应的情况下,弹性系数均在0.12以上,这要高于欧美等国家的就业密度弹性系数,这与库姆斯等[18]和范剑勇[19]发现的结论一致。库姆斯等总结了2000年来集聚经济的估计情况,指出在采用标准估计方法的情况下,就业密度对工资水平的弹性系数一般在0.02-0.05之间[17];霍伊尔曼(Heuermann)等也指出,在早期文献中城市工资溢价大约为0.05-0.10,但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在内的诸多控制变量后,工资溢价大多为0.03左右[21]。
进一步比较这6个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如果没有控制微观个体效应,将会高估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通过观察微观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可以找到其中的原因:本文重点关注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变量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以及职业岗位均与工资水平正相关,而且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统计显著。这与库姆斯等的结论一致,其基于法国数据的研究发现,当模型引入劳动力个体固定效应时,就业密度的回归系数约降低一半[12]。企业规模控制变量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与劳动力工资水平正相关,这是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的反映。在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中,城市市辖区土地面积在1%的显著水平上与劳动力工资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在控制城市就业密度的前提下,土地面积较大城市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要高于土地面积较小城市的劳动力工资水平。
反映地区产业结构效应的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与劳动力工资水平正相关,而且专业化经济效应明显大于多样化经济效应,这表明生产要素空间集聚效应在区域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城市多样化经济和城市专业化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相互排斥,可能同时发生作用,只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而已。城市地理特征中,城市区位显著影响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来自东部地区城市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而城市等级的影响不显著。反映所有制改革的制度变量在1%的显著水平上与劳动力工资水平正相关,这表明中国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为特征的所有制变革促进了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反映对外开放的制度变量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2.工具变量法
虽然控制微观个体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集聚经济识别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但就业密度和工资水平之间的反向因果以及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仍然需要有效处理。下面将采用传统的工具变量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工具变量的选择需要从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个方面去考虑。综合既有文献,比简单滞后内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的做法更有效的工具变量主要有两类: 一是采用地理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如行政区的土地面积[6,18-19];二是采用滞后期的政策变量作为工具变量[18, 22]。据此,本文分别选取1990年度的人口、就业密度和土地面积等变量作为集聚经济变量就业密度的工具变量。此外,库姆斯等认为初始时期的部门结构变量是集聚经济工具变量很好的选择[17]。所以,本文选取了1990年各城市的产业结构变量,并用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来表示。之所以选择1990年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主要是借鉴相关文献总结的工具变量选取经验和具体做法[18, 22]。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中国改革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停滞期,虽然农村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但城市改革却刚刚开始,而且僵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依然固化着整个经济结构,所以本文假定其与当前的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无关,但是与集聚经济变量就业密度相关。在具体的计量分析过程中,本文首先对所采用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23]。
表4报告了城市经济学模型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模型6和模型7分别以劳动力工资和收入为因变量,均假定除了就业密度为内生变量外,其余变量均为严格外生变量,并使用1990年的人口、土地面积、就业密度和产业结构作为工具变量。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工具变量均通过了有效性检验,而且内生性检验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零假设,所以只有工具变量法(IV)估计才能取得一致性结果。根据表4可知,IV估计结果中就业密度与劳动力个体的工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城市就业密度每提高1%,劳动力工资水平平均提高0.12个百分点,劳动力收入水平平均提高0.09个百分点,但回归系数要小于OLS回归结果。这表明,在存在内生性的情况下,OLS估计高估了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上述结论也可以从城市市辖区的土地面积与城市劳动力个体工资水平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得到佐证:在控制市场潜能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面积较大城市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要高于土地面积较小城市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城市层面的集聚经济变量(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均与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进一步表明城市集聚经济提高了劳动力的收益。表4中的模型7是以城镇劳动力收入作为因变量进行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回归系数要小于前者。
3.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利用2002年和2007年CHIPS劳动力个体数据进行分析。2002年CHIPS劳动力个体数据调查样本涵盖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甘肃12 个省、市、自治区,共涉及8个副省级城市和50个地级市。2007年CHIPS劳动力个体数据样本的来源城市与2008年CHIPS个体数据一样,也来自文中第三部分介绍的15个城市。如表5所示,模型8和模型10是采用OLS方法进行的回归分析;模型9和模型11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其中,集聚经济变量就业密度的工具变量分别选取1990年度的人口、就业密度和产业结构变量。在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基础上,两个年度的模型均没有通过内生性检验,所以只有IV估计才能取得一致性结果。两个年度的IV估计结果显示,就业密度作用于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净效应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统计显著。
对比OLS和IV两种方法可以发现,在存在内生性的情况下,OLS估计高估了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微观个体效应变量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OLS估计基本保持一致。对比两个年度的回归结果,相对于2002年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2007年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要大一些,这表明城市集聚经济效应随时间而变化,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虑时间效应以更有效识别集聚经济。
五、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综合利用城市宏观数据和劳动力微观个体数据,通过控制微观个体效应和运用工具变量法等手段,实现了中国城市集聚经济的有效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个体的工资水平与就业密度显著正相关,集聚经济让进入该区域的劳动力变得更有竞争力;是否控制微观个体效应对回归结果的大小影响显著,对于集聚经济的相关研究存在高估的情况。基于工资溢价的集聚经济识别结果证实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显著的集聚经济效应,劳动力在就业密度更高的城市会获得更高的能力,或者说就业密度更高的城市有能力支付给劳动力更高的工资;在控制就业密度的条件下,土地面积较大城市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要高于土地面积较小城市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这也是生产要素依然纷纷流向大城市和较发达地区的主要原因——即便这些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成本比较高。如果政府忽视这一事实,不注重深化发达地区的开放程度,逐步消除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和降低交易成本,而是盲目出台有关政策吸引资金和企业落户到集聚经济较弱的地区,那么政策效果势必事倍功半。
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的城镇化还将高速发展,将有2亿-3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如何发展城市经济,以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来充分吸收来自农村的大量移民将是决定这一进程的核心问题。从1993-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密度与快速城镇化的速度是不同步的,甚至部分城市的人口密度实际上是在降低的。如果以就业人数来度量的话,情况更不乐观,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任重而道远。
基于中国城乡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充分发挥中国城市集聚经济需要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通过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相互作用的市场均衡机制来实现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和空间协同。在快速城市化和城镇空间扩张的总体背景下,只有在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前提下,采用相对紧凑的空间发展模式才有可能更好地规避城市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这也是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足够重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显著集聚经济效应,遵循城市发展的自然法则和市场规律。中国农业劳动力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转移面临以户籍制度为根源的诸多制度障碍,城市集聚经济效应的充分发挥受到限制,进而影响到全国城市体系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所以,要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特别是跨区域流动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24]。城市和发达地区应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分享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要科学评价和积极应对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负外部性。不能以和城市集聚效应共生的“城市病”为理由,人为限制城市规模,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城市病”导致城市衰退[13]。至于如何有效处理上述两方面的“矛盾”,最根本的还是要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管理水平,科学规划土地资源,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参考文献:
[1]CLARK G L, GERTLER M S, FELDMAN M P.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477-486.
[2] GLAESER E L, MARE D C.Cities and skill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1, 19(2): 316-342.
[3] MION G, NATICCHONI P.Urbanization externalities, market potential and spatial sorting of skills and firms[R].CEPR Discussion Paper, No.5172, 2005.
[4] COMBES P P, DURANTON G, GOBILLON L.Spatial wage disparities: sorting matter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8, 63(2) : 723-742.
[5] PUGA D.The magnitude and caus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0, 50(1) : 203-219.
[6] CICCONE A, HALL H R.Productivity and the density of economic activ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 86(1) : 54-70.
[7] GLAESER E L, RESSEGER M G.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cities and skills[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0, 50(1): 221-244.
[8] OTTAVIANO G.“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11(2) :231-240
[9] VENABLES A J.Productivity in cities: selfselection and sorting[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1, 11(2) : 231-240.
[10]COMBES P P, DURANTON G, GOBILLON L, PUGA D,ROUX S.The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of large cities: distinguishing agglomeration from firm selection[J].Econometrica, 2012, 80(6) : 2543-2594.
[11] 梁琦,李晓萍,简泽.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与地区生产率差距研究[J].统计研究, 2013(6):51-57.
[12] COBES P P, DURANTON G, GOBILLON L, ROUX S.Estimating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with history, geology, and worker effects[M]//Glaeser E L. Agglomeration Econom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15-65.
[13] 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10(10) : 20-32.
[14] 陆铭,高虹,佐藤宏.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J].中国社会科学, 2012(10) : 47-66.
[15] 丁成日,谭善勇.中国城镇化发展特点、问题和政策误区[J].城市发展研究, 2013(10) : 28-34.
[16] COMBES P P, MAYER T, THISSE J F.Economic geography: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s and nations[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283-291.
[17] COMBES P P, DURANTON G, GOBILLON L.The identification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 2011, 11(2) : 253-266.
[18] COMBES P P, DE MURGER S, LI Shi.Urbanisation and migration externalities in China[R]. GATE Working Paper ,WP1303,2013.
[19] 范剑勇.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J].经济研究, 2006,(11) : 72-81.
[20] DURANTON G, PUGA D.Diversity and specialisation in cities: why, where and when does it matter?[J].Urban Studies, 2000, 37(3): 72-81.
[21] HEUERMANN D, HALFDANARSON B, SUEDEKUM J.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and the urban wage premium: two literature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J].Urban Studies,2010, 47(4) : 749-767.
[22] AU C C, HENDERSON J V.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6, 73(3) : 549-576.
[23] 王美今,林建浩,胡毅.Ⅳ估计框架下模型设定检验问题的讨论[J].统计研究,2012(2) : 82-89.
[24] 蔡昉.如何进一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2(1) : 8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