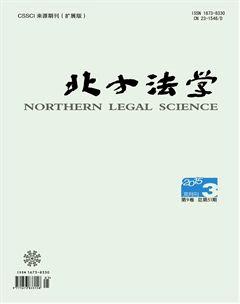公众参与理念在美国土地规划票决中的实践及启示
吴亮
摘要:美国的投票式分区管制将票决制度运用于土地规划,是一种最强程度的公众参与。实践表明,土地规划领域有适用票决制度的必要,票决制度体现的公众参与特征包括决策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双向沟通关系,决策结果对公众参与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在信息公开制度健全、议题限制、平等保护审查等条件下,居民投票不会沦为“愚众政治”,与专业机构判断的对立也会缓解,而且也不会“压迫少数人的意见”。我国应在涉及健康、生命安全的公共项目选址决策中引入票决制度,并同时完善信息公开配套机制,以及加强对居民投票决策不违反公益要求的程序管控。
关键词:投票式分区管制票决制度公众参与土地规划
中图分类号:D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5)03-0064-08
土地规划决策如何通过公众参与来安置与开发行为相关的民意诉求,已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理论热点。土地规划领域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已经行之有年,如城乡规划草案应当“通过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村庄规划在报送审批前还要“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但是,每逢重大的开发行为仍屡屡爆发严重的抗争冲突,甚至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从启东事件、什邡事件等源于环境风险的群体性事件来看,公众参与程序的缺陷与低效是引发决策失误和民众抗争的主要原因。因此,居民怎样参与才算妥当,在诸多参与方式中如何选择最令各方满意、最有效果的一种,还存在着很大的探讨空间。
鉴于土地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所遇到的难点,探讨在个案中如何选择最佳方式来落实公众参与理念,就成为务实的解决思路。在这方面,美国土地规划领域的票决制度无疑走得最远。在这种制度中,具有利害关系的地方居民以票决方式参与涉及到人居环境、生态资源、土地使用和公共设施项目的土地分区管制,与政府分享规划的主导权。①在我国强调公众有效参与土地规划的语境下,探究美国如何通过扩张公众参与机制来增强土地规划决策的“民意敏感度”,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实现均衡,可以为我国提供方法论上的宝贵经验。
一、土地规划中的票决制度及其法律结构
(一)票决制度适用于土地规划的必要性
票决制度一直被视为是最强程度的公众参与。1969年,美国学者艾恩斯坦在“公众参与阶梯”理论中依据公民影响决策的程度差异,将公民参与由强到弱分为实质参与、象征性参与和无参与三种。其中,票决制度属于实质参与,是公众参与程度最高、对决策最有影响力的参与类型。②在这种方式中,行政机关做出的决策最贴近公众的实际需求,也最能获得其接受和信任。将票决制度引入土地规划领域大约开始于1960年代,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政府主导的规划出现过分偏重经济发展利益的偏差。土地规划的重心是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对立关系,避免过度的开发行为损害到居于弱势地位的环境价值。这里的环境泛指人的自然生活基础,不仅包括生态资源与自然景观,而且包括文化古迹、社会经济、邻里结构、街区文化等人文生态环境。③由于经济开发带来的利益立即可见,而环境保护带来的利益是无形或隐形的,因此不少地方政府的规划决策出现过分追求商业开发和牺牲环境价值的偏差。这些开发方案在带来商业利益、促进地方发展的同时,也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公共交通堵塞、地方财政赤字、地方文化破坏、生活成本和房价飞涨等问题。同时,随着官员失职、官商勾结投机土地交易的丑闻不断曝光,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规划决策愈发失望和不信任。
第二,政府的规划难以反映真实的民意,无法满足公众维护良好环境的公益需求。由于体制的僵化和规划权的过分集中,地方居民的利益诉求无法被规划者及时知晓,导致城市开发的布局难以反映真实的民意需求,如有秩序的城市发展、保存原有的邻里结构和街道文化、平价住宅的短缺。④当政府决策与民意相左时,居民的自治意识就开始高涨,希望亲自参与规划的决策。例如变电站、机场等邻避设施虽对城市整体环境具有正面效应,却对特殊地段产生地价贬值、生活品质等负面影响。⑤由于有些邻避设施的成本、收益分配有利于政府、开发商、金融机构等少数群体,很多邻近居民则没有获得公正的待遇。在此情况下,居民就会发起抗争要求参与规划。
第三,民众与居住环境之间形成“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比政府更能了解规划中的关键问题,并具有解决环境问题的决心。如垃圾焚烧场的选址、旧区改造的设计等规划事项与民众的生活品质、身体健康紧密相关,因此更容易获得民众的重视与理解。而且,居民往往比政府具有更充分、真实的切身体会与一手信息,对规划决策的判断也更为合理全面。
第四,专业机构在政策争论的过程中无法得到充分信息,难以做出理性的风险决策。环境决策的最大特征在于其不确定的知识基础。也就是说,受限于人类认识能力的界限,对于污染、辐射设施对健康或环境造成的冲击,环境危害的机率和损害规模,应采取的预防和处置措施,即便是专家也无法提供准确的答案,这就使得环境问题的决策充满“利益衡量”的意味:⑥要么冒着未来可能受损害的风险享受当下的科技;要么选择放弃所有未来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科技。不同的利益团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考量,对于有些开发商和地方官员而言,其宁愿以开发造成的危害来换取就业机会和当地经济发展,但是普通民众也许宁可牺牲某些物质享受,也不肯接受环境破坏的恶果。在对环境问题做出利益衡量时,公众的投票有助于专业机构预先评估民众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风险接受程度,判断如何在民众容许的范围内进行理性的风险决策。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地方纷纷在加强公众参与的口号下,让居民通过投票亲身参与涉及环境问题的规划决策。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等州率先于1960年代末进行所谓“投票式分区管制”的尝试。⑦据统计,仅在2010年全美就有38个州实施了553项投票式分区管制,投票人数高达一亿人次以上。而且,民众提出的议案获得表决通过的成功率也在大幅攀升,从1988年的46%上升到2007年的70%以上。
在实际操作中,投票式分区管制主要包括如下两种:其一,邻避设施对抗型。当地方居民由于变电站、机场、高铁等有害健康、生态的邻避设施而可能遭受损害时,便会诉诸投票来抵制邻避设施进入该地区,制止对地方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其二,公共建设选择型。分区管制如果增加土地的开发密度,或者将其从农田转为商业区域,就会导致局部地区与周边社区的不相容,引发交通拥挤、生活品质降低、土地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等。不满的邻近居民便会诉诸投票来限制和延缓城市的盲目扩张,维护城市开发的公平性,如对住宅开发设限、扩充公共基础设施、否决对地块的过度开发(容积率、建筑率过高)、指定某块区域为自然景观或防洪保护区、为中低收入户提供住房补贴、要求某项土地使用须经居民的同意、要求房地产业的发展不得破坏其他工商实业的均衡发展等。
司法机关也相继承认了投票式分区管制的合法性。在1976年“东湖城诉森林企业协会”一案中,⑧最高法院第一次允许居民投票对土地分区管制进行推翻和修正。首席大法官伯格在判决中指出:公民利用投票来对公共政策问题做出决策属于宪法赋予的“传统权利”,投票式分区管制是“跨越民意代表,通过直接立法来满足公共利益”。
(二)票决制度体现的公众参与特征
第一,决策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双向沟通而非单向传递。如果将整个公众参与的形态视为一道光谱,那么光谱的一端是传统的被动式参与,即当事人享有被行政机关倾听的消极权利,可向决策者提出自己知悉的证据和争议点,包括听证、陈述事实和表达意见。光谱的另一端则是以票决制度为代表的主动式参与,即当事人享有参加决策过程的积极权利,通过主动投票以及参加投票前的审议程序来影响审议过程和决策结果。⑨票决制度不再是决策者向参与者的单纯信息收集,而是双向式沟通与开放式协商。规划决策不再为少数人垄断,而是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商程序达成共识,并作出最符合民意和公益的结果。
第二,决策结果对民众参与具有高度的依赖性。换言之,公众参与对决策的正当性起到了补强作用,成为在法律效果上拘束决策的有效装置。依据立法通说和实务见解,行政机关应对投票结果负有如下两种程度的尊重义务:
一是复决式票决对行政机关产生法律拘束力。如威斯康辛州规定,一旦有55%以上的人在复决中投票反对,分区管制法案就不能生效,而且政府在一年内不得出台相同内容的法案。⑩这里的复决(Popular Referendum),即民众不能主动提出立法议案,只是针对政府已经提出的分区管制法案进行投票决定。B11社会公众往往是通过复决来抵制地方政府的新开发项目。地方议会一旦收到社会公众联名提交的复决请愿书,就会考虑撤回、修订原先的规划法案,尽量避免投票的发生。另外,复决议案即便未获通过,也会促使地方社会和政府反思和完善规划。
二是咨询型投票对行政机关产生事实拘束力。这里的“咨询型投票(advisory Referendum)”,是指投票结果只是一种决策参考依据,对行政机关不具有法律拘束力。B12咨询型投票的结果虽不能直接拘束决策者,但其事实上的拘束力却不容忽视。政府不敢忽视和违背投票所反映出的民意主张,如果最终的规划决策违反咨询型投票的结果,那么官员就要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甚至是被追责、罢免的风险。因此,地方政府一旦收到民众提交的复决请愿书,就会立即提出替代原法令的修正案,并举行咨询型投票来试探社会反响。
由此可见,对于依据严谨程序并耗费时间与人力完成的投票结果,行政机关无法忽视其蕴含的多数居民意向。除非基于特殊理由,政府在进行规划决策时必须尊重乃至遵守居民的投票结果。投票式分区管制科予行政机关的尊重义务,是作为被动式参与方式的民意调查所欠缺的。民意调查不能对行政机关产生拘束力,公众的赞成或者反对能否得到重视完全操控在官员个人手中。对于行政机关与官员而言,由于规划一旦违反投票结果就会导致严重的违法风险与政治影响,行政机关和官员不敢忽视民意诉求和遗漏任何利害关系人。同时对于民众而言,正是凭借着投票对地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居民、弱势群体原本遭受忽视的利益诉求才得以伸张。因此,居民在投票式分区管制中是抱着“实质参与行政过程”的认真态度来参加投票的,这也是民意调查所不具备的。
二、对票决制度的反对意见及措施回应
有人对土地规划中的票决制度提出很多疑虑,甚至反对其施行。如何释解这些反对意见,对于理解票决实施的必要性而言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笔者对此试作初步归纳。
(一) 居民投票是不是“愚众政治”
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普通民众缺乏专业的土地利用规划知识,在规划决策时容易出于一时的情绪冲动,或者受到别有用心的少数人利用和煽动,因此,居民投票纯属“愚笨群众”作出的非理性判断。B13这种愚众政治的误解导致土地规划领域的票决制度一度受到阻碍。其实,居民尽管没有专业知识背景,却具有通过投票参与土地规划的正当性理由:其一,居民之所以要参加决策,无非是为了更适宜人居、更安全的环境,对于这种单纯、实际的心态,法律应当予以尊重,而不能一概斥之为“愚众政治”;其二,在教育普及、网络发达的当代社会中,居民对信息的取得、吸纳能力今非昔比,因此对环境问题的判断、决定也大多是采取审慎、理性的态度。
若因公众意见存在消极面而一概抵触,就等于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并弃置。其实,居民投票是否会带来非理性决定的危险,其关键并不在于居民本身的素质和能力,而在于有没有向居民提供正确的信息。如果居民缺乏真实和充分的素材,就往往做出片面评价和误解,甚至容易被少数人煽动和利用。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的“深思熟虑理论” ,B14民众作为分散孤立的个体,彼此之间如果对土地使用政策缺乏充分的掌握和深入交流,只能依靠主观直觉产生的“自然意思、表面选择”来做出投票,那么投票结果就会缺乏“深思熟虑”,并容易受到感情、偏见、他人煽动等因素的影响。
为了保证居民投票不至于有滑向“愚众政治”的危险,各州均强调将投票式分区管制与信息公开程序进行联结,强化居民作出决策的信息基础,让居民对某项公共议题具备相当程度的了解和专业知识,避免其由于信息不足而难以作出理性判断。这些程序措施大致如下:
1 在提出票决议案之前的规划初期,政府应通过听证会、审议会等调查程序及时听取公众的反对和异议,并且使其反映在规划方案上。
2 在提案审议与投票阶段,政府的信息公开责任包括:一是散发公报,将投票提案的内容、投票日期和投票方法制成文书发给公众;二是遵守第十四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设置事前告知和听证会等程序,主动将有关行政规划信息提供给居民阅览;三是举办讨论会、座谈会,为赞成派和反对派提供辩论和交流机会,并为居民提供答疑解惑。
3 行政机关应当遵守价值中立原则。详言之,行政机关在履行信息公开职责时,必须基于公正、中立的立场,不偏不倚地提供信息。B15这是因为:第一,完整、准确的信息是保障居民做出理性抉择的前提,而基于错误、偏颇的信息所做的判断则毫无理性可言;第二,由于城市规划应当尊重投票结果中的多数民意,因此在投票之前行政机关不得做出任何“选边站”的举措,否则将会影响规划决策的公正性;第三,投票结果虽然不是行政机关的最终决定,但是却代表着政府将分区管制委托给居民做决定,行政机关希望影响投票结果的任何事前举措都有失公允。
在官民双方对开发的意见相左,居民通过投票反对政府规划法案的场合,如何贯彻价值中立原则就成为一个棘手问题。实务中的普遍做法是尽量避免由行政机关单方承担信息公开的工作。例如俄勒冈州将信息公开的主体由行政机关更换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 。B16具体做法是由投票的申请代表二人、州长指定的二人,以及这四位代表共同推举的一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发表投票公报、举办讨论会和座谈会等事宜。
(二)居民投票与专业机构判断是否对立
尽管教育程度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民众更易获得决策信息,但是如何保证居民在取得信息之后合理地加以权衡与选择,仍然是一个困难问题。居民投票在规划政策的选择上往往带有对抗“专家判断”的民主色彩,由于对一些复杂的土地使用议题缺乏专业经验,容易做出与专业机构判断相悖的决策。与此相对,专业机构通过细致的资料收集、规划方案的评估、管制法案与整体土地使用政策之间的考察,从而做出客观的判断。民众通常无法承担如此精密复杂的工作,往往跳过这些专业分析而依据朴素情感做出判断,如此就可能导致决策的不理性。B17
而且,居民投票有时还会带来主张地方利己主义的复杂问题。由于小范围管制的决策主体缺乏价值中立性,导致少数群体主张不同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少数人利益,影响整体规划的实施。典型例子如“利己效应”,即当规划所欲实现的公益与居民自身的私益相矛盾时,当地居民未必是以社会整体的发展作为优先考量,造成对公共利益的破坏。B18例如规划修建有害健康、环境的邻避设施时,邻近地区的居民大多采取反对的态度,造成公共设施的区位无法选择。因此,将规划问题委由居民投票并不意味着可以就此完全排除专业机构的介入。居民投票并不能取代专家判断,法律必须对居民的票决议题与规范内容进行控制,避免其囿于一己私利做出抉择,或者盲目地受到煽动。这些限制措施大致包括如下:
1 票决议题限于一部分立法事项,不得付诸票决的议题包括如下两种:
(1)行政机关的专属事项。投票式分区管制只能用于立法事项,不容许居民通过投票来影响行政执法活动,削弱或者破坏既有立法政策与目的的执行。加州上诉法院通过“第41号林肯财产基金会诉法律委员会”一案指明,B19综合发展计划、分区管制法令的制定或修正属于立法事项,可适用投票式分区管制。而土地细分、特别许可与条件使用等则属于非立法事项,不适用投票式分区管制。加州最高法院随后在“七千人协会诉艾文市”一案中,B20具体分析了立法事项与非立法事项之间的两项区分标准:一是形式标准,即法规的语言表述使用的是“地方立法机关”还是“执行机关”。二是实质标准,如该事项是政策创造还是政策执行;在影响范围上是否限于少量的街道社区;是否属于纯粹的市政管理事项。
(2)可能削弱地方政府根本职能的部分立法事项,如大部分土地财政、公共税收事项。这些立法事项关系到地方政府的根本职能行使,法律不允许居民取得票决权。如在“纽森诉管委会”一案中,B21加州地方法院判决建造和经营收费道路的授权许可是专属于地方议会的特权,居民的投票创制将完全破坏政府对市政建设的根本职能。不过,法院强调涉及到地方政府根本职能的事项,仅限于“是否批准建造”以及“将道路交由谁来经营”。当政府做出决定后,居民仍可就缴费标准、收费年限、设施维护等后续事项进行投票。又如在“七千人协会诉艾文市”一案中,奥伦县居民为了改善道路拥堵状况,提出了一项要求将本县的发展税全部用于兴修高速公路的创制。加州最高法院判决州法已经授予市议会对发展税使用的专属决策权,该县居民不得干涉。法院认为,运输系统的建设影响到奥伦县以外的其他地区,需要由上级政府统筹考虑公共设施的整体情况、交通路线的布局作出决定。
2 规范内容不得与上位法律相抵触。居民的票决结果必须符合州法(state statutory)才能生效。例如在“邻居行动组织诉卡拉沃斯市”一案中,B22加州上诉法院认为,投票式分区管制需要在土地使用、公共交通、住宅、环境保护、开放空间保留、噪音和安全等七个方面遵循州法的要求。该法院还通过“德波利诉诺克市”一案判决指明:B23居民没有权力设立与州的规划法令相抵触的分区管制条例。该条例若与州法之间存在着“明确、直接的不一致”,就违法无效或者被撤销。
(三)居民投票是否会“压迫少数人的意见”
由于居民投票是自愿的,在某些场合难免会使特定区域的偏狭地方利益成为主导,出现压迫少数人意见、剥夺少数人权益的情形。为了避免形成地方利益团体对规划决策的不当垄断,美国法院更加关注平等原则在投票式分区管制中的贯彻。法律强调享有规划决策权的主体是整体居民而非特定社区,因此在投票程序中,所有受到规划影响的居民权益应当一视同仁。宪法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不容许投票结果偏袒某些集团的利益,或者强迫小范围的土地权益者或者特定团体忍受侵害。
1 对个别土地权益者进行平等保护。如在“弗瑞诉黑沃市”一案中,B24当地居民创制了“一号措施”法令,要求开放空间未经市民一致同意不得改作其他用途。因此,高尔夫球场所有者弗瑞希望将球场改为住宅用地的申请遭到驳回。加州最高法院判决“一号措施”违背平等保护的原则而无效。法院认为,不同类型的开放空间保留措施在公益性质、权利干预程度方面具有很多差异,“一号措施”不应等同视之。就高尔夫球场的保留而言,一方面,该管制所欲实现的公益层次较低,仅仅是为了增加周围住宅、商圈人士的福利;另一方面,该管制未予补偿就剥夺了土地的经济用途,给土地所有者带来过重的负担和限制。因此,“一号措施”没有对利益冲突做出妥善的协调,构成“准征收”。
2 对特殊群体进行平等保护。如在“阿诺公司诉考马萨市”一案中,B25当地居民创制法令要求政府取消单身公寓的开发计划。加州上诉法院判决认为,根据州住宅法的规定,提供充足住宅以满足不同阶层人群的住房需求,是一项全州性的公益。公民的创制法令漠视单身人群的住房短缺问题,产生对特殊群体的差别待遇,并违反了州住宅法。加州上诉法院随后通过“诺斯沃德公司诉莫瑞格市”案进一步阐明,B26如果创制的目的仅在于阻止有争议的房产开发,与公益并无实质性关联,那么就不具有合法性。只有基于保护环境、健康安全等公益目的的投票式分区管制,才具有阻止针对单身人群的住宅开发计划的正当性。法院的思路暗含这样的判断,即投票式分区管制应当将自然环境、社会公众和特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纳入考量,对城市开发的决策一方面需要兼顾对特殊群体的平等保护,另一方面又应当限制在环境、个人健康、社会安全等承载的极限范围内。
3 对受到规划影响的所有民众进行平等保护。如在“豪恩诉凡塔拉市”一案中B27当地居民创制分区管制法令,要求政府在决定能否将废弃的空军基地转为民用机场时,须经机场邻近社区的居民投票一致同意。加州上诉法院认为该创制没有向本市其他居民授予投票权,未能平等地保护所有受到该公共设施影响的全体公众。法院指出,投票表决的主体只有最大范围地涵盖可能受到规划影响的社区,才能符合宪法的平等保护要求。
三、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启示
当前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偏低”现象可以说反映出我国土地规划制度遇到的实践困境。简言之,“有效性偏低”现象就是由于土地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机制不合理,公众参与程度不高且流于形式,导致公众不信任规划,宁愿诉诸激情抗争而非理性参与来表达意见与不满。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双向沟通和适当引入票决制度,也许能够扩张公众参与的制度容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机制的不足。近年来随着行政改革的深入,票决制度也开始在各地的规划实践中显出轮廓。实践中涌现的票决形态大致包括以下两种:
第一种是类似于复决的票决,居民投票的结果对规划结果发挥决定性作用。例如将胡同、城中村或者社区的改造方案、旧区拆迁或者土地补偿分配方案交由居民投票表决;或者根据居民票决结果,决定是否在社区增设电梯、水电设施等公共设施。B28
第二种是类似于咨询性投票的票决,居民投票的结果虽不能直接决定决策,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规划结果。最常见的就是行政部门将前期草拟的公共设施方案、地标建设方案、旧区更新改造或者动拆迁编制方案,交由当地居民乃至全体网民投票表决,并参考票决结果作出政策的选择。B29
这些改革的共同点就是认为居民投票可以集合众人的想法,有利于做出整体的最佳判断。之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改革潮流,是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提出了完善规划决策机制的要求,民众对分享规划决策权、保证决策理性产生了更加迫切的要求。由此可以预期,以居民投票为代表的公众参与机制将会在土地规划领域逐渐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当前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在涉及到健康、生命安全的公共项目选址决策中引入票决制度,使之接受高强度的程度管控。一方面,公共项目的选址具有较大的环境风险,对相当区域和数量的社会公众产生严重的健康或者生活威胁,对地方公众的影响程度较高;但是另一方面,目前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风险沟通效果不尽人意。从2007年厦门PX项目事件、2009年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2010年上海磁悬浮事件等来看,民众对规划的参与程度有限且时间滞后,公众意见不受规划者的重视,难以实质影响规划的决策,而且,有些地方政府怀着“博傻”心态片面掌控信息,故意向民众隐瞒环境风险以及可能给居民带来的潜在影响。B30
由于政府的规划决策忽略了作为规划对象的社会公众本身,引发了社会公众、社区居民的情绪性反弹,当规划的错误无法通过正式的程序机制加以避免或纠正时,就出现了不得不靠公众意见的强烈表达来纠正的事态。行政机关只有遭遇到民众的激烈抗争之后,才对规划的公平性问题予以回应。由于公众参与机制疏漏而导致的规划不合理、不公正是社会公众不满的重要原因,政府需要正视这种冲突产生的必然性,通过票决等双向沟通程序吸纳不同的公众意见,回应日益高涨的民众参与意识。与其让民众通过事后的暴力方式参与规划,不如通过事前的票决制度吸纳各种博弈力量的意见和态度,化解可能出现的社会暴力事件。
不过,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站在规划的专业角度来看,票决制度既然是追求规划的程序正当与结果合理,应当也只能在公民的决定正确、理性的限度内发挥其功能。在此笔者尝试围绕着如下两个条件进行考察:
首先是作为公众参与基础的信息公开机制。环境信息的公开是保证票决制度发挥公众参与、风险沟通功能的基础,但是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为中心的规划公开机制却难以达到对环境信息的完整、准确性要求。理由如下:
一是在信息公开与行政调查时作为环境信息主要提供者的开发单位所应当承担的信息公开义务欠缺。环境信息公开的相关资讯主要来自开发单位,但是《城乡规划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规定的论证会、听证会似乎仅仅是收集民众对开发行为的意见,却没有对与开发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开发单位科以主动公开信息的义务。这就导致开发单位要么通过选择性地释放环境信息,要么故意不主动公开环境信息,以此主导公众参与程序和诱导民众形成错误的意见。
二是公众参与过程中累积的信息资料不属于法定公开的范围。在公众参与规划过程中积累的资料包括听证记录、现场勘察报告、政府的过程性调查报告等:B31这些资料包含了不同意见的讨论与沟通,可以帮助民众迅速掌握规划决策所应考量的重点,但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没有将其纳入法定的公开范围,导致许多地方政府拒绝向公民提供这些资料。
三是规划公示的信息过于专业和简略,难以帮助民众作出准确的判断。由于立法对规划公示的格式和内容要求不合理,因此在实践中公示的内容大多简略,没有重点提示和阐明存在争议和风险的内容。而且,听证会、讨论会上的说明文件动辄就是上百页且具有高度专业性,难以为一般人所理解。
其次是对居民的投票决策不违反公益要求的程序管控。从美国的实践来看,完备的司法审查程序是制约民众滥用票决程序、甄别民众决策是否符合公益的有效机制。在土地规划领域,司法介入票决产生的争议大致包括三种类型:投票议题是否属于法律不允许票决的事项?票决产生的规范内容是否违反平等保护原则或者上位法律,侵害到少数人的权益?居民票决的程序是否合法正当?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属于空白。因为我国在一些小型动拆迁、土地补偿分配的规划编制阶段引入票决制度刚刚起步,居民票决结果不符合公益要求的案例似乎还没有出现,研究还停留在“票决制度是否充分地反映公众参与理念”的抽象层次上。但是从充实和发展公众参与原则的角度来看,认真思考票决的司法审查程序对于加强该制度的可操作性会有很大的贡献。
Abstract:In the US, regulations on ballot box zoning have been used in land planning with the feature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o the strongest extent. In practice, the referendum system is necessary to be applied in land planning for it involves citizen participation which can reach a bilate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decision-makers and participants and such decisions rely much 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Citizens ballot will not descend to “politics of fooling public” guaranteed by conditions of perfect system of information publicity, restriction of arguments and review of equal protection. Moreover, the confrontation against judgment by professional agencies will be alleviated and citizens ballot will neither result in “oppressing the minoritys opinion”. In our country, the referendum system should be introduced in decision-makings pertinent to public program sites involving health care and living safety. In the meanwhile, relevant measures on information publicity should be perfected and procedural regulations against viol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should be enhanced.
Key words:ballot box zoningreferendum systemcitizen participationland plan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