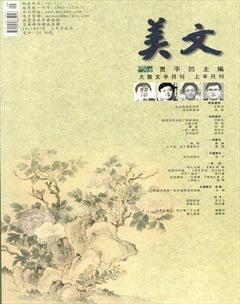诗人之旅
顾彬 朱谅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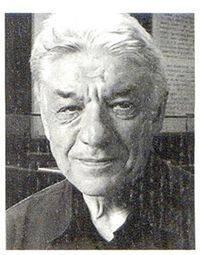
与好友举杯觥筹
胜过一切虚伪之禁欲
若爱酒之人都将入地狱
则世上无人知晓天堂
——欧玛尔·海亚姆
每一段回忆都是一段忧伤,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段回忆,故而每一次旅行都在一段忧伤中开始。我特别的忧伤名为北京,因为它的缺失让我痛惜,这也是我多年前开始写散文的缘故。那时,我的忧伤未被人带走。而如今,它却被所有人证实。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我情愿自己是错的。这是否只是一位诗人的观点?只是一位很快将与其他诗人一起从北京去帕米尔的诗人的观点?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世上的一切都是变化着的。这个世界也不会一分为二,一边是贫困的诗人,而另一边则是富有的中介。
一
1985年,我第一次和诗人杨炼在距北京动物园不远的西苑饭店见面。那时,他一边在饭店大堂等着我,一边翻看着《山海经》,如今已是2006年,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们又聚在了西苑饭店,共同思考着诗歌的声音。杨炼已加入新西兰籍,居住在伦敦。不到一年,他便在柏林买了一栋建于19世纪中叶的公寓。他曾自豪地给他的译者及粉丝寄了该公寓的照片。我作为他的德语译者,自然也收到了。从照片上看,公寓的窗户、灯具以及墙壁都经过了精心的翻修,像是在缅怀着一个逝去的时代。杨炼为何不在北京买栋类似的公寓呢?北京东交民巷 旧使馆区虽然大部已经拆除,但不是还存在一些建筑吗?虽然他多次公开批评过他曾经的祖国,但他不是还经常回去度假吗?
北京的殖民建筑遗产不在少数,但大多都衰落了。那封建建筑遗产呢?可惜它们无法使杨炼产生兴趣。它们多被少数人居住着,而且也在一步步走向毁灭。革命要求牺牲,先是房子,然后是人。曾经的旧中国,早已被新中国所取代,那些封建的东西便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如今那些仅存的些许古老建筑,要么是为旅游业服务,要么被那些经济实力强大的私企所用。如果想对此有一番了解,可以去北大具有象征意义的西门看看,那里的绿荫是曾经的圆明园的废墟。1949年后,圆明园对被解放了的人民大众开放,而这结果便是圆明园日渐的荒芜。直至不成样子了,政府才开始委托那些曾令人憎恶的商人们来挽救。经过一番修复后,圆明园的池塘、绿树交相辉映。除了一些商业组织,北大的一些学院也设在此,承担起了传承中国文化的任务。
在中国,每位诗人都有资助人,这在以前叫资助,现在改称赞助了。不过,没有哪位诗人会公开承认自己有赞助人。“诗人”也不再是单数,而是复数了。然而,这个复数却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弱势群体,虽然在国际上声誉很高,在中国本土却不受重视。如果中国官方对诗歌不扶持,即使那些耕耘在讲台上的大学教授们再殚精竭虑地推广诗歌也无济于事。几千年来,中国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盛产了众多伟大的诗人。要弘扬诗歌精神,就必须要有赞助商,引领着北大为中国诗歌事业做出表率,而此次的赞助商则是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根据《中坤集团报》的新闻,它在2006年1月投资了3000万人民币来促进(当代)诗歌的发展,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坤诗歌发展基金。3000万应该是大大说少了,据我私下了解到的信息,实际上有上10亿。
是什么让一个集团去投资这么大一笔钱,为的只是促进在中国仅是一个卑微的存在且无任何盈利的行当呢?事实上,我们知道,中坤这个1995年建立的企业,虽然起初的重点领域为房地产,但很快便发展到了其他领域。1997年,中坤国旅成立,立足于在那些看似日渐荒芜、但实际却大有可为的地区进行投资。中坤的董事长黄怒波也是位诗人,笔名骆英。他年轻、有活力、长相英俊、为人处世也十分得体。对诗人来说,他可以称得上是实实在在的“北京好人”。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2006年的9月19日。那时,他便坦诚地对我说,当代中国缺少三样东西,三样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东西:道德、权利以及诗歌。如果说中国1989年前社会主义没办到的,1992年后实行的市场经济都办到了——对崇高道德以及伟大诗歌的摧残与毁灭。然而,崇高道德以及伟大诗歌恰恰是中华文明古国一直被人津津乐道的两样东西。但现在,它们像人一样,像那些老胡同及四合院一样,都需要法律的保护。可诗歌能像北大的辽阔绿荫、晚霞中的胡同以及那些四合院一样被拯救吗?
1949年以后,中国几乎无人致力于保存老北京四合院的单层建筑,因为大家都想变得“现代”。而那时所谓的“现代”,便是以苏联那些丑陋不堪的建筑为模板,在北京城大兴土木。作为老北京建筑的四合院——中国的封建建筑遗产便开始遭受破坏,似乎这项遗产破坏了,便会有另一项遗产等着被接收。1979年以后,中国人又将美国视为现代的标志。很快,中国的电视新闻播报员便爱上了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高楼及有汽车疾驰的高速公路的背景前来播报新闻。殊不知,在一个欧洲人眼中,这样的画面不但不具备任何吸引力,反而是一种深深的刺痛。就算是那些冷酷的外国朋友,在看到这一幕时,也不禁要问:“中国人,你们真的自愿要如此生活吗?”
然而,丑的东西,就算没被拆除,也未被重建,它也是无处不在的。那些視自己为国家主人的所谓“人民”,为所欲为,对于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丝毫不知怜惜。而诗人们呢?他们虽然对衰落特别敏感,但却不具备重建的能力,而只能悲叹衰落、指出衰落。也许,在一个普遍沉默的国度,这已经很不错了。
2006年9月20日,星期三,诗人王家新及他的摄影师妻子胡敏带我去了离颐和园不远的达园后面的一个艺术村。那里与“文革”时的北京相去不远,到处都是一股年华腐烂的味道。除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日杂店以及一个妓院是新的,其他的一切都在走向衰落。还有谁会想在那驻足呢?估计也只有胡敏了。她曾与其兄——纪录片摄影师胡杰于1993-1994年在那实地拍摄了《圆明园的艺术家们》。如今,胡敏与王家新带着一个儿子,有时住在北京城里一栋实用的公寓里,有时住在乡下的一所装饰精美的农房里。至于她在拍摄那些破旧的房子、荒芜的街道时是否会有怀旧的感觉,我没有问她。
与外国人不同的是,北京当地的居民被允许穿过有警卫守卫、但对民众开放的大门,进入到已被翻修一新的圆明园。几十年来,圆明园里住着许多农户,他们随意开垦,任由着圆明园衰落。而现在,政府将其逐渐重新修复,目的是为了让前来参观的儿童、中小学生以及大学生能形象地知道,帝国主义曾经有什么含义义。当年的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在圆明园打砸抢烧,破坏文物,那便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多年来,圆明园废墟一直立着一个横幅“永勿忘国耻!”每年的三月,也就是国耻月,圆明园便成了教育基地。来参观的人格外多,而圆明园的废墟也象征性地伴随着我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我还记得1974年和其他年轻的汉学学生赴北京学习语言之前去位于波恩的中国大使馆的情景。当时大使馆的人跟我们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欧洲人把中国美丽的宫殿毁掉了。”从那以后,我脑海中便一直有一种罪恶感:所有中国的毁灭都与我有关,是我把北京毁了。
而那些既不能起到教育作用,又不(未)能作为旅游景点来推广的房屋和城市的命运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中国的私有旅游公司早已提出来了。中国的旅游景点琳琅满目,但都稳稳地掌握在国家手里。如此一来,私有旅游公司就只能自创能吸引人的景观。而其中的一个好策略便是:將某个农村整个买下来,然后在那里建高级酒店。虽说土地还和以前一样属于国家,但一旦掌握了土地使用权,便马上能成为新主人。那村民怎么办?他们有两种选择。第一,搬进开发商在酒店周边建设的新村落;第二,住在开发商修缮过的房子里,充当守护。这两种情况下,开发商都可以通过收取门票的方式,让充满好奇心的游客来买单。只是在第二种情况下,当地的土著居民便突变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
中坤集团便是这样发家致富的,除了京西的门头沟旅游板块以及安徽黄山旅游板块,中坤还选择了一片危险的地区——南疆,新疆多山的边境地区,简称帕米尔。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地区开展旅游业,这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它也许意味着那些百年老城将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迪斯尼乐园。我不能问新疆当地居民的看法,因为他们不会汉语。如果碰巧遇上一个会汉语的,其汉语水平肯定不如我这个欧洲汉学家。我只能相信我的眼睛,而我的眼睛注意到,喀什建在黄土高崖上一处名为高台的地方,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出于安全的考虑,原本是要拆除的,但现在,高台不仅有流动的水,而且由于发展旅游的原因,给该地区带来了工作岗位,它还收取与喀什老城区价格相当的门票。中坤在这里也投资了,索要的门票价格为30元。
只是,来自东西方的诗人与遥远的帕米尔有关联吗?还真有,而且这关联还不少。新疆独立了几百年后,在清朝才又被重新划分为其边境。1957年至1978年,新疆是很受欢迎的流放地。毛泽东1956-1957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名为促进文化事业,实则是为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做准备。很多人被送到新疆强制劳动,进行思想改造,曾经担任中国文化部长的作家王蒙(1934-)就是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在“文革”时期,又有第二代人被送到新疆。他们都是些刚初中或大学毕业的人,来向目不识丁的农民再学习。无论是农民还是这些下乡的人,骨子里其实都不愿意与对方打交道。对这段要求身心均衡发展的时期,也只有王蒙给予了积极记载——是新疆的回族人教会了他幽默,挽救了他的生命。但这一点,我们在“文革”结束3年后的1979年才知道。而被送到新疆沙漠改造的知识分子人数高达50万。在平反前,这些人只能保持沉默,没有人替他们说话。虽说这些都已过去,但诗人们呢?他们还能像80年代的文化热那样,大声抒发脑中所想、心中所思吗?他们还能把自己的声音借给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吗?
在去新疆之前,2006年的9月19号至21号,诗人们在西苑饭店开了几天封闭式会议。欧阳江河(1956-)直率地指出当下中国人生活不易;美国作家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1949-)则叹息中国正在重蹈西方的覆辙;文学批评家唐晓渡(1954-)警告大家说话要小心,因为到处都是麦克风。不过,我们好像对此都不以为意。私下里,我们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并没有什么顾忌。对于外面《新京报》及《南方周末》的记者,大家也都没什么忌讳,尽管我们知道他们将全场陪同我们从北京去往喀什,进行整十天的跟踪报道。
诗人们的步伐,也许最重要的一步是在400位热情的北大听众前的多语种朗诵会。在之后的新疆之旅中,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大学拒绝了一次类似此次朗诵会的免费活动,理由是无人对此感兴趣,弄得我们最后只好在乌鲁木齐的一家酒吧开了朗诵会。就这样,北大便成了日本女诗人白石嘉寿子(Shiraishi Kazuko,1931-)那些柔软而悲伤的诗歌最后的避难所,它们与她手中打开的纸卷一样,一起飘落到了地上,上演了一场视觉的盛宴。那听觉的盛宴呢?多多(1951-)与欧阳江河(1956-)还能像以前的诗人一样吟唱,而不是那索然无味的读诗。艾略特·温伯格以及法国的安德烈·维尔泰(André Velter,1945-)也分别用他们自己的母语吟唱了诗。他们是否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如果有的话,那也许就是缺失。诗人都离不开缺失这个话题,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喀什,都一样。欧阳江河作为中国诗人的秘密武器,一直叹息着三重缺失:好中文的缺失,海内外好中国声音的缺失,以及传统的缺失。真的有这么糟糕吗?也许事实比这更糟糕。诗人们已经开始变得沉默,有的是因为不想重复自己,有的是因为未能继续发展。翟永明(1955-)属于前一类,芒克(1950-)则属于后一类。美丽的翟永明在此次的新疆之旅中,便不想让我这个将她诗歌译为德语的人坐在她旁边,不断对我说:“你还是坐到别处去吧。”而芒克则一直跟我谈论着过去,仿佛过去还能再复活一样。
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13个世居民族,大部分人都信奉伊斯兰教,禁酒。然而,诗人若没有好酒,那又算得上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说,有酒才有诗。去新疆前,我妻子忧心忡忡地警告我:“你要小心那些柯尔克孜族人,他们并不遵守禁酒令,喝起酒来都是大碗大碗的下肚,你当心喝趴下。”不过,她和你们,我亲爱的读者们一样,哪里知道这些年来,我已经练就了一番喝中国酒的好本领?
八十年代初,北岛领着我走进了中国白酒的世界。那时,我们喝的是国民白酒二锅头。二锅头不同于那些名酒如茅台、五粮液等,价格很便宜,五、六块钱便能买一瓶。但无论是52度、56度还是60度,喝过之后,我第二天早上一准头疼。每次头疼时,我总是断然发誓再也不会任北岛给我灌酒。如今,北岛还是从2毫升的小酒杯里喝白酒,而我却不同,更钟情于0.2升的葡萄酒杯。为什么会这样呢?难不成我成了酒鬼?才不是呢!用葡萄酒杯喝白酒,才能真正掌握喝白酒的艺术。这一点,是我在济南做客座教授时摸索出来的。用大酒杯喝酒,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在斗酒时知道自己每次喝了多少。反之,如果用小酒杯喝,极易控制不住,也不好算出到底喝了多少。大盏喝酒更能掌控自己的喉咙。如果打算要大喝一场,不醉不归,那一定要准备另外两样东西:水和茶。当然了,白酒的质量也很重要。孔圣人家乡所在的山东省喝酒时的建议是,每喝一杯高浓度的白酒,就接着喝一杯水或一杯茶。山东很流行喝70度的白酒,虽然度数高,但如果喝得得当,倒也没什么大碍。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每年我去青岛作客座教授时,都会受邀去喝当地的琅琊台酒,但我从未喝趴下过。第二天早上起床时都心情愉快、精神抖擞,因为我喝酒时,总不忘兼着喝茶!
其实,让人更捉摸不定的是从酒瓶里倒出来的酒。在喝第一口前,我们是否能判断它的好坏?是的。对懂白酒的人来说,酒的颜色和气味十分关键。要想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白酒的好坏,需要对眼睛和鼻子进行多年耐心的训练。不过,如果你不幸被派做一个旅游团的代表,去与蒙古人或者柯尔克孜族人斗酒,你就会发现,这项多年的训练还是值得的。虽然我并不愿意,但我还是被推举为此次新疆之旅的斗酒代表。不过,与我妻子及亲爱的读者们可能想得有所不同,我并未在此次的多民族斗酒大会中沦为失败者,但这是后话了。斗酒前,我们得先动身离开熙熙攘攘的北京,去到新疆的最西南——人烟稀少的喀什。
西方的游客经常在喀什缅怀曾经的丝绸之路上所发生过的无数传说,也或多或少成功地找到了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1907-1971)提到的鞑靼的足迹。他们也许可以在随处可见的集市或是喀什著名的星期日市场找到自己心仪的玩意,可那些不愿去购物、宁愿像孔子一样远离商贾的人要做什么呢?也许在看到褐色的绿洲时,他们会把空气与光线作为思考的对象?以前,人们习惯说天很高,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全都是这样的。但70年代以后,天好像在很多地区慢慢下降了。大城市大多都见不到一望无际的蓝天白云,空气也变得污浊。东南沿海地区都奉行“致富为上”的方针,至于代价有多高,全然无所谓。以前,由于沙尘与云层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周大约会出现一次灰蒙蒙的天。可现在,大城市因工业浓烟及暖气的原因,基本上每天都笼罩在一片灰色之中。不过,喀什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城市,也许它也从未想变得富裕。与北京、青岛、上海等城市相比,喀什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时的香港,到处都是了无生机的宽马路、丑陋的混凝土建筑以及破败的风景点,毫无东方浪漫主义的痕迹。此外,喀什的博物馆也很衰败。在破旧的窗户及吱呀作响的门后,除了些许能证明新疆在公元前1世纪(汉朝早期)便已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文物外,几乎什么也没有。
不过,喀什虽然落后,却是阳光充足、空气清新。这两样东西与从沙砾里发掘出来的一件唐代丝织品一样,经受住了时间的洗涤,如今在喀什陈列品甚少的博物馆发着绿光。另外,喀什郊区有许多面积宽广的果园,它们大多位于私人的庭院里。我们到的那天晚上,也就是9月22日,便被中坤集团新疆子公司的经理,一位维吾尔族人,邀请去吃晚餐。在高阔的大厅里,矮桌席地而摆,我们脱鞋入座,先享用着蜜瓜、馕、酸奶等。在上羊肉前,也没人在乎什么禁酒令,端上了苹果酒。不过,我和在座的其他人一样,更喜欢随后上的伊犁白酒,它虽然只有52度,但喝着很舒服。那天晚上,我们并不需要做出什么真正的牺牲,主人并没有与我们斗酒,我们可随自己的心意决定是否喝空大酒杯里的酒。虽然如此,几天后要与柯尔克孜人斗酒的“三剑客”已在当晚的酒桌上初露端倪,他們便是:伊朗诗人艾姆朗·萨罗希(Ehmran Salahi,1947-2006),他生命最后时刻中最快乐的日子便是与我们度过的;苏格兰诗人威廉姆·赫伯特(William Neil Herbert, 1961-),当时他还不知道维吾尔族白酒的厉害;以及我这个中文名为顾彬 (1945-)的德国诗人。虽然我们在理论上与实际上都准备得非常充分,但在那之前,我从未喝到过假酒。我们“三剑客”还有个替补——杨炼,但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擅长的是将手指放到喉咙里,“吐”才是他的真正绝活。我们这四个笃信斗酒必赢的人,是当晚最后离桌的。我们尾随着最后一小拨诗人,穿过一个长满葡萄的院子,于一片黑暗中,朝大广场的位置走去。那里的毛泽东雕像前正举行民间表演,载歌载舞的大多是老人,他们技术娴熟,衣物颜色斑斓,甚是美丽,只是音乐太吵,使得我们很快便想离开了。
我们为何要看落后、慢节奏的东西?因为它们有自己固有的好处。30年前,北京与广州之间的每一步,都好像要凝固在一张画里。但现在,香港和台北的快节奏也蔓延到了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不过,我们入住的喀什酒店却丝毫未受影响。我们是酒店唯一的客人,那些穿着维吾尔族传统服饰的年轻女服务员们分布在酒店各处,热情地询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求,是否要用餐等。我们这些人要求都不高,所以很少需要她们的服务。她们于是便像画里凝固着的人一样,一整天都满脸期待地立在酒店各处的门口。她们没戴面纱,这一点,与随后的一天上午在离香妃墓(香妃据说全身散发着橄榄香,是乾隆皇帝的爱妃)不远的一个果园里等着为我们唱歌跳舞的姑娘们一样。她们跳的很有诱惑力的肚皮舞,一边欢乐地跳着,一边还玩笑式地邀请我们跟着一起跳。只可惜,我们跳得非常不怎么样。难道是因为我们都老了?还是因为我们太拘谨?抑或是我们太笨手笨脚?也许都有可能。对有些诗人来说,在长满果实的外廊享用苹果或无花果,比看肚皮舞要安全多了,可落荒而逃也不是个办法。我们中有些诗人很快便在考虑,是否要将此次旅途所写之诗献给这些随时期待我们光临的肚皮舞者。她们无忧无虑的纯真,难道不显然与30多年前中国人的纯真一样吗?那时的男人与女人,不是不太明白男女之别吗?
不过,喀什也慢慢浸染上了新时代的印记。建于1442年的清真寺,曾经是喀什最高的建筑,也许它现在依然是最高的建筑,但它旁边的大广场上却已是商铺林立,使得尖塔显得比它实际上要小。编筐匠、磨刀匠、牙医以及铜匠都在此安定了下来,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中世纪,那似乎永不会停止的中世纪。
参观清真寺前,原本允诺的当地红酒并没有出现在午餐桌上,理由是我们不能带着酒气进入清真寺。对此,我们表示了理解,而这理解也得到了补偿。清真寺的大庭院,树木众多,十分凉爽,对抵抗炎热很有裨益。我们的眼睛随着希腊风的柱子,流连于寺内深处。只是,当我们晚上在广场头号餐厅用餐,连啤酒也不被允许喝时,有些诗人便开始觉得晚餐索然无味,而更期待晚餐后将举行的关于诗人之地的会议。骆英则悄悄地在饭店隐蔽处塞给我们从北京带来的一瓶白酒及一些啤酒,并请求我们在喝的时候小心,不要把酒洒在地板上,否则酒香会留在空气中。要是被人发现,他作为此次新疆之旅的头目,一定会很难堪。我们当然愿意满足他的要求。对饥渴之人来说,每一滴酒都弥足珍贵。就这样,在稍后的中英双语会议中,不仅诗歌,连白酒也有了自己的声音。总的来说,一共有两种声音,这两种声音也是文学批评家唐晓渡倡导的:一种是在中国的声音,另一种则是在德国的声音。西川(1963-)忙着给艾略特·温伯格翻译,因为温伯格不会说中文,但却能将北岛的诗翻译成英文。此二人头脑都十分冷静,是此次新疆之旅中唯一拒绝喝酒的人。无论是多好的酒,他们都不沾,一路上只喝开水或茶。至于这是否能让他们更好地欣赏之后的七彩美景,我表示怀疑。如果只将中国白酒简单评定为是一种酒精度高的酒,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饮法得当,中国的白酒可以作为良药,能驱赶疲惫,令人重获力量,既能温暖身体,也能梳理思想与灵魂。
在会议上,西川激动地抱怨着美国没有为中国当代诗人说话的声音,甚至多次将美国与欧洲画为等号。听着听着,我不仅在心里暗暗发笑。西川不知道,中国当代诗歌早就被翻译成了德语,德国对此的文学研究也非常之多。虽然翻译在德国学术界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它并不像在美国一样被视为低级工作,不适合在大学研究等。
在新疆旅行,意味着要长时间在迷你巴士上坐着。沿途基本上没什么人,也没什么村落,乘客的一些自然需求便只能以古老的方式得到满足,女乘客和男乘客分别去巴士车左边及右边为数不多的树林子里解决。至于饮食,在那些有绿树及多水的地方都零星地分布着大大的帐篷,我们可以在那舒服地吃饭。帐篷前也像史诗中描写的那样,有漂亮的女舞者在等待我们这些诗人的到来,邀请我们一起载歌载舞。但我的目光不是看向她们,而是更多地伸向远处的高山。我老问喀什的维吾尔族导游,白沙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以及帕米尔有什么区别。每次,导游给我的答案都不一样,每次给我指的山群也不一样。那些山,有的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有的显现在灰色的沙漠中。最后,导游指给我看的是被一团红色包围着的群山以及冰山的黑色熔岩。而我,也只能满足于这些解释。事实上,回到家后,我查看了一张中国地图,才知道了真正的答案。不过,我却由此变得更困惑。如果一座群山长1200千米,高7000多米,那还有必要去询问它的名字吗?
新疆过去不仅是流放地,也是分别地。古时,士兵及官员离开疆土,踏上丝绸之路,通常都会有亲朋好友给他们斟酒践行。据记载,除了喝酒,还会有歌舞表演,以及那些垂立在一旁的忧伤女仆。柯尔克孜依旧保留了他们在地区入口处用白酒及饼干欢迎客人的习俗,俗称下马酒。我们“三剑客”对此早就做好了准备。那是一个早晨,主人将52度的白酒倒在了小杯里,是为了给稍后在乌恰城吟唱柯尔克孜英雄史诗《玛纳斯》暖身。
《玛纳斯》叙述了9世纪柯尔克孜族传说中的英雄和首领玛纳斯及其子孙反抗异族的斗争故事。该史诗于10世纪流传下来,20世纪时其片段被重新修复。而其吟唱者,竟然将长达20万字的片段大声背诵了出来!这让我们这些诗人很是汗颜,因为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背诵出自己哪怕一首诗!
谁喝了柯尔克孜人的下马酒,便会受到柯尔克孜人的款待。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十人一组,盘腿而坐后,便开始交替着与主人用大碗拼白酒。每碗都裝有二两酒,摆放在接待处的一个托盘上。大家都是拿到酒碗后,一口气喝下,然后将酒碗放回托盘,只有我是唯一一个小口抿酒的。到了第二轮,有些人就撑不住了,不得不离席去洗手间。而当时没事的,很快便会有事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很快”将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们从未想到,下了马的人,还得再上马。第三轮过后,我们都没事,全无一点醉意,于是决定先去骄阳下的大广场看歌舞表演,然后去市郊,观看用死羊来进行的马球比赛。看歌舞表演时,我们坐在椅子上,面对着苏联式的建筑,觉得甚是无聊。而看马球比赛时,我们是坐在马上欣赏。阴沉沉的天空下,球员分为两队,手举着羊,狂野地努力将羊扔进球门,与普通的马球比赛相比,蔚为壮观。
柯尔克孜人不会中文,但他们会热情好客之语。到了目的地后,我们得下巴士车。谁料等待我们的又是白酒,而且是大碗的!这就是所谓的上马酒,这让我们有些诧异,但我们还是把酒一饮而尽。只是我们不知道,饮尽后,马上又有满满一托盘的酒碗被递到我们面前。
从中午算起,苏格兰诗人威廉姆·赫伯特一共喝了四大碗,我应该也不少于这个数,而我们的伊朗朋友则认为自己能喝七碗。在回去的路上,大家都哼着歌,我则醉心于欣赏沿途山峰变化莫测的奇妙色调,只可惜这美景一共不过半小时。但就算为此要喝再多的酒,也是值得的。真的是这样吗?杨炼——我们原本的替补,吃过午饭就吐了,而自称能喝一瓶半白酒的骆英也在回去的车上吐了。我们“三剑客”呢·威廉姆·赫伯特在到达了酒店后很快就睡去了,而艾姆朗·萨罗希则被三个朋友一起从巴士车里驮到了床上,虽然他的样子看起来只是微醉,但却自己动不了。我呢?我没事。作为“三剑客”中唯一屹立不倒的我,晚上还接着喝,与那些平常不大喝酒的军官喝。我以为如果按照山东喝酒的方法,喝一口酒,喝一口水或茶,应该没事,但我万万没料到一件事。我早就听闻中国有很多假酒,但我从未喝到过。不料在酒店的餐厅,却有人在酒里掺了水。刚喝了一杯半(葡萄酒杯),欧阳江河发现我神色不太对,便推断说这酒肯定有问题。一听到这,我便飞也似的回到房间,马上开始效仿杨炼,将手指伸到喉咙里。吐出来后,我舒服了一些,头脑也很清醒,但身体却不听使唤。我在洗手间呆了好几个小时,才慢慢积攒了些许力气,摸索着爬到了床上。
虽然与军官们的那顿晚餐惨不忍睹,但我们与人民解放军所用的早餐却很不错。我们围坐在大圆桌上,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似乎诗人与士兵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而那顿早餐,也并非是解放军邀请我们的最后一餐。在喀什军事基地,外国人原本是不能进去的。但骆英却将那里的士兵称为真正的士兵——他最好的朋友,于是我们得以进去。平常在喀什市,一般都看不到这些士兵的影子,就像诗人在世界里扮演着隐身人的角色一样。但在宴会时,这些士兵都努力让自己被人注意:汉族人给我们做饭,也给我们上酒上菜。当地的特色是野蘑菇与野蔬菜。这种“野”很合我们这些诗人的口味。伊朗诗人艾姆朗·萨罗希也和我一样,十分好酒。好酒好菜,岂不美哉!
然而,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段回憶,而每一段回忆都代表着一段忧伤,故而每一段旅途都以忧伤而结束。
在回北京的路上,我们顺道去了乌鲁木齐。街道两旁种满了树,和曾经的北京一样,但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却只有上星期的,去银行也不能像在上海或青岛那样随意取钱。这种落后,其实是很适合诗人的。只可惜,新疆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大的大学,没有人想听诗人的声音。我们只好最后一次把它送给自己,送给和我们一样的诗人。骆英让人在一家酒店准备了一些当地的红酒以及一些吃食,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诗人、翻译还是朗诵者,都收到了一束花作为临别礼物。当地的电视台给我们摄了像,以便向世界报道。
我将带着什么回北京呢?一束来自乌鲁木齐的百合。在分别的前一天晚上,我记得那是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骆英又让人摆上了红酒。红酒瓶上标注着“内部使用”的字样,属于中法联合生产,每瓶价值200美金。这对艾姆朗·萨罗希来说,是一个很庄重的道别,算是圆了他的中国梦。我们相拥告别。他不会中文,也不会德语,但他用拙劣的英文告诉我,他能理解我的声音。我不懂他的母语,却懂他诗歌的英文翻译及他吟唱的《纸飞机》及《1001面镜子》。柯尔克孜人也很喜欢他的吟唱。在县级市阿图什创建20年的庆祝会上,艾姆朗·萨罗希作为世界诗人的代表,在帕米尔自由的天空下吟唱。结束后,柯尔克孜人热情地向他抛洒金属箔条。难道说柯尔克孜人不仅懂白酒,也懂诗?也许吧。不过,我们也不想过于夸张。
艾姆朗·萨罗希回去后,肯定会向他的朋友们讲述他那终于圆了的中国梦。他也许还会喝酒,虽然他的中国翻译在临别前竭力劝阻他不要再喝。只可惜,他的心脏不能再一起快乐了。他回国后没多久,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对此,我们能送上的,只有一首诗,一段沉默,一份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