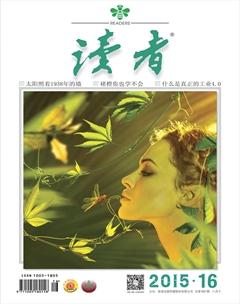父母的二战往事
普京

父亲主动要求上前线
战争爆发的时候,父亲在一家军工厂上班而无须服兵役,但他写了入党和上前线的申请书。就这样,他被派往了仅有28人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别动队。队伍被投送到德军后方,完成炸桥和破坏铁路等行动,但他们几乎立刻就中了埋伏——有人出卖了他们。法西斯分子在树林中不断搜索,但父亲活了下来,他在沼泽地里躲了几小时,用芦苇秆来呼吸。
我记得很清楚,父亲曾对我说,别动队队长是个德裔公民,但其实他还是德国人。
值得一提的是,两年前有人从国防部送来了该别动队的档案。我在新奥加廖沃的家里珍藏着档案的副本,上面记录了小组成员名单和简短介绍。是的,一共28人,队长是德国人,跟我父亲说的一样。28人上了前线,仅有4人活着回来。
在列宁格勒身负重伤
后来,幸存者被派到列宁格勒郊外的部队。当时这里是德军包围的最热点地区,战斗异常激烈。父亲说,他在那里受了重伤。腿上的弹片未被取出,伴他走完了一生,从此落下了病根。
当时,他和战友向德军后方出动,他们爬啊爬,结果爬进了德军的火力点,遭到了敌方的机枪射击。从敌方走出一个健壮的男人,父亲说:“那个男人仔细地看向我们,然后接连向我们扔出了手榴弹。”生命就是这么简单又残酷的东西。
那么,父亲恢复知觉后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当时已是隆冬时节,涅瓦河上结了冰,他需要爬到河对岸寻求专业的医疗救助。但父亲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个河段被纳粹的炮火和机关枪控制,几乎没有东西可以掩护他爬到对岸。但巧合的是,父亲竟然碰到了在彼得霍夫的邻居。邻居毫不犹豫地把父亲弄到了医院,两个大活人是爬过去的。邻居一直在医院等着,直到确认父亲做了手术,然后他说:“好了,现在你活下来了,我该去赴死了。”于是邻居又返回了前线。
此后,他们彼此失去了联系,父亲以为邻居已经不在了。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父亲回到家后哭了起来,原来他在列宁格勒的商店里偶遇了这位救命恩人。
从死神手中抢回母亲
母亲讲述了她是如何到医院探望受伤的父亲的。列宁格勒已被希特勒的军队牢牢围困,人们忍饥挨饿。当时他们有一个3岁的孩子,父亲背着医生和护士,将医院的份饭偷偷交给母亲,好让她带回家喂孩子。后来父亲饿晕在病房,医务人员搞清状况后不再让母亲探视。
后来孩子被抢走了。母亲说,为了不让小孩子们饿死,他们被集中在幼儿园等待转移,这甚至不征求家长的意见。这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哥哥,在幼儿园得了白喉病,最终没能活下来。父母甚至没被告知他葬在哪里。
失去孩子后家里只剩母亲一人,当父亲拄拐出院回家时,看到卫生员正在往外抬饿死的人。在这些人里他看到了母亲,但他觉得母亲气息尚存。父亲对卫生员说:“她还活着!”卫生员却回答:“路上她就会死的。”父亲说,当时他举起拐杖冲向卫生员,强迫他们将母亲抬回屋内。在父亲的照料下,母亲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了1999年,而父亲则在1998年年底去世。
父亲一脉是个大家庭,他有6个兄弟,其中5人死于战争。对一个家庭来说,这是场灾难。母亲家也有亲人死亡。我出生得晚,母亲41岁才生下我。
我是在仇恨敌人的苏联书籍和电影中长大的,但母亲完全没有这样的情感。她的话我记得非常清楚:“能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呢?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普通的劳动人民,只是被赶上前线罢了。”
这些话,我从小时候牢记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