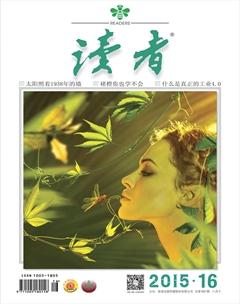我的生死北大
阿忆

王 力
1
从北大图书馆南门回本科生宿舍区,有一条穿越燕南园的近路。上中学时我就知道,燕南园是北大著名学者居住的别墅区。那时,我认定中文系是我的最佳选择,知道了燕南园60号别墅住的是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
王先生学越南语时,已经72岁,越南语成为他熟练掌握的第7种语言。这让我无法不自惭形秽,我14岁开始学英语,却认为太晚了。
我知道王力先生,是因为他编著了4卷《古代汉语》。我一直不知道王先生要花多少时间记忆,又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写完这部巨著。究竟有多少汉学家曾受益于它,谁也无法统计。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4卷书为王先生带来了惊人的版税收入。刚入学的第10天,中文系指派高年级学生王川带我们拜谒王力先生,路过燕南园南边的工商银行,王川说,这银行的半数存款是王先生一个人的!
进60号楼之前,王川叮嘱我们,见王先生时,“切忌手在脸上乱摸乱抠”。这句嘱咐,让我觉得王先生十分神圣。等到我作为高年级学生带新生拜谒前辈时,“不得乱摸乱抠”也成了一条铁打的戒律。我痛恨一切把这句话当耳旁风的人。我们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雨,去参拜长者,除了毕恭毕敬之外,别无他选。
王先生家最让我垂涎三尺的,是客厅墙上挂着的梁启超写给先生的条幅。另外还有一幅水墨画,是老舍的夫人胡絜青画给先生的。
先生家到处都是书,包括厕所,因此60号别墅显得拥挤不堪。后来我发现,因为书多而拥挤不堪,是所有学者家居的特点。前不久受香港传讯电视之托,在朗润园采访87岁的季羡林先生,老人家的两套单元房,全部被书刊占据。

朱光潜
我入学时,王力先生已超过80岁。他既是老人,又是孩童。王先生曾拉住我的手说:“听说你们班出了个陈建功……”大家窃笑。陈建功是77级学生,当时已因《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蜚声文坛,而我们进校时已是1983年。
提起“文化大革命”,王先生十分委屈地说,当时的红卫兵还没有我们大,却伸手戏摸他的光头,先生从没受过此等委屈,认为这比让他死还要可怕。
由于身体原因,王先生已深居简出,但当年的中文系元旦联欢,先生还是被搀扶着出席了。我实在不清楚,毛孩一帮,群魔乱舞,先生何以看得津津有味、笑逐颜开。
上二年级时,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写一写燕南园主人们的晚年,写写他们如何在阳光雨露下颐享天年?我怕别人赶了先,没打招呼便直奔60号楼,按了先生的门铃。先生下楼后,坐进沙发。当他确认我没有预约,便无论我问什么,回答只有两句:医生不让我多说话;你没有预约。
没有想到,10年后我自己也经常被人造访,而我最不喜欢的,也同样是不速之客。
不过,没等到我悟出此类同感,王先生已经作古,终年86岁。
2
上中学时,我们常去北大玩耍。有一次,途经燕南园一段残垣断壁,看见一位十分矮小的老人,静静地坐在青石板上。看到我们走近,老人拄起拐杖,慢慢绕到残垣之后,隔着那段残破的矮墙,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
同学们一定是被老人家浪漫的举动吓坏了,便加快脚步,慌张地跑掉了。我只好一个人走上前,站在矮墙外,双手接过小花。我看见老人的嘴角在动,我知道,他是在努力地微笑。
直到考上北大,我才知道,老人家竟是美学大师朱光潜。但我无论如何无法接受,那位写出鸿篇巨制的朱光潜,竟会是如此矮小的老人!他学贯中西,学富五车,身高却只有1.5米。
那些年的中午,每逢我从图书馆抄近路回宿舍,总会看到朱先生独自静坐在青石板上,目光中充满童真,凝望着来来往往的后生。
先生对后生的爱,听着让人动容。那时,许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时常到先生家领受钱票。
大三的时候,我从燕南园独自穿行,途经那段残垣,先生又一次隔着矮墙,送过来一枝小花。
直到今天,我一直偏执而迷信地认为,那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它分明是人类精神之树的果实,是一代宗师无言的暗示。在即将熄灭生命之火的岁月里,先生不断越过隔墙,把旷世的风范吹进晚辈们的心灵中。
朱先生病故时,是89岁。听闻先生驾鹤西去,我驱车回家,把那部夹着两朵小干花的《西方美学史》点燃,心中默念着: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3
王瑶教授是我所见过的先生中,寿命最短的一位。但他74岁时,记者还误以为他会长寿。
记者问他:“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王先生答曰:“秘诀有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
王瑶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完全继承了朱先生的遗风。他从不给研究生上课,而是像朱先生那样把学生们请到家里喝茶,他自己则像朱先生一样抽着大烟斗。据说,王先生所有的研究生也都个个继承了王先生的衣钵,信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是长寿之本,因此大多体弱多病。

王 瑶
1996年,我为中央电视台系列专题片《香港百年》做总撰稿,每星期要去港澳办文化司审节目。谢伟民是王先生的博士生,在那里当处长,我见他不吸烟,便责问他为何不发扬先生的健身法则。谢伟民立即辟谣说,先生以身作则是真,但弟子全部效法是假。
不过,如此浪漫的讹传佳话,我简直不忍截断,所以至今仍热衷于以讹传讹,不在话下。
王先生溘然长逝时,恰是他发表长寿宏论的第二年,终年75岁。
4
大三的时候,我对中文系厌倦到了极点,闹着要转到法律系。正是这时,我们开了一门新课,是“民间文学”。
开课大约4周之后,我才勉强听了一堂课,原因是听说授课教师是屈玉德,她是金开诚先生的太太。当年“金开诚”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不光是语言学家,而且是社会活动家。他的太太该是什么样子呢?
事实上,第一次上屈教授的课,我就被吸引了。但吸引我的不是她的民间文学——她讲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只是望着她发呆。
听说金先生娶屈教授时,屈教授是北大第一美女,但眼前的屈教授,已被疾病改变成另外的模样。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中,屈教授祸不单行,患了咽癌。长期的痛苦完全摧毁了她青春时代的美丽容颜,也差不多摧毁了她的发声器官,她竟以鼻音方式为学生们讲了十几年课。
记得1985年隆冬一个极为严寒的早晨,刮着凛冽的北风,本来就不乐意忍受屈教授难听的鼻音的同学,这下就更不愿意离开热被窝去教室上课了。那一天,屈教授在教室里耐心地等待着,但可容纳百人的教室只稀疏坐着7名学生。她没有像往日那样点名,把没来的人登记下来。她望着窗外的风,低声说:“有7个人,我也会来上课。即使只有1个人,我也会来。不过,如果1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但这不可能发生。”
当时,我们在座的7个人都很难过,课后讲给没来的同学听,大家都后悔了。
我有一个夙愿一直没有完成,我想亲口告诉她:“我敬爱您。”
1989年4月15日,屈教授咽癌扩散,与胡耀邦总书记同一天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