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消解“派”藩篱提高“评”成色
居其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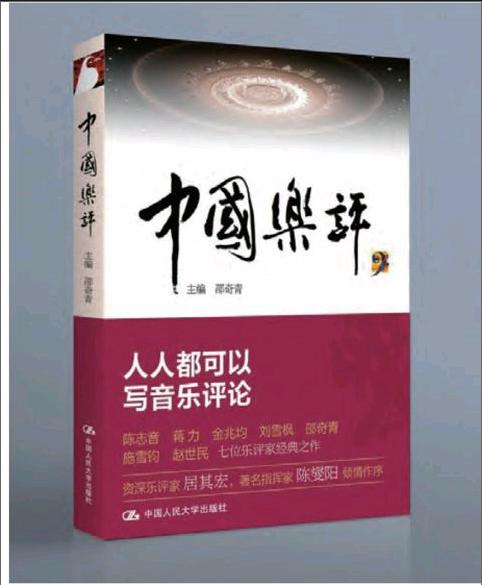
收入这本《中国乐评》中的作品,是近年来在我国音乐批评领域十分活跃的七位知名乐评人陈紫茵、蒋力、金兆钧、刘雪枫、邵奇青、施雪钧、赵世民(按姓氏汉语拼音第一字母排序),按照本书主编邵奇青“麻辣烫”要求,从各自作品中选编出来的乐评文字。
在七人中,蒋力、金兆钧是我在歌剧界和音乐界的老友故知,彼此接触较早,公私交往甚多,情谊亦深。陈紫茵曾在《中国音乐报》与我有过一段短暂的同事经历,后长期在《音乐周报》工作,我是该报读者和作者,亦常读到她的乐评和报道。我与赵世民相识,是他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期间,本人一篇论战文章即经他之手发表于该刊:后来便极少见面了。与邵奇青相识虽迟,但拜读其洋洋洒洒之文在先,亲睹其雄健豁达之人于后,在推杯换盏、大声说笑中,当时即生相见恨晚之感。唯对刘雪枫和施雪钧二君,因早就读过他们的不少作品而清誉灌耳,可惜至今未有一面之缘,深以为憾。
大概因为我在音乐界混迹已久,也经常发表一些音乐批评文字,与上述七人算是广义上的同行,故此在本书行将出版之际,主编邵奇青约我为之作一篇序。
其实,按照邵奇青对乐评人的分类,我自然属于“学院派”,是有可能被所谓“在野派”视为“非我族类”的。之所以依然命我为之作序,大概是有感于我的某些批评作品似乎介于“学院派”和“在野派”之间、可能具有若干“中间派”色彩之故吧。
依邵奇青之说,乐评或乐评人可分为“学院派”、“在野派”,基本根据有二:其一是乐评人是否系学音乐出身,其二是乐评作品的品格或成色。
在我看来,出身问题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中国历来就有“好汉莫问出身”的古训,就连大名鼎鼎的汉斯力克和罗曼·罗兰也不是地道的音乐科班出身,但又有谁敢于否定这两位批评家及其批评作品在欧洲音乐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呢?即便是音乐科班出身如从各类音乐艺术院校音乐学系毕业的优秀学者,也未必都能写出高成色的批评作品。因此,与专业出身相比,乐评作品的品格或成色才是衡量一个乐评人及其作品高下优劣的唯一标准。
为此,我很赞同施雪钧在《乐评家的“脊梁骨”》一文中提出的优秀乐评四标准,即“准确、到位、深刻、麻辣”,以及达到这个标准必须具备的三条件,即“一定的人文功底、审美眼光,较高的音乐素养”:而赵世民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音乐丰富你的体验,哲学创造你的深悟,诗歌锻炼你的语言。有了这三样,你就可以写出血肉丰满、骨骼强劲、灵魂激荡的音乐评论。
无论是施雪钧的四标准、三条件,还是赵世民的“这三样”和“三境界”,说的都是乐评人的修养和乐评作品的成色,而与乐评人的专业出身并无太大关系。
当然,有一些话还有必要加以扩充,做进一步的展开,方能令我们的表述更臻完善。
首先,乐评人之所以被称为“乐评人”,他们的批评作品之所以被称为“乐评”,第一等的要务当是音乐。说这话看似废话,但却关乎乐评之大本。评乐、论乐的前提是爱乐,挚爱于它,痴迷于它,将它视为生命必需、灵魂鸡汤,或是精神家园和梦里情人,而不论是否学音乐出身。有些终身以音乐为业者,但未必真爱音乐,一不听音乐会。二不进剧场看戏,三不关注当下鲜活的音乐事象,仅仅满足于书斋作业;其所以经常涉足乐评,更多将它当作谋生之道、进身之阶而已。他们的乐评作品,看似有乐之形,实质无乐之魂。但也不能因此而以偏概全。在职业音乐家中,挚爱音乐、与音乐相伴终生者不乏其人,他们的乐评作品非但有乐之形的描述、乐之技的分析、乐之美的玩味,亦有乐之情的挥洒、乐之思的阐发和乐之魂的张扬。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被陈紫茵称为“老专家”、“大学者”的梁茂春、杨燕迪、韩锺恩、明言等人,以及未被入选的“硬骨头音乐家”贺绿汀等中国乐评老前辈。
对“在野派”的大多数乐评人而言,他们之涉足乐评领域,是由乎自然,发乎性情,全然出于对音乐的真情、真爱和痴迷而毫无功利性算计,为此,他们在本职工作之外,用大量业余时间,自掏腰包听音乐会、看戏、买光碟,全身心沉浸其中,为之陶醉,为之歌哭,始终保持与周遭音乐现实的血肉联系,用他们各自的心灵和个性化视角来感受乐坛风云,臧否艺术得失,阐发一得之见。
但也并不是所有音乐爱好者都能成为乐评人。固然“音乐评论人人都可以写”,但也不是举凡喜爱音乐的人就愿意、就能够、就一定能写好乐评。事实上,在当下中国,音乐爱好者多得无法确计,但真正动手写乐评者还是极少数;写出来的作品能够见诸报刊者则更少之又少;发表之后在音乐界引起同行注意、产生广泛影响,在读者中激起赞赏和共鸣者,除本书这七位作者外,即便乐观估计大概也不出一二十位。因为,乐评毕竟不是爱好者随口说几句好与不好或者喜不喜欢之类听后感和随想的实录。为此,陈紫茵提出乐评“有基本标准但无统一标准”说,其言甚善惜未展开;倒是施雪钧指出的,乐评人要“依据自我音乐积累以及喜好、感受”,对音乐“作出评判”,而此评判又要达到邵奇青提出的“有感而发,有理有据”及蒋力所言始终围绕“乐”或“艺”置评且“有感而发,有据可凭,点到为止”,故此施雪钧强调之“较高的音乐修养”、赵世民之“丰富的音乐体验”就显得十分重要。虽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乐评人对作曲四大件的系统掌握和熟稔运用,但对音乐艺术各门类、各行当基本规律及各自特点的通晓和把握,高层次音乐审美听觉经验的长期积累和体悟之类却断不可缺。假若对音乐创作或表演不做最起码的艺术赏析,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如何能够说得“准”、道得“确”,写得“到位”?阁下“感”从何来?“理”在哪里?“据”何所据?你写出来的文字纵有生花妙笔,充其量不过是一篇拿音乐说事借题发挥的抒情或议论文字,甚或等而下之地成为云山雾罩的隔靴搔痒或徒有其表的绣花枕头,与音乐艺术、与音乐评论实无内在关联,当然算不得是合格的乐评。这也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刘雪枫何以爱乐有40年之久而其“乐评”生涯却仅20年的奥秘。
其次,爱乐、知乐,是合格乐评和乐评人所必备的基础性条件而非优秀乐评和乐评人的充分条件;若使乐评和乐评人的品格、成色达到更高境界,仅止于此尚远远不够。这就牵出乐评人的文史哲功底这个话题。历史意识、哲学修养、审美眼光、文字表达能力之有无、之高下,是判断一个乐评人及其作品成色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特别赞同赵世民倡导之“哲学创造你的深悟,诗歌锻炼你的语言”这一说法,坚持认为非如此便绝难达到施雪钧所言之“深刻”境界;而这种深刻,也绝非莫测高深、故弄玄虚、掉书袋、迂腐气的同义语,而是执著爱乐情结、长期知乐修炼与洋洋史家胸襟、深邃哲学启迪、真切审美感悟和潇洒诗化表达之高度熔铸、化为一体的结晶。endprint
再次,不能否认,乐评当然可以是乐评家个人对于当下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乐坛众生相的品评实感、艺术抒怀或浅吟低唱,可以寄寓乐评人的主体性和个性特色。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乐评之公器担当和道义责任的消弭;恰恰相反,一个时代的乐评,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和当代中国乐坛的乐评,面对种种不正常,不健康的音乐事象,更呼唤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和铜板铁琶,更需要独立寒秋的怒发冲冠和仰天长啸,更期盼敢于直面·惨淡现实的登高一呼和深刻批判。不然,当代中国乐评就得了软骨病,施雪钧的“麻辣”说、邵奇青的“敢为人先,敢讲真话”说、赵世民的“骨骼强劲”说便成了一纸永无兑现之望的空头支票。
我高兴地注意到,本书收录之七位作者及其乐评代表作,尽管各自的专业背景、关注的领域、批评性格、文风才气多有不同,作品的成色也互有短长,但多在广大读者、乐评界同行中建立起较高的公信力和广泛的影响力,成为中国乐评界一支生机勃勃的力量;更为可喜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展露出一个可贵的品格,即:不仅在口头上倡导“乐评人的那根笔直的‘脊梁骨”,而且在其乐评实践中,也不同程度地践行着他们的批评理想、张扬着他们的批评人格、勇气和智慧。因此,当我读到其中一些篇针对某些将乐评当广告写、甘当创制单位或主创者新闻发布会宣传词二传手的乐评人直言不讳的辛辣批评时,当施雪钧对某些名人新作大声说“不”并畅然宣告“不能与人沟通的音乐,只能死亡,别无他路”时,当刘雪枫指名道姓批评谭盾“无论是音乐还是观念,都和任何‘主义扯不上干系!他在音乐方面重绘‘地图式的‘寻根,不过是在用他的小聪明制造‘伪文化而已”时,总是禁不住地灵魂激荡、热血喷涌,总是禁不住地拍案而起,独自大呼“信哉斯言”!
金兆钧援引李白的诗句,称自己的乐评作品为两岸啼不住的“猿声”,将音乐比喻为已过万重山的“轻舟”。窃以为,此比甚为精当。
其实,面对随时代大潮永恒川流不息的音乐轻舟,乐评人和他们的作品,不论“学院派”或“在野派”,也不论两岸发声者是猿啼狮吼、虎啸龙吟、莺歌燕语、狗叫鸡鸣,只要它发声有一定质量,歌唱有较高成色,就都是中国乐评这部庞大交响合唱中的一个声部,各有其价值;因此既不能妄自菲薄,也无权妄自尊大,尤不可互不买账。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之以《中国乐评》为名,无论从时间空间还是从乐评家族广泛性代表性的角度看,似乎都有些大而无当——我如此说,或许是我掉书袋、学究气、迂阔酸腐的老毛病又犯了?
尽管如此,我仍坚持主张:对于当下不甚景气、也不甚健康的中国乐评而言,最重要最迫切的命题是消解“派”藩篱,提高“评”成色,并以此做了这篇序文的标题,在用以自勉之余,亦愿与本书七位作者和中国乐评界其他同行共勉。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