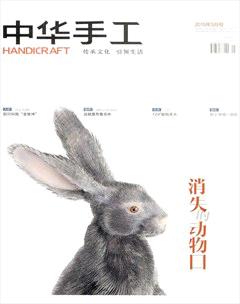别只叫我“金鱼坤”
谢凯
过了今年,郑益坤就80岁了。然而,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仍然待在家里由阳台改建的漆画工作室里,不知疲倦地画着。家里人都劝他好好歇着,他不肯,“画了一辈子漆画,不是想放就放得下的。”
进工作室之前,郑老反复询问:“对大漆过不过敏?别进去后出来变猪头。”在得知没问题后,他才放心地点点头。工作室很狭窄,空气里满是大漆特有的酸味,一张大工作台上摆着好几十块书本大小的金鱼漆板,上面的金鱼各具姿态、栩栩如生。“我打算画100块金鱼漆板,每一块都体现一种金鱼姿态或画法,把毕生画金鱼的经验总结出来,供年轻一辈参考和学习。”
气死猫的鱼
金鱼是郑益坤画得最多,也是画得最好的题材。关于他画的金鱼,有这样一个故事广为流传:有位收藏家收藏了郑益坤创作的一只脱胎鱼缸,缸里画着数条各自悠游的金鱼。由于画得太逼真,惹得家里的小猫天天围着鱼缸团团转,最后竟然因为吃不到鱼缸里的鱼郁郁而终。
“都快把我吹上天啦!”郑老笑着说,“不过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让我思考如何才能把鱼画得更逼真,达到‘气死猫的效果。”在黑色的漆板上画鱼,和在宣纸上画鱼一样,要讲究“只画鱼儿不画水,此中亦自有波涛。”与白宣纸相比,黑漆更容易让人产生“水深不可测”的感觉,因而更适合作为画鱼的背景。不过,漆黑在色谱中是最深、最重的颜色,在上面画金鱼,容易让鱼漂在黑漆上,沉不到“水”里去。
郑益坤说,这也让他反复琢磨了很长一段时间,把福州传统漆画技艺几乎试了个遍,还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我学过十几年西方绘画,对三大面五大调子很熟悉,于是就尝试通过明暗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郑益坤拿起一块画好的金鱼漆板,指着上面的金鱼说:“我把鱼背画得厚一些,有时候还采用堆漆技法来表现鱼背露出水面的样子,再用金箔粉和银箔粉分别对鱼背和两侧的鱼鳞进行晕染,让这些部位看起来鳞光闪闪。有了这样的光感,金鱼的立体感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在罩上透明大漆后,金鱼不仅沉到了水里,而且整个画面也显得很深邃。”
不过,在正式创作金鱼漆画时,郑益坤很少只画一条鱼,通常是几十条金鱼出现在同一画面中。金鱼的数量多了,就要体现画面的深浅层次,不能让所有的金鱼都浮在水面上,也不能都游在水底,而是要分布在水里的不同深度,才能让画面既丰富又饱满。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郑益坤的做法是:先画好最底层的金鱼,罩一层不太透明的推光漆,平磨后再画第二层金鱼,用透明性更好的大漆髹涂,如此一来,上面一层的金鱼就比下面一层的金鱼亮一些,金鱼的深浅层次就产生了。郑益坤还大胆使用了现代合成涂料——聚氨脂漆,因为它的透明度比大漆还高,可以把画面的深度拉得更大,在一个画面中可以同时表现三层、四层深度的金鱼:有的潜在水下,有的浮出水面,还有的若隐若现。郑益坤从墙上取下一幅金鱼漆画让我们数金鱼的条数,大家一致数出是20条,然而按着郑老的指示拿到窗边光线好地方再一数,竟然又多出5条,让人又惊又喜。
因为擅长画金鱼,郑益坤被誉为“金鱼坤”。不过,他并不喜欢这个“雅号”。“金鱼只是我众多漆画题材中的一种,不知道的人听到这个名字还以为我只会画金鱼。” 郑益坤说。
当刺刻遇上白描
在福州画坛,郑益坤崭露头角是国画先于漆画,他曾跟随著名画家陈子奋学习传统绘画,练就了一手出色的白描工夫,所画线条既连贯,又有顿挫,既圆润,又挺劲。在从事漆画创作后,他很自然地将白描的审美趣味融入漆画的线条和造型中。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在他的针刻漆画里。
福州传统漆画本没有“针刻”这一技艺,是郑益坤从汉代漆器上恢复出来的。1973年,郑益坤接到湖南省博物馆的邀请,前往长沙复制马王堆汉墓刚出土的漆器。在这过程中,汉代漆器上极细的花纹让他一直捉摸不透,经过反复推敲,他判断只有缝衣针才能刺刻出来。经由郑益坤的手,针刻这一古老的漆艺技法终于重现人间。
受汉代漆器绘饰的影响,郑益坤也开始创作刺刻花卉,并伴随在自己的漆画创作中。《菊香》,在黑漆背景上,先以针代笔勾勒出一丛菊花,然后在刺划的凹痕里戗入金粉,既格调清雅,又生机勃勃,呈现出与彩漆描绘全然不同的风格。尤其是线条,在顿挫、流畅之外,又似有颤动感,白描的线韵跃然漆上。
在光滑的漆面上如何刺刻?郑益坤把工作室里那幅未完成的《观音坐莲图》摆在工作台上,准备示范。刺刻笔,是郑益坤用刻钢板的刻刀,将其磨成锐利的尖锥做成,像这样的刺刻笔,全是自己制作,十几支,大小不一。在正式创作时,郑益坤一言不发,也叮嘱我们不要说话,只见他拿起笔,时而点,时而勾,时而划,时而转,笔过之后,黑漆板上留下一根根流畅的细线。“刺刻有两大难点,一是下笔要稳,因漆面不易着力,稍不留神线条就会偏离图案应有的轮廓,在不该有刻痕的地方留下不易消除的痕迹;二是要顺,如果心存迟疑,所刻线条必然断断续续,缺少气韵。”放下笔,郑益坤长舒一口气,“所有的线条容不得半点差错,精神稍不集中就可能前功尽弃。”
经过几十年的磨练,虽然如今郑益坤的刺刻艺术已经十分精湛,但他并不满意,“我还想结合版画艺术在针刻技艺方面进一步探索,并把它发展成福州漆艺的一个专门技法。”
“落伍”与创新
在繁忙的创作之余,郑益坤还带了几个徒弟,他们都是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功底好,对漆画也很感兴趣,有的已跟着他学了好几年。对此,郑益坤很满意地说:“我一直认为带徒弟要带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因为徒弟的素质好坏决定了这门手艺未来的发展前景。我不是否定过去手工家庭作坊家族内部传承的做法,而是说在如今这个开放的时代,选择徒弟时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郑益坤有一个来自西安美院的女徒弟,她一面认真学习郑老的传统技法,一面用这些技法描绘出自己创设的画面。例如她创作的漆画《三坊七巷》,将许多自己拍摄的福州老街巷的画面层层堆叠,再通过电脑处理,产生黑白光影效果,深邃神秘的画面让人感觉走入的不是街巷而是历史之中。看到这幅与自己的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郑益坤坦然地说:“这些年轻人的东西我不擅长,我的那些东西落伍啦,现在年轻人都喜欢抽象,有想象空间,该是他们大展才华的时候了。”
虽然郑益坤笑言自己“落伍”,其实他一直在探索全新的漆画技法。漆画《夜巡》,他用了全新的漂漆浸渍法表现海景。“先将漆板置于盛水的池中,把用汽油稀释后的蓝色漆倒入水里,然后轻轻搅拌,牵引水面的色漆,待产生的纹理变化达到理想效果时,再放空池水,漆色纹理自然滞留于漆板之上。”如此一来,所形成的海景生动自然,就像照片一样。
在表现自然形成的溶洞景观时,郑益坤一改传统画法,将各色漆稀释后即兴泼洒在倾斜的漆板上,让漆液自上而下流动,并上下变化倾斜角度,使漆液互相交融,产生“人天参半,妙趣天成”的效果。
“做了60多年漆画,闻惯了漆味,但我仍不敢断言已经深谙漆性。”郑益坤说,正因为漆的不可捉摸,让他像个好奇的孩子一样在漆画这片神奇的天地里不知疲惫地追逐着,“我想,这种追逐必将伴随我的一生。”
——2023湖北漆艺三年展作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