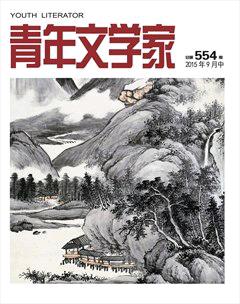萧衍《净业赋》研究
摘 要: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梁武帝“舍道事佛”的信仰背景以及“净业”一词的内涵。其次,分析了《净业赋》序言的主要内容及正文的写作思路,认为《净业赋》是一篇行文思路简单清晰的大赋体作品,但其内容又包含了个人思想怀抱的抒发,具有小赋的精神实质。文中大量引用了佛语进行说理,并辅以一些文采出众的景物描写。《净业赋》中也体现了梁武帝的三教同源的思想,体现了对作为统治手段的佛教的世俗化解读,这不仅是一篇结合自我真实的修行经验来宣传佛理的作品,也是一种宣扬世俗化宗教统治政策的作品。
关键词:梁武帝;净业;赋;三教同源
作者简介:薛茜严(1990-),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外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6-50-03
引言
自东晋佛学兴盛以来,文人学士在所写辞赋中掺入个别有关佛学理念的文字,早在孙绰《游天台山赋》、謝灵运《山居赋》、《闲居赋》就己经出现,但是以佛教用语名篇,并以赋的艺术形式来宣扬佛教学说的,萧衍的《净业赋》是最早的一篇。梁高祖武皇帝萧衍,南北朝时期梁朝政权的建立者,在登基第三年(504)下诏“舍事道法”,皈依佛教,从此便成为了十分虔诚的佛教徒。据柏俊才《梁武帝萧衍考略》考订,《净业赋》大约作于天监十年辛卯(511),梁武帝48岁之时。
[1]“净业”一词最早见于《观无量寿经》,来自释迎牟尼佛与韦提希夫人的对话,佛祖说:“欲生彼国者(指愿生彼西方极乐国的人),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净业。……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2] 第一种福是世间善业;第二种福是出世小乘善业;第三种福是出世大乘善业。这三种福既是三世诸佛的净业正因,可见诸佛的修行不仅修大乘,连小乘、凡夫的善行也是不放弃的。梁武帝以此名篇,既有宣传净业福报、劝人向善的意图,也是一种对自身真实修行体验的展示,更包含了其复杂的佛学思想。
一
《净业赋》正文之前有一个很长的序言[3],主要叙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叙述作者平乱诛奸、平定天下的经历。并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洞察出当时世道艰难、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百姓擦擦,如崩厥角。” 二、交代了作者存有的归老山林的志向。从“少爱山水”到即位后深感心疲力瘁,“欲避位”、“择能者”,以“归志园林,任情草泽”。这些体会预示了作者以后一心向佛的心理基础。 三、提到立志向佛的两个细节:一是“蔬食,不瞰鱼肉”,“自内行,不使外知” ;二是“断房室,不与殡侍同屋而处,四十余年矣”。 四、在厌烦种种俗务之后,悟出思想归向。最后以《礼记》语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并道出了这篇赋的创作缘由,即“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净。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悟,患累无所由生也。乃作《净业赋》云尔。”
正文中首先铺叙了人的各种欲望对于趋向善道的障碍,极力阐述了因果轮回思想,并大量引用佛语,如开头便罗列“六尘”对人心的影响:“观五色之玄黄,玩七宝之陆离,著华丽之窈窕,耽冶容之逶迤。……观耳识之爱声,亦如飞鸟之归林,既流连于丝竹,亦繁会于五音……至如香气馞起,触鼻发识,婉娩追随,氤氲无极……大苦咸酸,莫不甘口,啖食众生,虐及飞走……身之受触,以自安怡,美目清扬,巧笑峨眉,细腰纤手,弱骨丰肌,附身芳洁,触体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识攀缘,乱念无边,靡怀善想,皆起恶筌。”“六尘”指色、声、香、味、触、法等六种境界,是能引起感官与心灵感觉、思惟的对象,因为它们具有污染情识的作用,有如尘埃一般,所以称为“六尘”,与“五欲”(财、色、名、食、睡)一起构成了普通人在日常修行过程中所遇到的第一重魔障。
在阐明了净业障碍的基础上,萧衍又尽力描述了修净业的正确途径, 训导众人欲望由六根六识生起,所以要灭欲,只有清净六根,明心见性,才能脱离苦海。“如是六尘同障善道,……随逐无明,莫非烦恼。轮回火宅,沈溺苦海,长夜执固,终不能改。屯否相随,灾异互起,内怀邪信,外纵淫祀,排虚枉命,蹠实横死。妄生神祐,以招福祉,前轮折轴,后车覆轨,殃国祸家,亡身绝祀。”“无明”也是佛语,为十二因缘之一,意为不信佛法,不能见到世间实相的根本力量,是我们执取和贪嗔的根源。“轮回”即“六道轮回”,佛教认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如不寻求“解脱”,就永远在“六道” (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 中生死相续,无有止息。另有“因果”、“八难”、“贪嗔痴”等佛语穿插其间,使整篇文章显得说理性极强。最后,梁武帝叙述了摆脱轮回,寻求“解脱”的方法,那就是“外清眼境,内净心尘,不染不取,不爱不嗔”,这是要求关闭人的感官,防止“外尘”对“内境”的污染,最终达到“修圣行其不已,信善积而无穷,永劫扬其美名,万代流于清风。岂伏强而称勇,乃道胜而为雄”的目标。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梁武帝不仅有向佛的虔诚之心,而且对修习佛教清净善业的体认也是非常深刻的。
由上观之,《净业赋》的行文逻辑比较简单,基本沿循着举例——分析——结论的思路。值得注意的是,此赋并不是纯粹的说理性文字,在宣讲佛理时也有一些结合描写自然外界风物来写自己宗教体验的文字,如论述外物对人心的影响时,有“若空谷之应声,似游形之有影”之说,在 描述内心清明的境界时有“如玉有润,如竹有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兰之生春……雾露集而珠流,光风动而生芬”的生动比喻。景物描写传神,颇显作者文采,但也存在着佛理宣讲与景物描写结合得比较生硬的弊端。体物与抒情同属于赋体文学的两种功能,《净业赋》是梁武帝根据自己的修行经验写成的赋体文章。汉代大赋流行时期,赋的体物功能被逐渐发挥到极致,东汉中期以后随着抒情小赋的兴盛,赋的抒情功能又逐渐受到重视,并最终反过来占据主导。期间赋体文学的抒情因素日趋强化,魏晋以来,赋家的个体意识逐渐增强。《净业赋》虽然在形式上属于大赋,但其内容属于个人思想怀抱的抒发以及对宇宙人生等根本问题的追问与解答,并结合了作者私人的体验、观念,具有抒情小赋的精神实质。同时,梁武帝把佛事佛理写入赋这一文学表现形式,实是扩大了赋体乃至诗体的题材范围。
二
梁武帝的思想比较驳杂,儒、释、道三家均对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在《会三教诗》中说自己接受三教的过程为:“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4]武帝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弱冠之年当在永明元年(483)。齐高帝建元四年(482)正月开国学时19岁的萧衍入为国子生,此正可以为“弱冠穷六经”做注。武帝的道教信仰来自其家族传统,陈寅格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认为:“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在不避之列,所以然之故虽不能详知,要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王鸣盛因齐梁世系‘之、‘道等字之名,而疑《梁书》、《南史》所载梁室世系倒误,殊不知此类代表宗教信仰之字,父子兄弟皆可取以命名,而不能据以定世次也。”[5]梁武帝在其作于天监三年的《舍道事佛疏文》中也表示曾经“经迟迷慌,耽事老子”[6]。在其《会三教诗》的“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两句中,表达了三教同源的观念,认为三教同源同善,这是梁武帝佛教学说的一个重要创造。任继愈先生认为,梁武帝的三教会通思想应为“三教虽有深浅而均善”[7],笔者同意任先生的观点。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武帝持“三教同归源于佛”[8]的观点。武帝在《敕舍道事佛》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9]这是说佛祖如来和老子、周公、孔子是师徒关系,儒、道二教来源于佛教。他又把最高的佛教比作黑夜里的月亮,把次等的儒教、道教比作众星。三者既有高下区别,又互相烘托,交相辉映。方立天先生认为“ ‘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追根穷源,既无二圣又非三英,佛教是本源,是至圣、是至英,儒、道不是本源,而是佛教的辅助。”[10]
在《净业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梁武帝将儒、释、道三教合并的趋势。例如在论述“解脱”的具体做法时写道:“为善多而岁积,明行动而日新,常与德而相随,恒与道而为邻。”前两句的逻辑类似于《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11],强调对“善”的具体行动和坚持。“与徳相随”、“与道为邻”不仅是对儒、道两家经典术语的借用,也是把修儒、修道当作修佛的重要手段。“修圣行其不已,信善积而无穷,永劫扬其美名,万代流于清风。岂伏强而称勇,乃道胜而为雄。”更是把“扬美名”的儒家理想追求和“道胜为雄”中道家对“道”这一终极实体的肯定共同的当作佛教的终极追求,这之中蕴含着明显的三教同源思想,但是作者并未能在三者之间找到完整的契合点。萧衍只是看到了佛家行善积德、静心养性等旨义与儒家礼教、天人合一观有可以调和的一面,具体应该怎样调和,梁武帝并未找到答案。[12]不但如此,这种三教同源说虽然肯定了佛教的主要地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佛教的误读。佛教追求的是人的“解脱”,小乘佛法以自我的“解脱”为最终目的,大乘佛法则以普度众生为己任,“扬美名”、“流清风”明显是对“我”以及对这个尘世的执着,是世俗而功力的,这与佛教所要达到的目标不仅不一致,而且是背道而驰的。另有“既除客尘,反还自性”一句,似乎也未参透佛法。佛教把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作为真正佛法的三法印,其中的“诸法无我”是指万事万物都是五蕴(色、受、想、行、识)随因缘聚散而成的,都是没有自性的,即是所谓的“空”。而梁武帝却把“自性”的找寻和归还当成修行的目的之一,这明显是错误的。由是观之,梁武帝对佛教的体认似乎只进行到了“诸行无常”的阶段,这对于笃信佛教、钻研佛历多年,并且著作颇丰的梁武帝来说似乎是不应该的。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宗教一旦与政治联姻,那么对宗教的心灵皈依与对宗教的世俗利用就很难分开了,梁武帝的情况便是如此。梁武帝除了致力于佛理的建构外,其真正用力之勤在于对佛教宗教形式的实践上,他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实行家”[13]。其宗教事迹主要有:建佛寺,塑佛像,讲佛经,设法会,受戒,舍身入寺等。[14]梁武帝长年吃斋,并把其推广到所有寺院之中,更曾极力与持无断肉语之僧徒往复论难,作《唱断肉经竟制》,并写了四篇《断酒肉文》[15],以帝王之权威严戒僧人喝酒吃肉,自此形成了中华汉族佛徒特有的斋食传统。皇帝本人皈依佛教、遵守僧人戒律的行为是一个形式指引,它指向的是社会结构的冲破和主流价值观的重新确立。梁武帝是把佛教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利用其统治者的权威,通过对佛教思想的重新解读,如在前人已有的丰富的译经成果上依然组织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如《大品般若经》、《涅槃经》等大乘佛典),树立了与佛教思想融合的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只用从这一层意义上讲,佛教才真正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佛教世俗化的过程。如此,再反观梁武帝写作《净业赋》的初衷,便会发现,这不仅是一篇结合自我净业修行经验来宣传佛理的作品,也是一篇宣扬世俗化宗教统治政策的作品,佛教也从来不可能作为单纯的信仰为帝王所接受。
结论
《净业赋》是一篇行文思路简单清晰的大赋体作品,但其内容又包含了个人思想怀抱的抒发以及对宇宙人生等根本问题的追问与解答,具有小赋的精神实质。文中大量引用了佛语进行说理,并辅以一些文采出众的景物描写,但二者结合的比较生硬。《净业赋》中也体现了梁武帝的三教同源的思想,体现了对作为统治手段的佛教的世俗化解读,这不仅是一篇结合自我真实的修行经验来宣传佛理的作品,也是一种宣扬世俗化宗教统治政策的作品。
注释:
[1]柏俊才《梁武帝萧衍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2]丁宝福《观无量寿经笺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
[3]严可均辑《全梁文》卷一,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页。
[4]道宣《广弘明集》卷30,《大正藏》第52册,第352页。
[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
[6]严可均辑《全梁文》卷六,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1页。
[7]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7页。
[8]李晓虹《从“三教同源”看梁武帝之政治理念》,《普门学报》2007年第42期,第1-10页。
[9]严可均辑《全梁文》卷四,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1页。
[10]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6页。
[11]张燕婴译注《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页。
[12]于英丽《梁武帝萧衍思想与其赋之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49-52頁。[13]详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3页。
[14]详见陈伟娜《梁武帝萧衍的佛学思想及宗教实行》,《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52-54页。
[15]严可均辑《全梁文》卷七,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2页。
参考文献:
[1]柏俊才《梁武帝萧衍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丁宝福《观无量寿经笺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严可均辑《全梁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
[5]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版。
[7]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
[8]于英丽《梁武帝萧衍思想与其赋之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49-52页。
[9]陈伟娜《梁武帝萧衍的佛学思想及宗教实行》,《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52-54页。
[10]李晓虹《从“三教同源”看梁武帝之政治理念》,《普门学报》2007年第42期,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