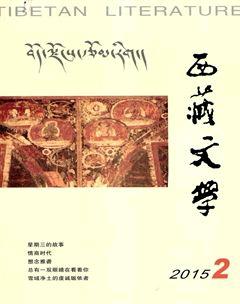埙缘(外一篇)
子嫣
埙,这种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乐器,近些年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活力,在三秦大地上尤其活跃着。走在古城西安的大街小巷中,你的耳膜常常会在不经意间被一种沉静的音韵不轻不重地击中,这声音温和得让人无意识去防范,又沉稳得令人不能忽视,它,就是埙的声音了。
造型简约质朴的埙,其声音却有着极强的穿透力,它似乎是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带着岁月的沧桑、艰涩,却不改步履的坚定,走得不急不徐、不慌不忙;穿越唐砖汉瓦的深沉厚重,却保持着清新的生命活力,走得从从容容、自在悠然。这份悠然从容,大概源于它有明确的目标吧?我认为,埙乐的目标只有一个——直达人心!的确,埙只想抵达生命的最深处,目的,则是激活生命原始的鲜活力量。
埙乐初一入耳,感觉到它如泣如诉,仿佛蕴涵着无尽的苍茫与哀伤,如同挟裹着重重的尘埃与迷雾,然而,不急,由耳到心时,它会抖落掉层层纷繁与喧嚣,只把一份悠远的宁静带给你。静静听下去,埙乐带给你的,必是清新如莲、清净如竹、清凉如月的,不管你懂不懂音律,都会由衷地感觉到,那悠悠扬扬、缠缠绵绵、温温和和的音韵,与你的心的律动,是那般熨贴,那般契合。
初闻埙这一器乐之名,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春天,从大作家贾平凹老师的文中看到,那时只是隐约感觉到这种器乐所蕴涵的静幽渺远,以其时年少轻狂的心是难与之合拍的,看过也就放下了。后来每去书院门游玩时,总能见到密密匝匝摆在货架上的埙,那古朴中含几分稚拙的造型形态,让人总忍不住想拿在手里把玩一番,不过,也仅此而已。
岁月匆匆,时光荏冉,转眼二十年过去了,于癸巳年三月,天地间春光明媚、人间正花红柳绿时,被偶然的机缘引领着,我随朋友来到了终南山下一个宁静美好的地方,毫无征兆地,在这里与古老神秘的器乐再度邂逅。这一次的相会,可谓因缘和合,心似乎早做足了准备,来赴这一场约会,只是我不自知罢了。简约质朴的埙,以它粗浅无雕饰的天籁之音,瞬间便毫无障碍地扑进与它同质地的心田里,相融相合,再也不用分开。埙韵,与我的心语,竟是琴瑟和鸣,相应相和。如莲从污泥中过滤出纯净、绽放出圣洁;如竹从风雨中荡涤出清新、展露出风骨;如月从黑暗中净化出光明、铺展出光华,二者如此合拍、如此默契,宁静而悠远,似乎从无始处来,向无终处去,从不张望,永不回头……
说来也巧,与埙的二次相逢结缘,恰是藉由一个跟贾先生颇有几分神似的人——吹埙人秦实先生。初识秦实先生时,感觉他具备关中男人特有的气质——秦岭山的气质,可算秦人的典型代表。再听他忘情而投入地吹奏埙曲时,不禁被那完美和谐的情景所感染,不由惊叹:埙器、曲乐、吹埙人,竟是如此默契相融!人和人的相知是精神相通,人和物之间又何尝不是啊!没有精神上的高度相通,怎能演绎出相同的高远气质来?怎能诠释出和谐的悠久神韵?在这一刻,已非仅仅人在演奏器乐,而是三者互动中,人、器与乐,既相互诠释、不分彼此,又各自为一、独立完整。说秦实先生内藏着埙的坚韧浑厚精神,或者说古埙含有秦实先生的沉静内敛气质,应该都是一个意思吧?
古埙演奏家秦实先生,与埙显然是有不解之缘的,他们似乎一起穿越过了历史的久远与厚重。而我与埙的结缘,在看得见的此生却走了二十年之久。拙朴可爱的埙,似乎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等待我历经沧桑,等待我沉淀清澈,等待我安静地走近,然后以它纯净宽广的胸怀,瞬间便完全地接纳了我、包容了我,让迷茫的心灵沐浴在天籁之音中,安住于微风拂莲般的熨贴的抚慰中。这,就是缘分的奇妙之处,它让两种气质相同的东西,在正当合适的时候,刚好得以相遇相识。
古老的埙,与久远岁月之后的我们,有着怎样绵延悠长的缘分呢?
抱朴归真 讷中生花
——从[墨界·色界]书法展观王江其人其字
王江是一文友的朋友,无意中听友多次说起过,大概知道他是个有成就的书法家,便也好似熟识了一般。实则心知,我熟悉的只是人名。真正走近他的书法艺术,得以用自己的眼去了解和感知他的艺术世界,是在甲午夏月亮宝楼的书法展上。展览消息传来时,“墨界·色界”几个字以及字眼后面隐含的意蕴让人眼前一亮。
循着熟悉的人名和颇具新意的展览名号前往亮宝楼观展,本也是持一颗平常心。但你走进展厅,却是不寻常的发现,一不小心,你的心被打动了。循着一幅幅作品走过,慢慢地,心情不再平静,欣欣然地看了一遍又一遍,越看越有味道,离开后仍念念不忘,回味无穷。你仿佛从这墨界色界里,读到了法界朦胧诸相,更感受到了生动真实之心界。
墨本是古墨,字自是亘古,艺当然承古,而一应古老元素成就的产物,却非但没有古旧之气,反而有一股真实的清新。这清新气息,非生于奇异时尚,而恰源于他对书法艺术之纯正质朴特质的坚守,全没有哗众取宠的时弊流俗习气。王江的字,不同于以往看过的所有书展,似乎少了些龙飞凤舞的潇洒,少了风花雪月的绮丽,少了云遮雾罩的迷蒙玄奥,或者也寻不到你所喜欢的清逸,并不符合你惯常的审美习惯。但你看着这些字,却就是不想移开目光,那一个个透着几分稚与拙的字体,仿佛带着温度、藏着厚度,一点点地暖着你、托着你,在你心头滋生出一种贴心的踏实。再看下去,几十副作品,大张小幅皆风格一统,主文、落款、印章,点、线、面,均是一以贯之的态度,一以贯之的气韵,一以贯之的质朴本真。没有一处虚浮应付,没有一处跳跃翘脚,形与神内外一统,意与韵和谐自然。各种形制的作品,由内而外莫不透着一种沉稳的庄重、扎实的虔诚。你被这无形的气场吸引着,浸淫其中,流连忘返。透过这认真的拙相,最后,你不仅读出了大巧,读出了刚毅,读出了秀,读出了美,而且读出了艺术大家的精神和境界,不觉间对眼前的艺术作品已肃然起敬,对书者也油然而生钦佩。
此时,你大概知道了,为何你的目光不能随便从它移开,尽管一开始它并不是你所喜欢的那一类书法形式。吸引你的,是艺术的真。而打动你的,则是创作者的诚。是的,王江的艺术风格是抱朴归真,他用真诚表现着真美,用真诚感召着真诚。从中你分明感受到了书者的精神特质,他在墨色世界里毫不掩饰地描绘着他的心界。
及至见到王江先生,还是有点意外。虽然都说“字是心的画”、“字相即心相”,但也绝想不到,他的人和他的字竟是这般统一!不惑之年的他,面目上尚保持着几分学生的纯真意气,神情乃是未被世俗雕琢的平实淳朴,且藏着一丝腼腆。言语简而短,目光于宁静中透着睿智和刚毅。这一切现象传递给你的信息,是敦厚与真诚,更有倔强与坚韧。我想,王江先生大概把所有的热情、个性和思想都用于对书法艺术的执着追求上了,留给世俗生活的,便只剩下这有几分清冷的朴实与谦逊。而他的艺术造诣,则深深地隐藏于平实的表相下,任谁一时半会儿也是读不透的。用大智若愚的心,书大巧若拙的字,这样说王江先生,大概是贴切的罢。
见过创作者本人,再回过头看他的字,似乎读到了更多的内容。从他的书法作品中,能看到他治学的严谨认真,和对艺术的孜孜以求、刻苦耐劳精神。在他精心准备的展品中,有一组作品共十二幅,分别录着不同年代的十一位诗人所写的同一标题的古诗词——《忆长安》,从正月一直排到十二月,完整而有序。十二首诗词时节不同、内容各异,用来表现它们的书体形式,也随之而巧妙变化、适宜应和。姑且不论创作者书法技艺的精湛擅变,也不论他搜集整理十二首诗词时的良苦用心,单就这一构思的精巧别致,就足以令人耳目一新,而心悦诚服!
丰富的落款,是王江书法作品的另一大特色。这些落款,不仅是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阐释着主文,而且如同作品的色与声,有效地整合和强化着作品的内蕴光芒。如他录的《贾岛诗·净业寺与前雩县李廓少府同宿》,落款写着,“古净业寺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沣峪口,隐於终南山之中。白居易曾修佛于此。有物为证。”;《唐·王维·终南别业》作品的落款是:“王维与孟浩然、韦应物诗风皆颇类晋之陶渊明,以山水田园之气息,视人隐逸遁世之心境,极真文人也。”接着录的《王维·桃源行》落款“此诗以晋陶渊明桃花源记而改之,意言此二人性情相近也”,此说进一步论证了上面的观点。通过这些作品,不仅其严谨认真的为学作风可见一斑,其丰厚的学识修养也略现端倪。
展品中最清新的,是一组对古老瓦当的书写和诠释。这组作品约有十幅。每一幅从对瓦当的原形的摹写,到字体的精当评论,及意境的深刻阐释,乃至历史背景的详尽说明,构成了一种新颖而又完美无缺的艺术表现形式。这怕也是最能体现他深厚的艺术造诣的作品之一吧。这组作品以及他的所有丰富落款所蕴含的内容,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书法技艺的范畴,而分明是一个文化学者的专业研究视角,支撑它的,是精以求精的严谨治学精神。
从以上气象万千的展品中,你知道了,书法艺术中,并非只有单调寂静的水墨,还含着亮丽的色彩和光华,更蕴着大千世界、自然万象之丰富音声。这一独特又丰盈的艺术气韵,单靠书写匠之艺技雕工,自然是不能成就的。王江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精神特色,早已下足了书法笔墨之外的功夫,从深厚的古传统文化和天地自然中,不断汲取着养分,丰满着笔端的墨界色界,同时,也颐养着自己的心界。书者的心灵世界反映在作品中,作品也便带了个性,有了思想,含着温度,着着色彩,而打动人、感染人的,也正是这个。
刚毅和木讷,应该是王江先生最显著的标志。观其人,眼神中透着刚毅,神情中有木讷;观其字,表象是稚拙,内在却透着风骨精神。刚毅木讷似乎是他的性格特色,而成就他的,也正是这一特色。天性的木讷,为他屏蔽了现代社会的喧嚣浮华,刚毅则使他能坚持本色、安于寂寞,固守一份真纯,直到,从灰暗中绽放出绚丽。
有人说,一辈子并不长,只够好好爱一个人,只够认真做好一件事。一生未取得成就者,大多不是因为笨,而是耽于聪明。书家王江恰恰避开了这无用的聪明,由木讷而扎根,凭刚毅来培育,直到长成一棵大树,广博的学识和饱满的思想,是大树丰茂的枝枝叶叶,而书法艺术,是大树开出的艳美花儿。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此一论或也正适合于王江先生。他的字相和心相,的确氤氲着温和仁厚之气。于稚拙中寄寓着真淳,于平淡中蕴藏着深刻。那是天地的大爱,是自然的气度,来自大千世界,再回归于大千世界。
“从心所欲不逾矩”本是孔夫子就做人境界的最高论,我以为,借以形容王江的艺术创作之境界,或也正合适。真正的艺术创作,最怕墨守成规、拘泥古旧,忌讳复制。而要形成自己独立的符号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又必得循着古圣先贤的路径,一步步扎扎实实地走过,源古才能承新。所谓创新,并非为了立异,却是为了更接近本真,接近道。显然,近三十年的学养历程,他早已夯实了基础,厚积而薄发,如今已是笔意通达自如,心界淳厚圆融,正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
而王江才四十岁出头,这正是艺术家的开花时节,可以说,属于他的艺术黄金期才刚刚开始。展望未来,看他在浩瀚的书法艺术园中独树一帜,真正有所建树,成就一番大事业大境界,发出独特而耀眼的光芒,当是完全可期的。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