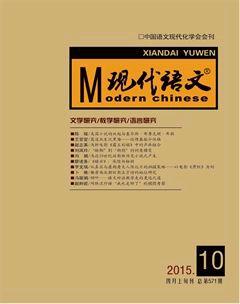动画电影《千与千寻》的叙事艺术
摘 要:电影叙事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优秀的叙事是电影成功的基石。《千与千寻》是日本著名动画大师宫崎骏众多作品中的代表作,在传统的电影叙事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创新元素,从故事情节到色彩线条,以其独特的叙事模式、叙事方式成为动画电影叙事艺术的典型,达到了形式美和内容美的高度统一。本文从电影叙事的角度出发,探析《千与千寻》的叙事艺术。
关键词:宫崎骏 千与千寻 叙事艺术
宫崎骏是日本现当代最著名的动画电影大师,是日本动画界的一个传奇,也是第一位将动画上升到人文高度的思想者,其动画电影作品之一《千与千寻》在2001年上映,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该影片都达到了宫崎骏动画和同时期日本动画电影的巅峰,获得柏林金熊奖和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受到广泛赞誉,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是“堪与迪斯尼遥遥相望的世界动画另一高峰”[1]。一时间,以日本为中心,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持久不息的“千寻热”,其艺术成就和影响可见一斑。本文将从该动画电影的叙事入手,分析本电影在叙事方面的独到之处,探索宫崎骏动画电影的成功因素。
一、叙事结构模式:在戏剧式线性结构中推陈出新
关于电影的叙述结构模式,电影理论中并没有统一的固定分类,不同学者对电影叙述结构模式有着不同的分类方法。宋家玲编著的《影视叙事学》一书中将戏剧式线性结构纳为电影叙事结构之一。
戏剧结构强调矛盾冲突,跌宕起伏;线性结构注重连贯统一,环环相扣。戏剧式线性结构,一般会利用一个矛盾作为情节设定和叙事背景,通过明确的开端、合适的情节发展指向合目的的结尾。整个情节有一个决定性的因果律。[2]创作者从一开始,就需要使故事情节的变化发展合乎戏剧逻辑地指向那一个既定的终点。
(一)层层递进的戏剧冲突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
宫崎骏动画电影的叙事模式比较简明,大多符合戏剧式线性结构和散文式线性结构的特点,而《千与千寻》则正好符合戏剧式线性的叙事结构模式,但它的成功却不是因为选择了戏剧式线性的叙事结构,而是因为它在安排结构、发挥叙事优势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叙事元素,使故事在符合逻辑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多彩、扣人心弦,大大增强了故事性和可观赏性。
在《千与千寻》中,贯穿整个故事的最大冲突就是千寻如何拯救变成猪的父母。在故事开头,千寻和父母无意间闯入了神明的世界,父母因为贪吃和不守规矩中了魔法并变成了猪。千寻在遭此变故后只能与掌管神界的汤婆婆签订劳动合同,为拯救父母而忍辱负重,与汤婆婆斗智斗勇。伴随着这个主要矛盾,各种次要矛盾纷至沓来,层层相叠,节奏分明。在拯救父母的过程中,无脸男对千寻畸形的喜爱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白龙偷取钱婆婆的魔法印章并被惩罚、千寻帮助河神洗清身上污垢并得到报答……这多组矛盾看似与千寻救出父母这个主要矛盾无过多的联系,但正因为经历了这些小事件,千寻才得以从身心成长起来,为千寻最终得以救出父母埋下了伏笔。
《千与千寻》这种叙述艺术的特点,集中蕴含了影片戏剧传统的艺术张力,客观上产生了极具吸引力的艺术魅力,具有扣人心弦的强烈悬念,这也许是宫崎骏动画电影成功的重要因素。
(二)多个小闭合结构构成连贯统一的情节线
动画电影为了增强自身的艺术魅力,它的故事情节既要符合生活逻辑、性格逻辑和情感逻辑,又要具有内在的连贯统一性,以建构完整的艺术整体。宫崎骏的《千与千寻》就做到了这一点。
闭合,其基本意义是“首尾相连的,封闭的”。顾名思义,闭合结构,就是首尾相连的环形结构。电影叙事中,出现的情节和人物带着悬念出场,最终有一个明确的交代和归宿,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圆”并回到原点。《千与千寻》是以千寻在神境的经历为情节线的,整个故事按时间线索的顺序展开,而整个故事线的走向就是从提出问题到解答问题的过程。在《千与千寻》中,对于最主要的问题:千寻是否能够救出父母,电影并未根据人物设定给出直接的回答,而是通过娓娓道来的方式,将充满童趣的幻想和对人类自身价值的思考用个人成长印记的线贯穿起来。[3]简单的悬念其实富有更深层的哲学追问:人类能否找回迷失的自己?人类能否拯救自己?影片在简单的故事中给出了耐人寻味的回答。千寻先帮小白龙找回了本名和记忆,后帮助无脸男褪去了欲望和丑恶的枷锁,又带领汤婆婆的大宝宝走出了宠溺的襁褓……叙事主体一直在向前发展,而这些有开始有结束、交代完整的小闭合结构将千寻救父母的过程填充起来,构成了“双向发展”。它们既交代了故事中出现的次要人物的结局和命运,同时作为论据,从侧面证明千寻在成长,她最终救出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最终将情节统一起来并连成完整的故事脉络。
中国古代小说、评书、相声、曲艺等等非常喜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方法,意思是说:要讲述两件以上的事情,先来叙述其中之一。《千与千寻》运用多个小闭合结构,构成连贯统一的情节线,很类似中国古代“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艺术韵味,显得作品愈加具有艺术性和完满性。
(三)充满悬念的结局
在叙事作品中,故事结局充满悬念,这是叙述艺术作品创作非常重要的艺术规律。宫崎骏在《千与千寻》中做到了这一点:影片结局悬念重重,耐人寻味。
《千与千寻》在故事结尾,千寻和小白龙、大宝宝一起从钱婆婆处返回,并根据神界规则撤消了自己在汤屋的劳动合同,并救出了父母,一同返回了人间。至此,《千与千寻》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圆满的故事,但在结尾部分,千寻返回人间之前与小白龙的对话却又给整个电影留下了一个悬念:
小白龙:“千寻照原来的路走回去就可以了,但是绝对不能回头看。”
千寻:“白龙呢?白龙的将来怎么办?”
小白龙:“我会跟汤婆婆商量,不再做她的弟子了,不要紧的,我已经找回自己的名字了,会回到原来的世界的。”
千寻:“我们还会在那里相逢吗?”
小白龙:“嗯!一定会!”
千寻:“一定哦!”
小白龙:“一定!”
小白龙和千寻的这一段对话给观众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可以说就千寻与父母在神界的纠缠已经有了交代,告一段落,但千寻的人生和小白龙的人生都是新的开始。如此肯定的回答,让观众好奇两人能否再次相遇?在哪里?以怎样的方式?故事在结尾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让观众产生了新的期待。其实,两人的相遇与否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自己心中的感受。如果观众观影结束感受到了希望,那么千寻和小白龙就一定会重逢,至于时间、地点、方式则是“一千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了,这便是宫崎骏在《千与千寻》中的创新之处和点睛之笔。
二、叙事方式:非限制性叙述与限制性叙述的灵活运用
故事的叙事流程是靠叙述者以一定的角度呈现出来的,宫崎骏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以独特的风格在世界动画电影界独领风骚,除了其利用独特的叙事结构表现内容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巧妙地利用了动画电影的叙述视点。视点决定了故事叙述的层次与焦点,而对层次与焦点的把握是通过非限制性叙述与限制性叙述两种不同方式来实现的。非限制性叙述可以给观众以全知的视点,多方位、多角度去了解故事中各方的发展动向;而限制性叙述则易于设置悬念,“叙事可以通过控制不是内容的信息范围而达到强有力的效果”[4],《千与千寻》中得体的视角把握与恰到好处的视角切换使其在叙事艺术中独树一帜,成为视角助力叙事的典范。
(一)以限制性视角统领故事
叙述视角是电影展开叙事的索引,也是观众在对作品进行接受和审美的切入点之一。正确把握叙事视角的使用方法和切换时机,可以为影片起到“开源节流”的作用,即呈现已知,屏蔽未知。在《千与千寻》的故事中,观众的主观意念承载于主人公千寻的形象中,宫崎骏将千寻的个人成长经历和奇遇用日记一样的叙述方式向观众展现出来。
在影片开头,千寻亲眼见到自己的父母变成猪,这么突然的变故,观众和千寻一样不明所以。之后小白龙的出现并无条件地帮助千寻,观众和千寻同样迷惑。小白龙为何突然出现又出手相救?无脸男为何对千寻表示好感?神明也会泡汤洗浴?在这个不熟悉的地方为什么要不停地劳动?因为限制性视角,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主人公同化,以所知道的不多于主人公的信息量寻找自身审美的兴趣点以及渲染影片的神秘感。宫崎骏以限制性视角使观众跟随主人公的视线来了解整个故事的发展,体会角色的遭遇、心理和成长变化。它一方面有效地封闭了观众所得到的信息,放大悬念的效果,另一方面又让片中角色揭开谜底,就好比观众自己窥探到了神秘世界的本身,更增强了故事的可信性,让观众在夸张的电影幻象中得到真切的情感体验。
(二)以短小的非限制性视角丰富故事
《千与千寻》的独特之处在于并不是以一种叙事方式贯穿全局,而是适当地在影片中运用其他叙事方式,调节情节和故事发展的效果。
无脸男与千寻的相遇使整个电影中仅有的两次非限制性视角出现了一个:在千寻忙着寻找受伤的小白龙时,无脸男大闹汤屋,此时观众的视角从主人公千寻身上分离,变成了全知视角,一方面知道千寻和小白龙的危险境况,另一方面又知道无脸男因为见不到千寻而让汤屋陷入一种混乱。这时非限制性视角的运用给观众带来了一种焦急的心理,两个矛盾同样重要,千寻又何去何从?给故事的发展设置了新的悬念。而另一处非限制性视角的运用是在千寻独自一人踏上了前去找钱婆婆的不归路,此时,视点再次从千寻身上转移,镜头切换到锅炉爷爷的火炉室,小白龙因为吃了河神赠给千寻的丸子苏醒过来,后找到汤婆婆进行谈判,告诉她大宝宝被钱婆婆掉包的事实,并以自己带回大宝宝作为放走千寻一家的交换条件。此时的全知视角为结尾千寻和父母能够平安离开神界做了交代和铺垫:千寻之所以有机会救出父母是小白龙和汤婆婆做了利益交换,而这是千寻自己所不知道的信息。这样在故事中插入短小的非限制性视角的方式,客观上并不会削弱故事悬念带来的心理预期,反而留给观众一条线索,促使观众做出自己的预测和判断,这样恰恰有利于增强艺术悬念。
《千与千寻》中宫崎骏灵活运用了限制性叙述与非限制性叙述有机结合的方法,以主角的经历控制整个故事流程,但在完成情节铺垫和人物性格塑造的任务时,适当屏蔽信息,使观众加深对主角命运的担忧和期待,反而加强了故事悬念的强度,避免了主角口头评述的呆板和主观,使故事主要依靠客观的画面讲述而显得更加真实。[5]
三、结语
宫崎骏在《千与千寻》的创意中,从叙事结构模式、叙事方式插入了自己的创新点,并灵活地运用和融汇多种电影叙事手法,通过营造“放得开,又收得拢”的大开大合式的完整结构,既注重叙述模式的完整与完满,又具有开放性的艺术张力,能够通过激发观众的高度想象,在给观众带来强烈视觉冲击的同时,给观众以惊奇的审美愉悦。
注释:
[1][5]杨晓林:《动画大师宫崎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第145页。
[2]陈奇佳:《日本动漫艺术概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
[3]杨晓林:《动画大师宫崎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4]彭吉象等译,[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著:《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于小玥 山东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6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