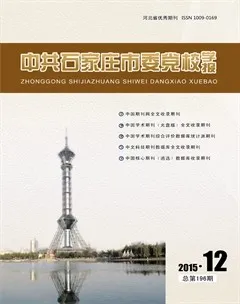国外大城市空间扩展方式的实践探索
[摘要]“大城市病”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各国为治理“大城市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艰难探索。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大城市在今后的发展中,要改变目前的单中心单向集聚的倾向,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角度进行科学规划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将大城市的部分要素和功能向周边地区疏解。城镇化要以都市圈、大都市区、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从而使大城市的空间结构由单中心空间结构向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化,这是保持大城市的活力,增强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区域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根本路径。
[关键词]大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国际经验
[中图分类号] F061.5 " " " " " " " [文献标识码] A " " " " " " " " " "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5)12-0018-05
大城市借助良好的区位优势、行政资源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备、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以及较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吸引着各种要素的集聚,在推动各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及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增强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竞争力方面,均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大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毫无例外的遇到了交通拥堵、地价高昂、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对于如何防治“大城市病”,中外学者从不同领域和视角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见仁见智,提出了很多极有见地的观点,世界各国也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艰难探索。本文拟从空间扩展方式的视角对世界各国大城市的实践探索进行总结。
一、东京:从“一极集中”到“多心多核”的城市复合体
东京位于日本的关东平原地带、东京湾西北部,在明治维新前被称为“江户”,始建于1457年,是德川幕府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德川幕府为加强对各地“大名”的监控,实行“参觐交代”制度,江户诸侯云集,人口增长迅速,至19世纪末,已成为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之一。1868年,日本开始了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导致幕府政治的垮台,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大的改革,开启了日本追赶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同年,日本皇室由京都迁都江户并将其改名为“东京”。[1]20[2]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而东京作为日本首都的优势是其它城市无可比拟的,大量的金融资本、企业、人口快速向东京集聚,东京湾附近建设起大量的钢铁、军工、纺织等企业,东京在原来政治中心的基础上迅速发展成为日本的工业中心之一。虽然东京在二战中遭到严重的破坏,人口急剧下降为战前的一半,只有278万,但随着战后重建和经济的逐渐恢复,东京人口快速增加,城市空间规模也不断扩大。东京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限制增长阶段
在1946年的《东京城市震灾复兴规划》中,提出要将东京人口控制在350万以内,但这一限制很快即被突破。为控制人口的过快流入,1958年,参照大伦敦1944年的规划,日本政府制定了《第一次首都圈建设规划》,将城市中心10-15km范围内的区域作为城市建成区,将建成区外围8-10km范围内的地域设置为城市“绿带”,以“绿带”为界防止城市的无限蔓延扩张。在“绿带”外建设新的工业城,形成圈层空间结构。但由于私人土地所有者不愿放弃地价上涨带来的巨额收益,这一做法遭到他们的抵制,在实践中并未真正发挥作用,城市建城区面积反而加速增长,至1960年达到了341km2,1965年达到了493km2。[1]21
(二)“一极集中”阶段
反思第一次规划控制实效的原因,《第二次首都圈建设规划》(1968年编制)调整了思路,肯定了东京为全国经济快速增长中枢的地位,将原来的“绿带”改为“近郊整备地带”,即城市有序开发的预留空间,要求在开发中保留足够多的绿地,同时提出了建设地域范围包括“一都七县”(一都即东京都,七县即神奈川、千叶、琦玉、群马、茨城、山梨、枥木)的东京都市圈的构想,拟通过铁路和公路的建设将各城市连接起来,向周边城市疏解东京的部分功能,以减轻东京压力。虽然此后都市圈内建设了大量连接各城市的交通设施,但由于东京的吸引力过于强大,第二次规划的目的并未顺利实现,各种要素向都市圈核心东京“一极集中”的特征更加显著,东京市建城区的面积在1970年已增加到877km2,且建城区表现出沿交通线蔓延的趋势。[1]21-22
(三)“多心多核”发展阶段
针对大城市与周边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在1976年由日本国土综合开发厅主导编制的《第三次首都圈建设规划》中重点强调均衡发展原则,提出了在都市圈内发展多个相对独立、各有分工的核心城市,建设具有“分散型网络结构”的城市复合体的构想,以此分担东京的职能。在都市圈的第五次规划中更加突出了次中心城市的地位,同时强调各个城市的自立以及城市间的分工合作与功能上的互补。“分散型多心多核”模式对于均衡布局区域内的产业与人口,促进都市圈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增强东京都市圈的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1]22
不仅如此,在规划引导、发达的交通体系的支撑、不同城市间的竞争、合作机制等共同推动下,日本的三大都市圈东京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大阪都市圈(近畿都市圈)联合构成了竞争力更加强大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二、巴黎:从单中心集聚到平衡发展的城镇体系
巴黎地处法国北部,塞纳河从城市中心穿过,作为法国的首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巴黎市仅包括原巴黎城墙内的20个区,而巴黎大区(巴黎都市圈)则包含巴黎市、上塞纳、瓦勒德马恩、塞纳-圣但尼、伊夫林、瓦勒德瓦兹、塞纳-马恩和埃松7省,面积12072km2,人口1149万。
处于防卫的需要,巴黎最早是在塞纳河中的一个城岛上修建并发展起来的,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虽历经波折,但城市空间基本上是以城岛为中心沿塞纳河两岸向外不断延伸[3]。19世纪末,法国的工业化加速推进,工业企业和独立住宅建设在巴黎近郊无序蔓延。为加强对巴黎及周边地区城市建设的统一规划和管理,法国政府于1932年颁布法律,突破行政区划的局限,设立巴黎地区。1934年,PROST规划发布,主要内容是:为适应汽车交通的需求,对路网结构进行调整,放射路和环状路相结合。自巴黎中心延伸出的五条主干道从不同方向辐射,联系法国及欧洲其它重要城市;对森林公园等空地、重要历史景观地段实行严格的保护措施;将巴黎以外的各市镇的土地划分为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既遏制了城市的无序扩张,同时也为日后的城市发展保留了大量空间[4]。
二战后,经过十多年的时间,法国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巴黎地区城市建设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区域内不同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为此,法国于1955年设立了巴黎大区(即巴黎大都市圈)计划区[5]35,并于1956年颁布了《巴黎地区国土开发计划》(简称PARP规划),该规划提出:降低巴黎中心区的密度,提高郊区的密度,使产业和人口等要素在地区内均衡分布,以缩小不同地域发展差距;疏散不适合在中心城区发展的工业以及过于密集的人口;在近郊进行大型住宅区建设,并沿城市边缘建设卫星城。在实践过程中,这些住宅区和卫星城的建设大都在现状城市建成区内进行,以尽可能减少新增建设用地[4]。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巴黎的空间形态表现为以市区为中心呈同心圆圈层结构向外扩展的特征,这种结构导致巴黎中心区的产业和人口过度集中和拥挤。[5]351960年编制的《巴黎地区区域开发与空间组织计划》(简称PADOG规划)在疏解中心城区的产业和人口、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方面继续推进,提出:借工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或转产之机将第二产业向郊区疏散;在区域内改造、新建若干个发展极核,以形成多中心空间格局;通过促进巴黎周边城市的发展或新建卫星城镇提高农村地区活力[4]。
1965年发布的《巴黎地区国土开发与城市规划指导纲要1965~2000》(简称SDAURP规划)提出:沿地区内已自发形成的城市发展轴线优先布局产业和人口;在城市建成区内及快速城市化地区积极培育多功能城市中心,以便使整个区域形成多中心空间格局;以公路、铁路、RER等交通线路引导城市空间扩展方向;在塞纳、马恩和卢瓦兹河谷划定了两条几乎平行的城市优先发展轴线,沿发展轴线设立8座新城作为重点开发的新的城市中心。与以往历次规划相比,该规划顺应了区域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从区域整体均衡发展的高度对巴黎地区的城市空间结构进行架构,对促进巴黎都市圈的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4]。虽然此后在1976年和1994年的规划中将拟建新城的数量由8个调整为5个,但构建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思路和原则都得到了继续贯彻[5]35。1994年的《巴黎大区总体规划》根据新形势要求,认为城市之间应保持合理的竞争;要保持各大区之间以及大区内各中心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规划对大区内的建设空间、农业空间、自然空间进行了划分,要求统筹兼顾,以实现区域协调、均衡发展[6]。
新城建设的主要原则是:必须在新城布局工业和其它产业以吸纳劳动力就业,同时要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通过对半城市化地区现有旧城的改扩建形成新城;在交通干线的重要节点上选址建设新城。新城在巴黎四郊均匀布局,除东郊的玛尔纳(距巴黎市中心15公里)外,其它4座新城与巴黎市中心的距离在25-35km之间,规划人口15-30万,将新城作为一个区域性中心来培育[7]。
在20世纪下半叶,巴黎将近郊的发展重点放在德方斯、圣德纳、博尔加、博比尼、罗矗尼、凡尔赛、弗利泽、伦吉和克雷特伊9个副中心,在这些副中心建成了很多工业园区。远郊发展的重点是色尔基、马恩拉瓦莱、圣冈代、埃夫里、默龙色纳5座新城。新城建设改变了过去作为“住宅区”和“工业园”的思路,注重增加各种就业机会,配备完善的生活、文化、娱乐设施,以便让新城居民能够与巴黎居民一样享有同等的生活水平。在1975年到1984年的9年间,巴黎大区的新增人口中新城占比达47%,实现了重新布局巴黎大区产业和人口、吸引地区新增就业人口向新城集聚、提升区域总体竞争力的目的[5]35。
为了保证巴黎城市空间的合理扩展及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政府制定了很多控制市区发展规模、促进资本、企业和人口向郊区扩散的法规和政策。1955年,巴黎停止了对市区新上工业项目的审批,同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政府部门往郊区市镇迁移。1958年,政府作出规定,凡在市区内的工业企业,无论是改建还是扩建,其占地面积均不得超过原有面积的10%。自20世纪60年代始,巴黎对市内的企业开始征收“拥挤税”,占地500m2以上的工厂若由市内迁出,政府给予60%的拆迁补偿,由市区迁出的各类机构则可获得15%-20%的投资津贴。对远郊新建城市给予优先发展经济、工商企业的政策,适度放宽土地开发限制。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促进了副中心和新城的发展,使巴黎最终形成了“市中心-副中心-卫星城-平衡发展的城镇体系”的空间格局[5]35。
此外,巴黎借助发达的高速铁路和航线与世界其它城市保持密切联系,发挥“文化之都”的魅力和辐射力,对于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的形成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伦敦:以新城建设为突破口,形成不同等级城镇协调发展的圈层结构
伦敦位于英格兰东南部平原地带,近临泰晤士河出海口,最早发端于公元49年古罗马时期建立的伦敦城,是当时罗马人的统治中心。便捷的交通使其成为连接欧洲大陆与英伦三岛的桥梁,并为其日后成为贸易与工业中心奠定了基础。公元2世纪,罗马人为应对动荡的社会局面在伦敦城周围筑起了一道长约3.2公里的城墙,这道城墙直至今日仍是伦敦城的边界。虽然在罗马统治时期伦敦城即已成为英国最大的城市,但随着帝国的崩溃和欧洲的动荡,在此后的一千余年里,伦敦的城市边界并未向外扩展。12世纪,伦敦获得了自治权,这是中央权力对地方权力妥协的结果。优越的的区位优势,发达的国内外贸易使伦敦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快速增长。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不仅标示着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同时也使伦敦成为英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血腥的圈地运动使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为毛纺业与船舶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使伦敦在工业革命前就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伴随着伦敦作为英国政治、商业贸易、金融、工业中心地位的逐步确立,伦敦的人口也迅速增长,至1700年,伦敦的人口已由1500年的5万左右增加到57.5万。此时的伦敦已初步形成了都市圈的雏形,威斯敏斯特是政治中心,伦敦城是金融中心,伦敦西郊主要布局了商业及奢侈品工业,东郊与北郊则主要布局了造船、呢绒等工业。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后,伦敦虽然没有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中心,但凭借其贸易与金融中心的地位,人口增加仍然很快,1801年达到101万,此后年均增速约为2.14%,至1939年达到历史峰值891万人[1]87。
1944年,“巴罗委员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就伦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个轮廓性的建议,后又做了伦敦市和伦敦郡的规划。当时的设想是在伦敦周围48公里半径范围内建设4个同心圈,由内向外分别是:城市内环、郊区圈、绿带环、乡村外环。大伦敦的空间结构为由放射状道路与同心环路相交形成的交通网络连接的单中心同心圆圈层结构。1946年通过的《新城法》提出在离伦敦市中心50公里的半径内建设8座新城,以疏解中心城区过于密集的产业和人口,其目标是“既能生活又能工作,内部平衡和自给自足”。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编制的大伦敦规划试图突破原来圈层扩展的局限,沿城市的主要交通干线设置三个由中心向外扩展的发展轴,在长廊的终端建设三座具有“反磁力吸引中心”作用的城市,希望通过这种空间布局来解决大伦敦地区非均衡发展的问题。在老城区出现人口持续减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英国于1978年通过了《内城法》,对以前的城市发展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注重对老城区的保护和改造[6]。
1992年,伦敦战略规划委员会发布的白皮书强调,要重新振兴经济,以交通引导开发,构建更具活力的城镇体系,提高环境承载力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1994年,该委员会又发表了新的伦敦战略规划建议书,旨在强化伦敦作为世界城市的地位,更好地发挥伦敦在带动区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参与世界竞争中的作用,同时阐明了伦敦大都市圈和东南部地方规划圈之间的关系及发展战略。在城市结构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强化了城市中心的重新振兴,城市间网络的联系以及绿化带和河流在城市景观中的作用。1997年,民间规划组织“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发表了为大伦敦做的战略规划,该规划涵盖了伦敦经济、社会、空间和环境发展诸方面,根据伦敦不同地域发展水平的差异,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战略[6]。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伦敦将其强大的辐射力作用于广大的地域,逐步形成了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都市圈(伦敦都市圈又被称为“英国城市群”)。伦敦都市圈在空间结构上可以划分四个圈层:中心区域为内伦敦,包括伦敦金融城及内城区的12个区,占地面积310km2;第二个圈层是伦敦市,也被称为大伦敦地区,包括内伦敦和外伦敦的20个市辖区,总面积1580km2;第三个圈层为伦敦大都市区,包括伦敦市及附近区的11个郡,属于伦敦都市圈的内圈,总面积11427km2;第四个圈层包括大伦敦地区、伯明翰、谢菲尔德、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和众多中小城镇的广大地域,整个都市圈总面积约45000km2 [8]。
四、纽约:从低密度蔓延转向“精明增长”
纽约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哈得孙河口,濒临大西洋。其最早的居民点是曼哈顿岛南端的印第安人住地。1626年,荷兰人以极低的价格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曼哈顿岛,将其辟为贸易站,称为“新阿姆斯特丹”。1664年,英王查理二世的弟弟约克公爵占领了该岛,改称“纽约”。纽约在1686年建市,独立战争期间成为美国的临时首都。1825年,伊利运河通航,随后又修建了铁路,使纽约同美国中西部的联系得到加强,城市快速发展,纽约在19世纪中期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
由于工业化进程中工厂、人口不断向城市快速聚集,导致城市中心地区生活环境日益恶化,纽约在19世纪晚期即出现郊区化现象,当时迁往郊区的人口主要是城中的富人。在1920-1930年间,纽约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已快于中心城区。二战后,随着汽车的普及以及连接城市间的高速公路的大量建设,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和高收入的蓝领工人也开始蜂拥至郊区。与此同时,实行自动化流水作业的工厂也纷纷迁往城市边缘和郊区。大量工业园区、人口小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纽约周边地区呈“散珠”状随意分布、低密度蔓延,模糊了城乡的界限,使纽约从多中心空间结构向低密度的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变,形成了覆盖广大地域范围的大都市区、集合城市。
自上个世纪20年代始,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PA)先后对纽约大都市区进行了三次规划:
1921-1929年,第一次规划提出,其核心内容是“再中心化”。提出以环路系统引导理想都市景观建设;疏散曼哈顿的办公机构;由市内迁出的企业以及新建企业集中布局在郊区工业园中;在广大的整个地区范围内分散居住功能;城市增加更多的开敞空间以吸引白领阶层。建立开发公司,促进工业布局调整与卫星城建设。实际演进中的纽约大都市区并没有实现再中心化,相反,二战后小汽车的普及以及公路交通网的快速建设却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向郊区的低密度蔓延扩张,成为“铺开的城市”[9]1。
1968年,第二次区域规划发布。该规划提出:建设新的城市中心,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吸引人们到新中心就业和生活,使纽约形成多中心空间结构;住宅类型和密度更加多样化,以便让低收入者也能够住上普通住房;改善老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环境,重新吸引不同收入水平和各社会阶层的人;在新城建设过程中应注意对区域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为新中心配套更好的公共交通运输设施,以确保其对外联系的便捷。该规划同时考虑到了旧城衰退与郊区蔓延、住房供给、生态保护等问题。但自1970年以来,纽约大都市地区的郊区化趋势并未得到有效控制,80%的住房建在区域的外环地带,消耗了大量的土地,而中心城市经济衰退,城市土地得不到有效利用,出现了“空洞化”[9]1。
1996年,RPA发布了第三次区域规划。针对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3州大城市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社会严重分化、乡村被郊区化侵蚀、空气和水体污染严重等问题,主张增加对基础设施、社会、环境、劳动力的投资,为提高地区的生活质量,提出了“3E”目标。所谓“3E”即是指经济(economy)、环境(environment)与公平(equity)[9]1。
尽管3次规划的侧重点各有所不同,第一次规划的重点是试图通过“再中心化”促进中心城市的发展,第二次规划的重点是新城建设,试图通过人口的再集聚改变郊区低密度蔓延的状况,至第三次规划时,因环境与社会公平问题突出,故将重点放在重建“3E”方面,但三次规划均把大城市的发展与周边地区发展联系起来,从整体上加以考虑,做出统一安排,以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9]1。
纽约与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五座核心城市统摄的大都市区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连绵成一片,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的巨大的城市化地区——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又被称为“波士华”城市群)。
除上述城市外,韩国的首尔、德国的鲁尔、俄罗斯的莫斯科等大城市在空间扩展方式上也都表现出由单中心空间结构向多中心空间结构转变的共同特征,这些探索实践,对于有效防治“大城市病”、缩小不同等级城镇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四、结语
从世界各国大城市的成长历程看,大城市的发展表现为从单极集聚向多极分散发展的趋势,其空间结构表现为从单中心空间结构向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变的过程,体现了在集中中有分散,在分散中有集中的双向过程。各国政府都试图通过大城市这种空间结构的调整,引导产业、人口等各种要素在更广阔的地域合理布局,以带动区域的协调发展,增强大城市辐射区域的能力和大城市地区的整体竞争力,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并借此使“大城市病”得到有效缓解和治理。将大城市由单中心空间结构调整为多中心空间结构是世界各国在解决“大城市病”问题上的基本实践取向。“大城市病”也是长期困扰我国的一个难题,解决“大城市病”需要采取综合措施,但从城市空间扩展方式的角度看,我国的多数大城市,(下转第40页)
(上接第22页)单中心单向集聚的倾向非常明显,这是造成“大城市病”以及大城市与其周边地区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欲从根本上治理我国的“大城市病”,就要改变大城市目前的这种单向集聚的倾向,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宏观视角制定相应的规划、法律法规和政策,将大城市的部分要素和功能向周边地区疏解。城镇化要以都市圈、大都市区、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从而使大城市的空间结构由单中心空间结构向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化,这是增强大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区域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1]王涛.东京都市圈的演化发展及其机制[J].日本研究,2014,(1).
[2]张晓兰,朱秋.东京都市圈演化与发展机制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2013,(2):67.
[3]王健.天津与巴黎城市空间形态的比较分析[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428-429.
[4]赵婷.巴黎新城规划建设及其发展历程回顾[EB/OL].http://www.docin.com/p-889426491.html,20
15-09-29.
[5]袁朱.国内外大都市圈或首都圈产业布局经验教训及对北京产业空间调整的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06,(28).
[6]章昌裕.仅次于纽约和东京巴黎都市圈形成的特征[N].中国经济时报,2007-01-08.
[7]倪前龙.国外大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及其借鉴[J].上海合作经济,1997,(11):45.
[8]邓汉华.伦敦都市圈发展战略对建设武汉城市圈的启示[J].学理论,2011,(10):135.
[9]谷人旭.国际大都市的区域规划[J].地理教学,2005,(8).
责任编辑:邓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