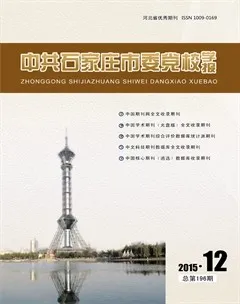全球化背景下李大钊复兴中华的思想理论及历史启示
[摘要]在中共历史上,李大钊是率先从近代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复兴”这一视角探索民族国家出路的先驱。他以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意识倡导了“民族复兴”理念,完美地诠释了全球化与“中华民族”、世界与中国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他的民族复兴理念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整个近代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一脉相承。
[关键词]全球化;李大钊;复兴中华
[中图分类号] D2-0 " " " " " " " "[文献标识码] A " " " " " " " " " "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5)12-0015-03
在中共历史上,李大钊是率先从近代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复兴”这一视角探索民族国家出路的先驱。李大钊在20世纪初期就以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意识倡导了“民族复兴”理念,完美地诠释了全球化与“中华民族”、世界与中国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
一、李大钊关于民族复兴的论述
“民族复兴”成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但民族复兴思想,应该说是近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当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在世界上的被动局面,积极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成为当时排满的一项主要的政治诉求。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又七次使用这个概念。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五族共和,这进一步增强了国人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中华民族”一词在报刊上更多地出现,其观念也进一步深入人心。这一时期李大钊在其文章中对民族的称呼有“吾民族”“吾之国族”,1917年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开始使用“中华民族”这个词语,主张合汉、满、蒙、回、藏融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这一词语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李大钊已经初具现代的民族意识,并积极倡导培育民族精神,实现对中华民族的更生再造。早在1916年,李大钊就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的“中华再造”“中华再生”“民族复活更生”等词语,隐含了“民族复兴”的思想,彰显出其救亡图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谋求国家统一等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李大钊更强烈地认识到“我们应该去做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下救济出来”。1924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会演讲“人种问题”,他说:“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贡献,大都以为是老大而衰弱。今天我要问一句,究竟他果是长此老大衰弱而不能重振复兴吗?不的!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得这民族复活的动机了!……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猛力勇进,要在未来民族舞台施展我们的民族特性,要再在我们的民族史及世界史上表扬显着我们的民族精神!”用“中华民族”“重振复兴”两个词表达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更指出中华民族应对人类文明有新的更大的贡献,彰显了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和决心。
二、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构建现代的民族国家
1914年8月,陈独秀在《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发表了《自觉心与爱国心》一文,对“爱国”与“爱国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指出,“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盲。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被,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几句话,不仅对“自觉心”与“爱国心”进行了阐释,而且还论述了这“二心”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在陈独秀看来,对一个不值得民众去爱的国家,可有可无,“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此番论调,对民族和国家的前途过于消极、悲观乃至绝望。陈独秀发表此言论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很多国家被卷入这次战争;国内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后,打着“国家”的旗号对革命党进行镇压。针对这种论调,李大钊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指出:“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要“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1]314,“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无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1]314-315,态度非常明确:第一,要建一可爱国家;第二,国民有能力去建。“民之于国,斯为甘心之爱,不为违情之爱。”[1]3171916年,李大钊在文中多次提到“中华再生”“中华再造”等词语,表明他不仅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理性的分析,而且把改造中国提到民族生存、民族复兴的高度来认识,他说:“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1]368,“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1]388。他鼓舞青年要努力肩负起“再造神州之大任”[1]358,“吾民惟一之大任,乃在迈往直前,以应方来之世变,成败利钝,非所逆计”[1]308。
(二)高举“新中华民族主义”旗帜,铸造民族精神,反对“亚细亚主义”,反对强盗世界
李大钊明确反对日本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高举“新中华民族主义”大旗。他高呼:“以吾中华之大,几于包举亚洲之全陆,而亚洲各国之民族,尤莫不与吾中华有血缘,其文明莫不以吾中华为鼻祖。今欲以大亚细亚主义收拾亚洲之民族,舍新中华之觉醒、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勃兴,吾敢断其绝无成功。”[1]494在李大钊看来,以中华民族在亚洲的重要地位,应该是亚细亚的主人翁,这既是一种不可谦让的权利,也是一种不可旁贷的责任。五族共和以后组成的新的中华民族,要建立高远博大之精神,统一民族思想。如此,“新中华民族主义确能发扬于东亚,而后大亚细亚主义始能光耀于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格局,也给了被压迫民族以契机,民族自决成为一战后世界各国的共同呼声。民族自决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内,反对专制,实现民主;对外,各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事务,不受外来民族的支配。李大钊针对日本提出的“亚细亚主义”,提出了“新亚细亚主义”,认为亚洲的弱小民族要想从西方列强中彻底解放出来,就要实行民族自决、平等联合,积极反对侵略,以求得民族独立与解放。巴黎和会使李大钊更清晰地认识到西方列强的强盗行为,认为巴黎和会所议决的事,都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2]221!因而,极力反对西方列强的分赃会议,主张“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三)主张中华文化的复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变动。一方面,中华民族生存危机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传统的儒家思想丧失了统治地位,改造中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各团体、各政治派别、政党等纷纷把眼光集中到西方,以寻求救国方案。西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乃至精神文化,国人大都采取了认同和肯定的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人对西方的文化产生了质疑,认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2]48。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大钊认真分析了东西方两种文明,认为东西文明分别为“动”的文明和“静”的文明,二者各有优劣,故主张中西文化应加以调和,创造“第三文明”,以“新中华民族主义”为旗帜,以俄罗斯文明为媒介,担负起创造“第三文明”的责任。同时,针对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采取了抵制的态度。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次大会的消息传出后,非基督教思想也开始勃兴。李大钊等人在《晨报》联合发表《非宗教者宣言》,紧接着又写了《宗教妨碍进步》《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文章。李大钊从宗教的本质、教义等方面入手,指出了它妨碍自由、妨碍平等、妨碍真理、妨碍进步的性质,而从更深层次来说,反基督教是在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从而从根本上维护我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与独立。
(四)提出了“中华民族无产阶级化”的理论
李大钊能够从世界形势之整体来认识中国形势,世情、国情相互比照,突破了传统文化局限于民族和国家的狭隘视野,使他能够以全球的视角来思考,来认识问题。同样,他把民族、国家置于全球的视域下来考量。特别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用唯物史观、阶级观点认识问题成为他的常态。他说,“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三、李大钊“民族复兴”理念的历史启示
(一)李大钊的民族复兴理念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整个近代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一脉相承
李大钊的民族复兴理念,勾勒出了近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轨迹,展现了近代仁人志士追求民族复兴而努力探索的爱国情怀,彰显了早期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迸发出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了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李大钊等人首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理论武器,而后创立了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22年中共二大制订了实现中华民族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最低革命纲领和渐次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党的二大第一次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3],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上的一个深化,它为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
(二)从“全球化”视角来看待“民族复兴”
李大钊思想解放,能够与时俱进,紧跟世界的潮流。特别是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观点、方法和“全球化”视野,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紧紧抓住当时世界发展的大势,在把握世情、国情的基础上,得出了中国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论断。他不是单向地看世界,而是双向地看;从中国看世界,又以世界观照中国。同样,全球化拓宽了其文化视野,使其能够从全球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东西文化:各有优劣,各有长短,主张二者相互融合,相互吸收。对待民族复兴,他从战后世界各国的民族运动中,看到了世界风云的变幻,意识到“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2]149,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故中华民族必须解放。同时,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中华文明应该对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其意蕴被习总书记赋予了最全新的表达——“中国梦”,它既是“对百年来中华民族为实现复兴而不懈奋斗历程的浓缩与概括,也是对当下中国人面向未来所有感情和力量的表达与凝聚”[4]。正因为中国梦承载了民族的希望,蕴涵了发展的动力,彰显了神圣的使命,相信,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李大钊全集:第2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李大钊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80.
[4]汪玉奇等.中国梦:昨天今天明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5.
责任编辑:李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