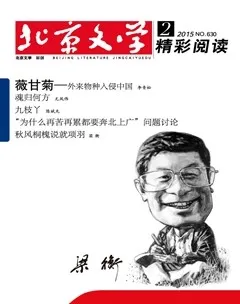苏东坡的东莞
在中国贬职流放史上,论及流放地方之多、流放时间之长,苏东坡当尊居榜首。“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贬得离京城越来越远,一路向南。黄州、惠州、英州(广东省英德)、儋州(海南),直至在应召回京时客死返京途中。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都是在“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人生阶段确立并高扬的。而那个与惠州相邻的东莞,亦因为苏东坡的到访,增添了无穷的光辉。
准确地说,苏东坡在东莞,并没有像他在黄州、惠州和儋州那样怀着一颗悲壮的心情,因为那里是贬职之地,而东莞则是他寻亲访友之处。世间最好的财富就是友谊,作为性情中人,苏东坡当然将东莞的一切当成自己的故乡,况且他所访的朋友竟然是名震南粤的东莞资福寺的方丈比丘祖堂。因与方丈比丘祖堂禅师佛缘极深,是忘年之交,苏东坡把满腹心事投入东莞的怀抱,在这块曾经孕育了博大沉雄的岭南文化的地方,步入了他另一个人生之路,打造他的莞式生活。
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惠州,一听说东莞竟是一步之遥,尤其是离比丘祖堂住持的资福寺隔河相望,苏东坡的心便恨不得马上到资福寺,来这里读经学佛,修身养心。但一到资福寺,竟然让曾久经沙场的苏东坡一下子就惊在那里。500罗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而那个曾不止一次梦到的德云罗汉竟然位列其中,那阵势似乎在向他问好。苏东坡静静地立在德云罗汉面前,久久不肯离开。
在那散发着佛经的清香禅室里,已近六旬的苏东坡像个小学生一样站在经书前,“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茫然不见其涯也。”
往事,随着那一册册经书在眼前掠过。
伫立在佛前,面对香烟袅袅,没有了声色犬马的放纵,没有了功名利禄的追逐,没有了风刀霜剑的欺逼,也没有了心若死灰的清冷,就像窗外的斜斜细雨,恬淡得似乎可以听到炊烟的说话。他思索着写一篇关于罗汉堂的文章。回到惠州居所后,他夜不能寐,兴笔疾书:
众生以爱,故入生死。由于爱境,有逆有顺。而生喜怒,造种种业。展转六趣,至千万劫。本所从来,唯有一爱,更无余病。佛大医王,对病为药。唯有一舍,更无余药,常以此药,而治此病。如水救火,应手当灭。云何众生,不灭此病。是导师过,非众生咎。此何以故?……
写罢便倒头酣然大睡,梦中赤蛇吐珠的景象令他暗暗称奇。感应就这样出现了,居然还有一个人跟他做了同样的梦。祖堂法师夜间睡觉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梦。祖堂法师迫不及待地来到苏东坡的住所。两人相见,都话梦事,惊讶不已。苏东坡百感交集,拿来清墨尚未干的书稿,在后面加上两人的同梦所见。写道: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金大贝皆东倾。众心回春柏再荣,铁林东来阁乃成。宝骨未到先通灵,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卜袭吉谁敢争,层檐飞空俯日星。海波不摇飓无声,天风徐来韵流铃。一洗瘴雾水雪清,人无南北寿且宁。”
苏东坡觉得还不过瘾,干脆拿出比自己生命还宝贵的佛舍利交给祖堂住持。这粒佛舍利是有来头的呀,这是朝廷赐号佛印和尚——宋代云门宗僧所赠。捧着苏东坡赠送的佛舍利,祖堂喜出望外,恭恭敬敬将文章和佛宝舍利带回资福寺后,用金银琉璃做塔,将舍利藏于塔中,将塔供奉在罗汉阁内。苏东坡曾就资福寺修建舍利塔作铭。
铭曰:真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明舍九州。此身性海一浮沤,委蜕如遗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结为宝珠散若旒。流行四方独此留,带犀微矣何足酬。璧来万里端相投,我非与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谁由,瑞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罗浮。
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对于一个被贬谪的文人来说,苏东坡的“宝骨未到先通灵,赤蛇白壁珠夜明”这首千古诗句,一时间让资福寺声名远播,海内外朝拜者络绎不绝,盛况空前。可惜在公元1277年,元将张弘范攻陷东莞,取佛舍利进京,这粒佛舍利从此不知所终。
在中国,文人的生命密码,就是用文人的骨气提炼出的精神。凡天才,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尤其在天才文人,他们天马行空,狂放不羁,更是遭遇排斥。泱泱中华五千年,文人贬谪举不胜举,他们将满腔的悲愤不平,孤独寂寞,凄楚忧伤,和对于生命的执着,对于理想的追求,构成了贬谪文学丰富多样的内涵。
苏东坡就这样站成了一种姿势。
苏东坡在东莞的数篇诗文,将一种化入目光融入血液的基因,将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与东莞历史文化、人文山水融为一体,华彩横溢,字字珠玑,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艺术的享受,更是生命质量的呐喊。苏东坡的笔轻轻一点,历史便在这里霞光万丈,资福寺顿时名声大噪,地位显赫,位列广东四大名刹之一,一时誉满南粤。清代被誉为“岭南才子”“两粤宗师”的郑小谷曾为资福寺撰联:“北宋访残碑,人去未忘罗汉果;东莞标古刹,我来曾吃赵州茶。”上联:“北宋访残碑,人去未忘罗汉果”,讲的正是资福寺与苏东坡的历史因缘。就在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苏东坡应召北返时,他仍念念不忘资福寺,夜宿韶州(今广东韶关),仍写信给好友朱行中,嘱其多护持资福寺。
世事沧桑,一切都会被岁月湮灭。而只有文化,只有精神,都够穿越时空,永远活在历史的长河中。为纪念苏东坡,1896年,莞人进士邓蓉镜在资福寺后捐建东坡阁,嵌苏氏《罗汉阁碑》(残石)于壁,直到1953年左右因故被拆。
贬职最大的希望就是官复原职或者再入仕途。“学而优则仕”,谁不想出将入相,光宗耀祖?“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这是苏东坡曾遭贬带着一家大小过太行山南行时写的一首《临城道中作(并引)》。他在引言里说:予初赴中山,连日风埃,未尝了了见太行也。今将适岭表,颇以是为恨。过临城、内丘,天气忽清澈,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忽悟叹曰:吾南迁其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书以付迈,使志之。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苏氏一家沿着太行山往南前行,到了赵州临城时,天气突然晴朗起来,能清楚地看见太行山的雄姿。中国人历来都有崇拜山岳的传统,他想这一定是一个吉祥的征兆。这个征兆一定就是自己不可能像柳宗元那样长期留在贬谪之地,而是像韩愈那样,很快就会被皇帝召还的。
他含着泪誊写韩愈写给柳宗元的《迎亲送神诗》仍记忆犹新。“愚谷留柳”的柳宗元,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以热情昂扬、凌厉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的抱负,却因革新被贬为邵阳(古称邵州)刺史,行至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过着“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的屈辱生活。10年后,被改派为柳州刺史。到柳州以后,虽是愁肠百结,但他感到在柳州,可以干一番“振发枯槁,决疏潢污”的事业,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尽管他那“十年践踏久已劳”的身体到柳州后又患上了“奇疮钉骨状如箭”和“支心搅腹戟与刀”的疾苦,甚至曾出现过“鬼手脱命争纤毫”的险情,但他仍然拖着病躯,以极大的热情在柳州传播儒学, 修复孔庙;破除迷信,动以礼法;激励百姓自爱奋发,改变滥杀牲口的恶习。同时,他针对柳州的现状,进行重大社会变革:废除奴俗, 解放奴婢;开荒挖井,发展生产。由于他的致力治理 ,柳州这座古城呈现出一派生机。平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在贬处,他感悟人生,将哀愁化作巨大的人生动力,即便被贬一方,也要造福一方,留名千古。他曾在柳州城头写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诗:“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可惜年仅47 岁,柳宗元就倒在贬所。“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为纪念柳宗元勤政为民,韩愈即兴创作了《迎亲送神诗》,苏东坡也怀念这位先人,含着泪誊写了这篇碑文。
相对柳宗元而言,同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则幸运得多,虽然一贬再贬,但时间不长就返京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韩愈反对宪宗皇帝欲倡导的迎佛骨活动,再次重走贬职之路。在潮州贬职的8个月里,驱除害人之鳄鱼,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农作物,赎放奴婢,兴办教育,使潮州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后来人们将整条江改为韩江,将潮州那座山改为韩山。当他遇赦北归过衡山时,便写下了《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味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8个月,改变了一座城市,也让韩愈的精神大放光彩。有关资料表明,韩愈到潮州之前,潮州只有进士3名,到南宋也就是韩愈之后,登第进士者就达172名,这正是他大开教育之功。有民间诗作为证: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事实与苏东坡想象的完全相反。当他还在赴英州(广东英德)的途中,政敌章惇、蔡京、来之邵等人又不断地在皇帝面前攻击苏轼,说他罪大恶极,贬谪英州仍不足以惩罚。于是,哲宗皇帝又两次对东坡加重处分,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这时的苏东坡,简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囚犯了。
看着苏东坡的满脸愁容,性格开朗的比丘祖堂将苏东坡引到寺院内的千年古树——再生柏旁。再生柏,顾名思义,曾遭受自然灾害劫后余生,一枝早就干枯,伸出的枝头仍顽强地立在风中,另一枝郁郁苍苍,似乎与晨钟暮鼓对话。“是心苟真,金石为开”,斜风细雨下的再生柏似乎给了他力量,他的嗅觉顿时敏捷起来,似乎又回到童年,回到眉山家门口那个石门,回到杭州西湖畔那缕缕杨柳。
“佛言诸法因缘生,再生柏历千年风吹雨打,即便惨遭电击雷霹也岿然不倒,何况一个曾执笔千里的文人?”比丘祖堂的一句话让苏东坡茅塞顿开,既然命运给自己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让自己走上贬职之路,那么就振作起来,像比丘祖堂所言:命实造于心,吉凶惟人召。信命不修心,阴阳恐虚矫。修心一听命,天地自相保。“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既然命运开了这个玩笑,那我就把握命运,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看着风中的再生柏,他的思绪随着叶尖上的露珠摇曳着,诗意便在清风里发散。“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一首礼赞东莞再生柏的诗娓娓道来:
生石首肯,奘松肘回。是心苟真,金石为开。堂去柏枯,其留复生。此柏无我,谁为枯荣?
方其枯时,不枯者存。一枯一荣,皆方便门。人皆不闻,瓦砾说法。今闻此柏,炽然常说。
云从龙,风从虎,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遇合,常常给人适逢其时的美感。苏东坡之于东莞,东莞之于比丘祖堂,从而有了一场斗志昂扬的东莞惠州建设演义。苏东坡再次来到东莞,听罢祖堂的诵佛后,将自己在谪贬之地惠州调研来的问题与比丘祖堂一一分析。他知道东莞与惠州山水相连,人情相近,比丘祖堂对东莞与惠州也相当了解。他认为:一、惠州城风景虽然很美丽,青山绿水。但是,由于惠州城四面环水,出入很不方便,尤其是一些老弱妇女出城砍柴割草和进行农业耕作,更不方便。苏东坡还亲眼看见有些妇女到西山去割草而掉进丰湖里。二、惠州常年天气比较炎热,雨水较多,比较潮湿,疾病流行。由于这里文化经济都比较落后,故缺医少药的现象比较严重。三、农业耕作技术比较落后。惠州虽然已超越了刀耕火种的时代,但是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少,没有什么先进的农耕工具。
比丘祖堂觉得路通才能财通,苏东坡完全可以将杭州西湖建设模式克隆过来。惠州城被西枝江分隔为两半:归善县城那半为水东,惠州府城这一半为水西。西枝江的江水流淌急峻,在西枝江流入东江的交汇处,原来是修有一座简陋的竹浮桥的,在五月间的洪水中已被冲毁了,现在只能用小艇来摆渡。但是,这个渡口又是城中的交通要道,行人很多。不少人因为船小摆动,人多挤逼而掉进河里去,认为在这里修一座用船只串联起来的船桥比较可行。“对,就搞这个‘两桥一堤’。”在平湖门和西山这两端各筑进一段堤,中间造飞楼九间以作桥,而造桥的木料全部改用罗浮山出产的坚硬如铁的盐木。按照这个方案建造的桥梁,气势宏伟,既可作为西湖中的一个景点,又可以作为一条交通要道,方便居民生产生活。
历史再次给苏东坡提供了生活的案例。苏东坡还采用比丘祖堂的建议,起用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由邓道士主持东新桥建设;起用栖禅院长老希固,由其主持筑堤工程。邓道士在西(支)江上,用40艘船连成20舫,上铺桥板,“铁锁石碇,随水涨落,榜曰东新桥”(《两桥诗辛辛苦苦引》)。从此两岸往来,安全便利:“岂知涛澜上,安若堂与闺。往来无晨夜,醉病休扶携。”(《东新桥》)而希固长老见资金不足化缘筹集资金,先“筑进两岸”为堤,再用“坚若铁石”“白蚁不敢跻”的石盐木在堤间建桥,取名西新桥。
绍圣二年(1095年)十月,惠州终于等来这个不朽的书生。书生办事,意气风发。他摊开图纸,建浮桥,立楼桥,筑堤坝,不出8个月这“两桥一堤”胜利建成了。竣工之日,惠州百姓欢欣鼓舞,兴奋异常,自发地在城西的西村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在寓惠期间,东坡还大力推广水力推磨,推广“秧马”,广泛施药,救死扶伤,掩埋无名尸骨,抗灾济民,建自来水工程,用自己的真诚厚意惠及乡亲。“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他仿佛看到昔日的荒蛮之地变成了车水马龙的闹市,人们安居乐业的盛景。
后来,惠州人民为了铭记苏东坡的功绩,便把丰湖的那两段堤称为苏堤,以作永久纪念。现在,苏堤已经成为惠州的重要文物景点之一。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阙写尽人生悲欢离合的吟唱词,对人生的体悟,对世事的豁达,都显出一种圆和无碍的通达和淡若浮云的苍茫。千百年来,仍旧在人民的心头弹唱,于思乡于怀古都是那么悠长恒久地激荡。词是写给与他共进仕途的弟弟苏辙的,兄弟之情、手足之意,淋漓尽致地展示着。那天,在东莞,王朝云弹着这曲千古绝唱,在场人无不感动得落下热泪。即便是出家多年的比丘祖堂,也紧紧地抓着念珠,一粒一粒地数着,或许他在捻数着家乡的亲人,或许他在捻数着离家的岁月——他真的醉了,是词让他醉在东莞的春风里。
“火那么壮大,水却熄灭它。水那么壮大,土却掩埋它。土那么壮大,风却吹散它。风那么壮大,山却阻挡它。山那么壮大,人却铲除它。人那么壮大,权位、爱恨、名利却动摇他。权位、爱恨、名利那么壮大,时间却消磨它。时间最壮大吗?不,是‘心’—— 当心空无一物,它便无边无涯。在名利面前,不须多惆怅,试向东莞探资福。”祖堂或许在自言自语。文人的力量,要么改变社会,要么丰富社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苏东坡的东莞,是真性情的东莞。他是一个乐天派,“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贬职生涯中,不管环境如何艰苦,他都微笑面对,“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人生风雨有几多?笑看我的超然情怀。曾在给资福寺的长老写的诗中就可以看出“累了就睡觉,醒来就微笑”的精神境界。“是是是。是资福,白老子。身如空,我如尔。无一事,长欢喜。东坡有,老居士。见此真,欲拟议。未开口,落第二。有一语,略相似。门如市,心如水。”(《资福寺白长老真赞》)
“门如市,心如水”,苏东坡的真性情更表现在他对家庭的态度上。
如果认为,像苏东坡这样的风流才子,又羁旅他乡,三妻四妾自不在话下,那就错了。在他的数百首诗词中,有三阙词作让人摧心扼腕、痛断肝肠,那就是关于他三任妻子的作品,表现出他至情至爱的真情。
王弗是苏东坡的第一任妻子,她在与苏东坡共同生活11年后因病逝世。悲痛欲绝的东坡,亲手在埋王弗的山头栽下了三万株松苗,把自己那一缕相思化成了三万株万古常青的松树,守候在爱妻身旁。在风雨中,他问亡妻:“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第二任妻子就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这个比苏东坡小11岁的进士之女,倒也看中了他的真情性,看中了他的爱恨情仇,感动于苏轼对妻子的深情厚谊,不顾一切地嫁给这个贬职的堂姐夫。想不到25年后,王闰之因病随堂姐而去。面对这个陪着他宦海浮沉,绝无怨尤的贤德妻子,苏东坡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苏东坡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10张罗汉像,又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将此10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
王朝云,12岁起就侍奉在苏东坡左右,她被大他26岁的苏东坡的深情打动着,“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无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姻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扶正后11年,33岁的朝云病逝,苏轼将她埋在惠州城西的丰湖边上,俯瞰二人一起开辟的放生池,一湖净水,有如朝云的一片丹心,令苏轼不忍重游。“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苏东坡的眼里流着相思血。
可以说,苏东坡对三任妻子的爱都是至情至深,对王弗“年年断肠”,即便在续妻之后,亦“不思量,自难忘”;对王闰之做到“生则同室,死则同穴”,真正实现了当初的誓言;对王朝云来说,更是“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比丘祖堂曾多次跟苏东坡说,俗人可以按照风俗纳妾,但苏东坡总是摇头,或许他放不下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他的誓言早就化作了三万株不老的青松。
在东莞,苏东坡颠覆了成功男人“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的所谓成功男人的定律,他用真情抒写了个性东莞。
责任编辑""" 张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