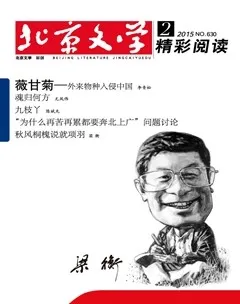国是之变 民必从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此话与中国的国情恰好相合,改革开放30余年,有深刻体会的就是这句话。市场经济,让中国人不再困守出生地与户籍所在地。乡下人与城里人一样,都是自由身。只要能找到解决饭碗之处,就是安身之处。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发生裂变,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的一次大地震。农民进城,宁肯让土地荒芜。说明城里的金比土里的钱好刨,不然谁愿弃家离舍,南下北上呢?农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生存场,做没有户籍的城里人,也不愿意困守一亩三分自留地。
时代之变,如此之烈。有资料证实,有2.8亿农民留城谋生存,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也跟随而至。最要紧的是,他们大部分没正规劳动合同,没法保障自得利益。新经济体中的制造商与建筑商雇佣农民工,将他们的利益最小化,由克扣拖欠工资,到少发与不发的事时有发生,但还是阻挡不了农民工进城。比如青年农民更愿意在城里,因为城里比在土地上干活风光,享受大城市的消费与时尚的风向标。新工业革命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联手,在全球新经济体中创造新劳动穷人。富士康在深圳聚集30万流水线工人,这些用青春换城市的行动背后,是没有技术价值再生产的“线工”。他们从事一个部件安装的重复工作,据某女工讲,她每天对着金属板打眼10000多次。当青春耗尽时,却没有掌握一技之长,只是流水线上的简单操作,工资能维持低品质生存。这种只掌握整体拼装某个环节的青工,离开工作岗位后,再就业的生存技能,基本为零。
《国家统计监测报告》称,在制造业工作的农民工占27.5%,建筑业占20%,其余53%聚集在第三产业。这个阶层是脱离土地后的中国新穷人,回到土地没有农业技术,根本不能靠种菜种粮为生。老农民懂得节气与时令,播种与收割。在新生经济体中催生新农业经济,已成为摆在中国农民面前的新课题。数日前,在陕西又有一批受过专业教育与培训的新农民,获得上级颁发的“职业农民”资格证书。他们的收入,比一般农民高20几倍。此项农业法规,将会吸引有识之“士”,回归田园,热心与土地打交道。习总书记出访美国,实地考察美国小镇的农庄经济,发达国家的农耕经验,有可借鉴之处。中国农业的发展,肯定要有大的改变,不然老土上,是留守老人们用最原始的耕作在种植,与时代步伐相悖。“职业农民”将会吸引徘徊在城里的农民工与大学毕业生。“田园将芜,胡不归?”新农场主的命名,并不比城里“线工”难听,只要懂得农业技术,肯流汗水,把准农业市场经济的脉搏,利益不会小。一位流水线工在城里的月收入与加班费,约一千七八百元或两千多元,租房后只活在维持生命的最低水平线而已。那些有头脑爱思考,觉醒意识强的青年,受不了制造业的呆板与重复劳动的无趣,他们越墙坠楼,用身体的破碎控诉现代工业的丑恶。他们不想回归乡土,置生命于虚无。不久前,富士康流水线上的诗人许晓东坠楼自杀,令人深省。他们与土地疏离,在城市的夹缝中求生。现实与理想相悖,导致放弃生命,诉说对现代工业的痛恨。
农民工进城,是时代大势。
城市人游移,也因国是之变。
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又怎样呢?从媒体说起,来深圳前是白领记者,到深圳变成蓝领记者。经历此种换位的人,要经受更多的考验。1994年元月,我南下深圳供职于《开放日报》,这是国务院特区创办的报纸,是中国首家股份制报纸。总掌舵的是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王强华先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香港分社等单位支援副总编数人。起初轰轰烈烈,报社养100多人的采编队伍。要保证报社正常运营,征订与发行是一项大任务,每位记者采编办报之外还要完成另外额度。虽说报社经营者用尽招数,但终归不解决根本问题,投资与回报难成正比,因无法与地方纸媒竞争更多的广告资源,离关门的日子就不远了。结果不到两年时间,照样关闭,刊号收回。此报后台不能说不硬。但投资方核算经营成本,一年1000万元,累积起来不是小数。深圳并非仅此一例,期刊也不例外。年头办年尾倒,也有持续办一年左右或更长时间的,那是少数。这个城市的大多数青工是小学与初、高中生,因而写日记的女工,当年成为时代新宠,就不难理解,很长时间文化沙漠成为此城的代名词。再后来深圳推举“打工文学”,为此城增光并由此普及全国。文学就是文学。只有中国才有这种旗号。这样的文学,品质怎样保证?“打工诗人”与“打工作家”满天飞。在世界文学平台上,诗人就是诗人,作家就是作家。只有中国生产等而下之的诗人与作家,仅命名就伤及人格与尊严。
再说深圳那些艰难生存的纸媒吧,其实用功能与金钱的关系,就如街边的婊子与嫖客。给钱就卖版面,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市场经济与文化事业相抵触,让许多文化人在深圳艰难前行,做市场的奴仆。时至今日,“虾报蟹刊”也难成气候。深圳30多年,有文化名刊吗?
国家重在改变贫穷,国情上演矫枉过正。为官贪腐严重,上梁不正下梁歪。民为谋利,无良心可言。一个抓钱抓狂的时代,背离先祖数千年追求的品德、良知、公义,却处于集体无意识。自由之人格,独立之精神阙如。许多人没有文化价值坐标的定位,从众是生存的万全之策。
国家的格调,决定民的格调。
本栏责任编辑 黑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