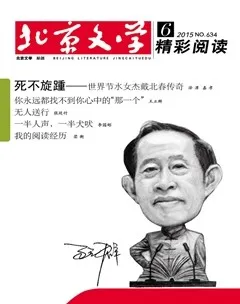清平湾一日
一
史铁生于2010年12月31日去世。4天后,即2011年1月4日,在京东大山子798艺术区举办有上千人自发参加的哀思会。会上得悉他捐献的肝脏植入38岁的天津患者,已能下地走动,立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铁生弥留之际,强撑着挨到红十字会奔来摘取器官的大夫到他身边,才吐出最后一口气,为使所赠器官处在鲜活状态。这是铁生以死救生的崇高。诚如他所说:“死,不过是一个辉煌的结束,同时是一个灿烂的开始。”
哀思会后,建立了由陈建功、王安忆、张炜、韩少功、张海迪、周国平、雷达等组成的“写作之夜”丛书编委会,编辑、出版了邵燕祥作序的《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极地之思——史铁生作品解读》等书。为把丛书编得更好,我们决定到史铁生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大队体验、考察一番。
2014年10月14日,编委们和插队知青们乘坐的车队,离开延安大学窑苑宾馆,驶往延川县。路过城东宝塔山,我想起1974年“文革”中第一次来延安傍晚登山看到的情景。那天我从延河边攀向山顶,想亲密接触革命圣地的象征——宝塔。山路崎岖,时有碎石尖插、躺卧在途中。接近顶部,暮色中看见前边有个挑水回家的受苦人绊了一跤,哎哟一声跌倒在地,两只水桶砰的一声滚落一边。好不容易从下面挑上来的水流个精光。见此,我悲从中来:抗战、解放战争中作出巨大牺牲的延安老百姓,至今仍过这样的生活,怎么对得起他们……
车队离开城区,向东北方行驶。由于朱镕基总理力推退耕还林,一路上沟沟洼洼、梁梁峁峁,种了不少树,群山郁郁葱葱,颇为悦目。
坐在面包车副驾驶座上的插队知青黑荫贵告诉我们:铁生下乡前参加过街道“红医工”培训班,到了村里,带着同住一个窑洞的孙立哲给老乡看病。立哲胆子大,先拿狗做试验,竟给疼得要命的老乡割去了阑尾。给难产孕妇动手术,发现自己和病人都是O型血,就抽自己身上的血输给她。老乡哭着求他:“你要倒了,谁来给俺看病啊!”当时有人质疑:孙立哲没有行医执照,怎能开刀?有关部门派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来考察了一个月,得出结论:孙立哲的医术相当于医学院毕业并有临床经验的专科医生的水平。消息传开,名声大振,老百姓称孙立哲是“神医”“救命菩萨”。
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抵达延川永坪镇。这儿曾是陕北苏维埃驻地,系红色根据地军政重镇。如今石油公司在镇上建了许多基础设施,并有输油管通过这儿,经济相当繁荣。当地人获悉孙立哲今天路过这里,便围住他坐的车子,跟他交谈。耽搁久了,领队着急,请大家让一让,放他走,说前方有许多老乡早在那边等着呢。
车队好容易挤出人群,沿着前面山谷夹峙的公路,向东南方开去。左边二三十米外,一直有条河相伴而行。荫贵说,这条清平河,直面关家庄,铁生在几篇文学作品中称它为“清平湾”。哦,我们终于来到了心中向往的地方。
二
车子拐过山坡一出现,关家庄村东就响起了爆竹声、锣鼓声、吹呼声。砰!砰!砰!叭!叭!叭!咚咚咚!咚咚咚!巨大的声浪震得清平湾山呼谷应、地动树摇。乡亲们举着“亲人回来了”“欢迎孙立哲重回关家庄”等横幅涌过来。司机停车,知青们、编委们跳下来,冲入欢迎队伍。我站在路边高坡上,看见人群里有举旗帜的,有打腰鼓的,有吹唢呐的,有跳秧歌舞的,有唱迎宾曲的,有跑旱船的,有撑彩伞的,有提灯笼的,有斜背大葫芦的,有手抱娃娃的……曾在这儿插队的女知青,搂着认识的婆姨,互呼姓名,嘘寒问暖。男知青跟一块儿干过活的老汉相拥相抱,诉说思念之情。人们混在一起,招呼、拉手、推挤,亲如一家。关家庄突然沸腾了。山也笑,水也笑,崖也笑,林也笑,秋阳在蓝天里也欢笑。你感到惊讶,这不大的山村,怎能一下子聚来千多个庄稼汉?你想不到这白毛巾缠头、朴素衣裳包裹、吃着粗粮的躯体里潜藏着火山喷发般的激情。这是心与心的交融,情与情的汇合;这是人民喜庆的节日,百姓由衷的狂欢。不到这里,你怎能想象在陕北山沟沟里,在一个极平常的日子,竟出现了闹元宵般的红火、热烈。
站在我身边的牛志强,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责编。他告诉我,1984年作品获奖后,他和北京作协几个朋友推着铁生坐轮椅回过关家庄。乡亲们把他团团围住,一双双粗糙大手抢着把他抱起来。一声声亲切问候,使他来不及应答。一个50多岁大妈,跌跌撞撞挤进来把铁生揽进怀里,又蹲下去抚摸他瘫痪的双腿,哆嗦着嘴唇说:“心儿家辛苦了,心儿家不简单,这个样子还写书!”铁生在关家庄住了两天,竟被乡亲们强请去吃了九顿饭。临走那天,村里人给他送了许多土特产,还有鞋垫、铺炕暖腰的毛毡。有个婆姨竟要把牵着的小娃娃送给铁生:“送他个小儿吧,心儿家苦哇,咋能成个家啊?”感动得铁生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锣鼓、唢呐、鞭炮声中,人们在拥挤、堵塞的路上慢慢往前挪蹭,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医疗站较宽敞的院子里。
三
知青和编委们在医疗站歇了一会儿,吃了老乡做的臊子面,迫不及待去探望铁生住过的窑洞。
那村外的窑洞属靠崖式结构,坐北朝南,冬暖夏凉。一排两孔窑,铁生和清华附中的几个同学住东间。如今空置在那儿,窗旁挂着“史铁生故居”的牌子。我贴近窑洞,从窗户外往里窥看,内有大炕、灶台。炕旁放着些家具。久无人住,蒙上尘土。
窑洞背靠崖畔,顶上杂长着几蓬蒿草。东边小坡上,有十几株细高的枣树。铁生初来这里,身体壮实,粮食不够,饿肚子时,曾用家里寄来的零钱换鸡蛋吃,还爬上枣树摘枣充饥。
领队请78岁的张老汉站在窑洞前说话。老汉说,分到俺队的20来个学生娃开始啥都不会,不会推碾,不会烧炕,不会砍柴。这窑洞里5个小伙砍柴,还不如一个12岁娃砍得多。可这些娃娃肯吃苦,经过几个月锻炼,锄镰镢耙样样会使,成了好受苦人。他说他教过铁生铡草、喂牛。铁生喂牛那个细心劲儿,玉米秆和草拾掇得干净,和主料拌得匀和,一夜几次起来照料,干这活不容易。有天暴雨夹着冰雹落下来,娃在野外受了寒,腰腿落下了病根。俺村以前家家户户修柜子,都要花钱请画匠。铁生娃画得好,串门免费画柜子。娃在俺村受苦了,俺们一直想念他……
接着编委章德宁、宗颖、邢仪、刘惊涛、柳青和赤脚医生朗诵了铁生写这儿生活的《插队的故事》《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之后画家邢仪拿出纸笔速写窑洞风景,王克明、庞沄等人则唱起了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和《圪梁梁》。歌声调动了叶廷芳编委的兴致,他自动站起来说:“我们面前流淌着清平河。想当年铁生会在月亮出来的夜晚,到河边看流水。那我就唱一首《小河淌水》吧。”接着他放开嗓门唱起来:“哎——月亮出来亮汪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哥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哥啊哥啊哥啊,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唱得委婉动听,声情并茂,余音绕山梁,博得叫好的掌声。
当叶教授在我身边坐下时,我伸出大拇指,说:“想不到你唱歌有专业水平啊。”他告诉我:“我上中学时,每天清晨到衢州市古城墙上练歌。考进北大德语系后,参加了大学生合唱团。1957年初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时,我们合唱团还到中山公园音乐堂给毛主席和伏罗希洛夫演出呢。”
最后全体来访人员排在铁生窑洞前合影留念。
四
文出延川。
历史上延川籍状元、进士、举人,多如河滩里的石头。以当代来说,延川就出了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他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至今仍是青年们最喜爱的读物。毕业于延川中学的曹谷溪,曾背着瘫痪的史铁生去看黄河壶口瀑布,曾任《延安文学》主编。生于禹居大队梁家河生产队的梁向阳,现任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1969年2月到延川插队的两千多名北京知青中,人才辈出,群英荟萃。除史铁生外,还有北京歌舞团的陶正,他和高红十合作的长诗《理想之歌》,诵遍大江南北,编入当时的语文课本。还有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先生。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吴美华女士。更有曾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7年、去四川取经、领导老乡建起陕北第一口沼气池的习近平总书记……这批扎根基层、接过地气、吃过大苦的知青,真正成了中国的栋梁。
那天下午在关家庄,我还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陕北剪纸艺术家高凤莲女士。2014年5月,我专程去中国美术馆观赏了“大河之魂——高凤莲大师三代剪纸艺术展”。我被陕北民间艺术的雄浑、大气、创造力、想象力彻底征服。高女士的剪纸内容广博,神话传说、戏剧故事、民俗风情以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全都信手拈来,仿若天成。她剪纸从不打草稿,胸有成竹,一气呵成,显出一位民间艺人的灵气和才华。看完展览,我在当天日记中感慨道:“智慧在民间,艺术在民间,天才在民间。”知悉高凤莲也到了关家庄,便请延川朋友带我去见一面。
我走进卫生院西侧一间房子,见大炕上盘腿坐着一位70多岁的婆姨。她花白的头发,宽阔的脸盘,红润的面色,硕大的耳朵,慈眉善目,一副祥瑞佛相。她见我进屋,脸绽笑容,眼梢漾现几缕皱纹,厚唇轻启,露出一口整齐白牙。我说:“您就是高凤莲老师吧?幸会幸会。”她双手放在膝头,朝我微微点头。我在炕沿坐下,好奇地盯着她那双巧手,问:“您的剪纸实在太精彩啦,谁教您的?”她微笑道:“俺延川妇女会生孩子就会剪纸,上炕剪刀下炕镰嘛。俺这儿女人一多半会这手艺。”我听了说:“哦,有了连绵高原的基础,才能耸立出巍巍巅峰。”朋友向我介绍:“高凤莲心灵手巧,干啥像啥。她担任过民兵连长、妇女主任、村支部书记。还是全村秧歌队的‘伞头’,村里办喜事时主持‘结发上头’的民俗高手。她是俺县的能人。”
高凤莲叫她女儿刘洁琼拿来两本精装的、沉甸甸的剪纸收藏集《大河之魂》,送给我和随后进来的德语文学权威叶廷芳教授。其时叶先生也侧身坐在炕沿上,正和斜卧在墙边铺盖卷上歇息的靳之林老人说起他当政协委员时写过关于建立国家民俗博物馆的提案。尊敬的靳老已86岁高龄,国字脸,寿星眉很长,面相很像具有汉学造诣、力主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他寡言少语,一副儒雅学者风范。这位耄耋之年的艺术家,是中央美院博导,长期深入延安地区,画出了气势磅礴的经典油画《南泥湾》。靳老是始皇帝抵御匈奴时修筑的陕北古迹秦直道的发掘者,是黄河民俗博物馆的倡建者,是乾坤湾阴阳鱼地形胜景的鉴定者,是高凤莲杰出剪纸艺术的发现者,因而也是她伯乐式的良师,更是法兰西颁发的“人类特殊贡献奖”金十字勋章的荣膺者。与这样一位艺术巨匠邂逅于关家庄炕头,是我人生的奇遇。
世界有时很小很小,我竟在史铁生的清平湾,近距离接触了当代两位艺术大师。这样,我的延川之行,就成了幸运之旅。
五
离开关家庄前,我独自出去,踱到村外清平河畔漫步。十月的秋风,掠过远处苹果园、近处枣树林,使空气里夹带了甜味。温暖的太阳已西移至窑洞后边的崖头。我望着对面山丘上一块块坡田,想象着当年铁生在这儿揽牛时留下的足迹和歌声。那是动乱时期,这一带树木稀少,受苦人一边放牛,还要艰难砍柴。庄稼汉们半饥半饱,吃上一顿白馍馍,是一种奢侈的盼望。40多年过去了,如今村里乡亲们的生活有所改善,这令我稍感欣慰。
我想起之前一天,在延安大学图书大楼学术报告厅举办的“史铁生的精神世界与文学创作”研讨会。会上韩少功、孙郁、李建军、甘铁生、解玺璋、岳建一、查建英等发言之精辟、深邃,是我在北京众多文学讨论会上很少听到的。最后,主持人邀我上台说几句话。我说:“这时候,在我们头上天国里,史铁生像颗辽远苍穹的星辰,默默照耀着我们。3年前,当铁生驾鹤仙逝时,我在798艺术区哀思会上,在玫瑰花丛和烛光摇曳中,写了这样一句话:‘铁生离开后所空出的位置,如今没有任何人可以弥补它。’现在,我要补充说,铁生身躯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灵魂、他的作品、他的思想没有离开我们,而是一直陪伴着、温暖着、启迪着我们。”这次来到关家庄,亲眼看到乡亲们和文艺家们对铁生的深情和敬重,说明他精神世界的高峻与辽阔。在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贪腐猖獗的世俗化、低俗化时代,铁生传承的思想境界和爱愿情怀,仿若雾霾中的明灯,特显珍贵。人啊,你要感悟:大美永存,不会泯灭。
正沉思于此,马路那边招呼我赶快上车。当我们的车队在老乡依依惜别中,缓缓驶离山村时,我忽然感到:从今以后,清平湾对我来说,已不再遥远……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