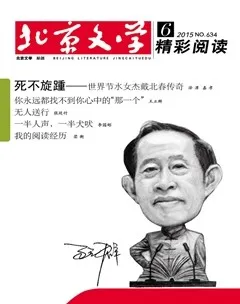院子
早晨起来推开窗户,对面的几幢高楼仿佛老熟人一样在向我打招呼。在晨曦初露的时候,这些高楼上半部是钢蓝色,下半部是橘红色,有一种海市蜃楼般奇幻的美感。
晨起出去跑步已经成了习惯。从两三年前的某个时候开始,想到和单位住得那么近,每天省去了上班路上的活动量,还是应该运动运动,于是就开始跑步。跑步在单位的院子里进行,跑过一条主干道,在5号楼前面绕一圈,就完成了。虽然跑得不长,但日积月累坚持下来,习惯成自然。
要是起得早,院子里往来的车少,院子里还是很清爽怡人的。春天里,粉红的桃花、黄色的迎春花竞相盛开,生气勃勃。四五月份雍容华贵的牡丹花也开了,像灿烂的笑容。七八月份月季花盛开,姹紫嫣红。五号楼前面的那条马路两旁,是高大的杨树,树干有一抱粗,挺拔矫健,风一吹树叶哗哗作响。杨树边有一片小树林,里面有硕大的雪松等树,这些树也有年头了,一眼望过去有些幽深,给人年深日久的感觉。还有几棵柿子树,秋天的时候红彤彤的柿子像红灯笼挂满枝头。
篮球场旁边有个小公园,是院子里的园子。公园里有两株白玉兰,春天里开花,花期很短。含苞欲放的白玉兰像一个个银白的杯盏,盛开的白玉兰像是女人优雅的手。
在时光的更替中,院子悄悄地变换着容颜。
想起第一次来这个院子报到的时候,我从西直门的家骑自行车到这里,从西到东贯穿北京城,路途似乎很遥远。那时马路也不宽,过了朝阳门就有些偏远,但我不觉得累,心中充满憧憬,一个新天地在我面前展开。那时心目中不止眼前这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的世界。年轻,就是对未来充满憧憬,前景无限,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
那时我们在5号楼办公,5号楼原先是个教学楼,房屋非常高大结实,冬暖夏凉,楼道里有个乒乓球桌,休息时我们就打乒乓球。我住在集体宿舍楼,晚上在办公室看书。每到黄昏的时候,到院子外面散步,公共汽车站总是黑压压地站满了候车的人,像潮水一样去了一群人,又冒出来一群人。看到车站,就想起远在西直门的父母的家,这时候有些想他们。那时交通不方便,我一般是一周回去一趟。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家里,每天上班在路上颠簸近3个小时。经过公共汽车上的拥挤、堵车,突出重围,到达单位,就像经过了一场洗礼。公交车经历也是生活磨砺的一种,生活对一个人的磨砺是多方位的。
燕京八景中有一景叫“金台夕照”。院子所在的位置就是金台路,“金台夕照”应该就在这一带,看不出这里的夕照和别处有什么不同。院子中的小公园里建了一个梯形的台子,叫“黄金台”,据说黄金台是古代设立用来招揽人才的地方。院子里现在可谓人才济济。单位像一个马力十足的庞大机器,每天风风火火地运转,每一个人都是机器上的螺丝钉。
早晨院子里显得风平浪静,就像风雨前的海面。
现在,世界似乎越变越小,小得就像这个院子,一眼就能望到尽头,我们正走向那个尽头。
西门那边正在修建的办公大楼,形状像一个巨大的企鹅。现在的建筑都是庞然大物,像科幻片中的未来世界。如今构成环境的重要元素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汽车、高楼、电脑。设想如果有一天电脑失灵,这些办公楼就瘫痪了。一位作家说,玛雅人预言的地球毁灭,在2000年时已经毁灭了,代之而起的是虚拟的世界。
在5号楼的后面,经常看到一个老太太提着一袋食物,在台阶上给流浪猫喂食,她给流浪猫取了名字,有花花、小黑等,一边喂食一边和猫说话。有一天不见了花花,老太太呼唤着:“花花,你回来吧。”声音很悲凉。后来不知为什么,很少看见这个老太太了。
在院子里还经常见到走过来的武警,走路很规范,有时远看是一个人在走,走近了才发现是一队人,即使是两三个人走,也要排成一队。编辑楼前面有一个旗杆,每天早晨,三个武警在这里举行升旗仪式,程序和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差不多,两个士兵正步走护旗到旗杆下,一个士兵扬手把旗展开,红旗顺着旗杆缓缓上升,场面很庄严。
起得早的还有清洁工,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挥动着大扫帚刷刷地扫马路。还有一群下了夜班的印刷厂工人,去食堂吃饭,说话的嗓门总是很大。
篮球场里有一些早锻炼的人,一群人或打羽毛球,或踢毽子,总是大声地嚷嚷。
有不少老人在小公园里打太极拳。院子里退休的老同志还有一种锻炼方式是步行,他们总是三三两两一起走,边走边谈论国内国外和身边的新闻。现在传播新闻的渠道有很多,他们在作新闻的解读,这是职业的惯性,这个院子里的人对新闻有特殊的敏感。他们退出了职业舞台,依然对世界充满好奇和热情。
我认识的那位老人好像从来没见他早锻炼过。他也住在这个院子里,两年前他离开了人世。
每次经过他住过的那幢楼,我就会想起他的音容笑貌,似乎他随时会从楼里走出来。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过年期间,我去他家探望他,他已经90岁高龄了,躺在床上,下不了地,他那一向看起来很健朗的身体好像很不甘心地侧卧在那里。一开始他记不起我是谁,后来总算想起来了,脸上绽开熟悉的笑容,谈笑风生。不久后,就听说了他去世的消息。老人的一生是一个传奇。他是一位诗人,年轻时家乡在日寇的铁蹄下沦陷,他投身抗日救亡和革命事业;在他为之献身缔造的新中国,因受胡风冤案的牵连,他蒙受了25年的不白之冤。他的正当盛年的25年是在被监禁、流放、苦役、凌辱中度过的,其中坐牢就长达10年。这样的苦难足以毁灭一个人。而他没有被苦难压垮,他挺直腰杆走过来了,苦难在他的强健面前显得无力。在监狱中他背诵唐诗宋词,将唐诗宋词翻译成新诗。获得平反后,他担任了报社群工部主任,接待了无数受冤屈的人,他自己是受过冤屈的人,感同身受,以满腔的热情为别人排忧解难。他也没有放弃写诗、译诗,见到他时,他时不时地送我一本他新出的诗集,有时是一本古诗今译集。去他家拜访时,总是见他埋头在堆满了书的书房里读读写写,他好像要和时间赛跑,没有时间停下来叹息,退休以后依然如此。我总在想,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走过那艰难的岁月?有些人经历这样的磨难,就一蹶不振了。而他总是对生活充满热情,每次见到他,他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他让人懂得,一个人的强健,不光是身体上的强健,还要有精神上的矍铄。
老人随着历史乘风远去,给我们留下苍茫的背影。一个人的一生,说起来也就那么短短的几句话,而生命的过程,是那么曲折和跌宕,丰富和复杂,既宏大又幽微,除了亲历者,谁又能真正体会?
现在院子里来来往往的那些年轻的面孔,伴着电脑、手机长大,有多少人会理解他这样的人生传奇?我们这代人对老人这样的上一代人在理解上已经有了沟壑,而这些年轻的新新人类看待老人这样的人生更是恍若隔世。
一代又一代的人走进这个院子,又从这个院子离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价值观,长江后浪推前浪。
从走进这个院子,到离开这个院子,一个人生命中的大部分都与这个院子相联系。进去时是风华正茂的青年,离开时已是白发的老者。一个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最好的年华也是在工作中度过。有一本书叫《我把青春献给你》,我也可以说“我把青春献给了这个院子”。在这里,痛并快乐着,成长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着,其中甘苦寸心知。人生的过程是一种历练,人生是一条不归路,走过了,经历过了,就不能后悔。
生活还是要继续。早起锻炼的人们,为了有一个好身体。即使生活中有种种的不如意,即使不再年轻,不再拥有那么多未来的日子,但还是要有一个好身体,更好地活着。我们究竟为什么活着?谁又能给出标准答案?这个问题被问了无数遍也被答了无数遍,每个人心中有自己的答案。好好活着其实也不容易,活着本身就是意义。
院子里7点过后,往来的车子多了起来,人也多了起来。忙碌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