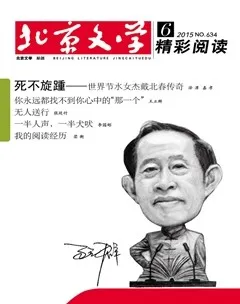校车事件(短篇小说)
2012年年初,一个礼拜日的早晨,我查看邮箱,发现一个题为“校车事件”的邮件,收件人有六七十人之多,发件人丹尼尔·欧文,我不认识:
礼拜五,也就是昨天,N城高中所有的3支篮球队——新生队、预备队、校队搭乘同一辆校车前往S城,参加那里的篮球比赛。
我已潜下心来揣测事件的深浅程度,电邮的前两行,将我下沉的心又托了起来,我看见我家西边的B路连同密歇根州一月的雪痕在眼前延伸,看见一辆“香蕉车”在B路上行驶,我的儿子陆小年坐在靠窗或挨近通道的位置。4个半月前,陆小年升入N城唯一一所公立高中,不久成为篮球队的一员,校龄减掉两个月,等于队龄。儿女小时候,一家四口喜欢在行车途中玩香蕉车的游戏,见到黄车,谁先喊“香蕉车”,谁就是赢家。
途中,校队的12年级学生布莱克·爱迪公然对新生队一个亚裔球员的种族特征进行嘲弄,他先笑嘻嘻地模仿了几个外语发音,接着,手横到新生面前,食指和中指间留一条缝(意即眼睛的形状),左右移动着,大声说道:“你看不见我!”
这里还有一些令人“心暖”的闪光点:那个新生队球员显然很不开心,他毫无兴致陪“插科打诨”者“一起玩儿”。车上的绝大多数球员都笑了起来,不是暗中笑,而是放声大笑,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点什么,即使新生队球员表现出明显的窘迫,成为布莱克公然戏弄的牺牲品。
你能想象么,布莱克的言行对新生队亚裔球员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在此之前,他或许一直在想,多么酷啊,坐在校车上,与两个高年级球队的球员在一起,和他的“野马”篮球队的兄弟们以及教练。
建议:和你的儿子谈一次话,我不认为你需要告知谈些什么,布莱克的所作所为,新生队球员的尴尬反应,你儿子的无动于衷,应已提供了足够的材料。
我们是否可以从组织得极好的喝彩助威的能量中拿出一点点来,用于道德品质的建设?
前进,野马!
丹尼尔·欧文
不忍搅扰小年周末的懒觉,我暂时咽下口中的疑问:你也是目击者吗?你笑了吗?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点什么?丹尼尔·欧文是哪个球员的家长?新生队亚裔球员又是其中的哪位?有一个瞬间,我的思维像长了脚,在最后的问题上绊住了,我心一惊,难道,除小年外,新生队再找不见第二张亚裔面孔?霎时,校车幻化成一出受虐剧的戏台,以我的儿子为绝对主角。宛若被一只飞来的篮球砸中头部,我的大脑冲入一个强烈的想法,为什么,为什么,儿子小年注定出生并成长于一个多重肤色的环境当中?自己受委屈可以;孩子,不行。
小年的爸爸大年读邮件时的身体语言,证实了我的判断没出差错,他的身体僵住了,一动也不动,说明有一个地方正动得厉害——他的心。
我把问题一一抛给大年,好似他是一部答问机:
“发件人是哪个球员的家长?”
“3个队30多个球员,没人姓欧文啊。”
“他是黑人还是白人,从姓名能分辨出么?”
“分辨不出。黑人球员一共才3个,新生队两个,校队1个,预备队根本没有。你问他是黑人白人干什么?”
“没什么,只不过,是白人,更显得公正无私。”
“只能说从比例来讲,白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他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旁观者清,我相信欧文儿子的眼睛,欧文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人,有其父必有其子。”
“学校怎么处理才合适啊?”
“不把布莱克开除出队,我决不答应。”
“这件事,小年怎么没跟咱们讲呢?”
“14岁了,又不是4岁。”
大年的回答,把小年一张童稚的脸和一句天真的问话推到我的眼前。10年前的一天,从幼儿园回到家里,小年问:“今天,艾米莉问我,你的眼睛为什么总是这样啊?”他学着,眼睛眯成一条缝。小年的问话,到了10年后的这个白雪铺地的早晨,我还记得一清二楚,连同他说话时的表情,连同我费力挤出的假笑及内心隐隐的揪扯。
早饭过后,小年取大年而代之,成为我的答问机,却极不情愿,又嬉皮笑脸:
“欧文是谁的爸爸?”
“我哪知道,篮球队没人姓这个姓。他说得太严重了,根本不了解情况。”
“布莱克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上了车,他突然兴高采烈地冲到我面前,大叫‘sing song sing song(唱-歌-唱-歌)’。”
“你没不高兴吗?”我明白sing和song都是单音节词,所以被用来模仿汉语发音。
“我也笑了。”
“你也笑了?”我想见当时的场景,想见他笑得何等地猝不及防,想见他笑过之后的窘迫,现在他不过是嘴硬罢了。他还不如说他哭了,更让我好受一些。我追问:“他又做了什么手势?”
“他就这样边移动边说:‘塞斯,你看不见我。’”塞斯是小年的英文名。小年右手横在眼前,大拇指朝天,小指无名指卷至掌心,食指中指间留一条缝。
“这时,你不高兴了?”
“有一点儿,只一点儿。如果这个人不是我,我还会笑的,布莱克的手势特别好笑。”
他所承认的一点儿,与他当时的真实感受相比,不过是一张乒乓球球案和一块篮球场地之比。我想说,你怎么不给他两句,你就那么软弱可欺?我忍住了。指责是轻而易举的,设身处地,14岁对17岁,9年级对12年级,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我改问:“就是说,你还是感觉受到了羞辱?”
“羞辱?”
“You felt humiliated.”我和他的对话永远以我汉语他英语的方式进行。
“没有。三年了,布莱克连任初中篮球夏令教练,他早就认识我才这样开玩笑的,哪有恶意?你知道吗,他是球星!礼拜五,他一人独得24分,投进两个3分球。”
“那个玩笑真给力啊,一车的观众为他捧场!”礼拜五,亏得小年好意思说。
“我们只是孩子!跟我开‘sing song’玩笑的人太多太多了,还有‘Hey,Asian! (嘿,亚洲人)’。”
对事件的把握我不禁又模糊起来,小年的心里是有杆秤的,他清楚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譬如在公共场所,他多次提醒我,别说“那个”。汉语的“那个”跟英语的“黑鬼(niger)”发音相近,被人听见易引起误会。但那杆秤,是否称量别人时准,称量自己,就失去准确度了呢?囚徒并不一定历数狱中遭遇,遭遇越是惨痛,越可能选择缄口。
跟小年谈话之后,大年的态度从强硬变得犹豫:“布莱克是校队主力,主力的主力,开除就算了吧,哪个教练乐意影响赛绩?”
“你说开除就能开除似的,缺了布莱克,校队就垮了么?”我答。
“让火箭队开除姚明,教练会怎么想?”
“你怕得罪了教练,小年进不了校队?”
“那是小年的最终目标,弄不好连预备队都进不了。打不成篮球,你还不如杀了他。”
等待的线绳,将时间的项链串连起来,一个钟点,一个钟点……我等待家长对欧文的回复,对小年的声援,对布莱克的质问,等待那一石激起的千层浪。5点了,也未溅起浪花一朵。我退而求其次,哪怕是喝倒彩呢,欧文的仗义执言也别无人理睬。我体会到一种人的心情,这种人宁肯臭名昭著,也不愿默默无闻。5点半左右,没等来电邮,等来了校队教练的电话,我抓住电话,像燥渴者抓住一瓶清凉矿泉水。第二天下午5点,教练安排了碰头会,他的态度很明确,决不姑息牵就,一定严肃处理。电话却并未使我对电邮的等待有所终止,我矿泉在手,还去抓可乐。我更看重家长的反馈。教练身在其位,发声是必须的,家长发不发声有选择性,相对更具分量。等待越是落空,欧文的形象越呈两极走向,忽而是犯了众怒的犯人,被放逐于边野荒塞自生自灭;忽而是悲壮的英雄,在我遐思的域界里腾扬飞升。中国和美国都是具有英雄情结的国度,英雄,不该是孤独的。就寝前大年出面作出回复,致了谢,也转述了教练的安排。碍于当事人家长的身份, 未群发邮件公开表态,为此,我深感歉疚。
夜不成寐,我的思绪围绕着碰头会七回八转。地点会选在哪儿呢?大礼堂的规格显然是过了,办公室倒是合适,又怕影响老师办公。大概是教室吧,也不该是小教室,怎么也要中号以上,盛得下三四十人才行。与会者需有一定阵容,倒也不必惊动校长,体育部门负责人到场就可以了,三个队的主教练都不可或缺。再有,就是布莱克的父母,做不到双双露面,一方露面也勉强通过,得饶人处且饶人。直至歉疚感拽我的思绪回欧文身上,大年的邮件,欧文会回复么?碰头会,欧文会参加么?猜测着,我才睡意渐浓,早晨醒来却心灰意懒,大约月亮和太阳换班时,不小心捎走了我的歉疚,将嗔怪遗落在我的怀中。我对碰头会上即将扮演的灰头土脸苦大仇深的受气包角色心生抵触,它平添了我“选美”的阻力。在美国,我受到一道双项选择题的长期困扰——中国,美国,哪一国更适合我?第二个选项以微弱或明显的优势频频胜出,我偏爱“选美”,有意无意,我缩小中国的利,美国的弊;夸大中国的弊,美国的利。我需要对自己选定的活法一次次作选择正确的心理暗示,久而久之,选择题成为我规律性的练习题,就像有人为维护心理健康,定时定点作冥想一样。选美阻力的增大自然令我不快,究竟,校车那一幕严重到什么程度,构得成一个事件么?兴许黑白交替之时即是非混淆之际,曙色微明中我确定了欧文的祸首地位,布莱克只勉强获取帮凶的头衔。我的思维方式,用一个字描述,就是“贱”。
这并不妨碍第一封回复进邮箱的“嘀铃”带给我莫大的惊喜:
丹尼尔·欧文:
假如此事确有发生,它必须引起重视,我会坐下来和我的儿子谈话。建立在种族之上的模糊观念是不能容忍的,我将期待儿子及其他球员予以抵制。
丹尼尔,你是否可以学会以下几点:
1. 此事应汇报给体育指导梅西和校队教练皮特斯,他们才是处理这类事件的恰当人选,我也相信他们能处理好。
2. 对布莱克·爱迪作没有根据的指称,并公之于众,你的做法令人难以接受。
3. 丹尼尔·欧文是你的真实姓名吗?如果是,建议你加以申明。如果不是,那么向如此之大的读者群发送煽动性极大的言论,无论真实还是不真,都是不坦诚的,懦弱的。下一次,用你的真实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