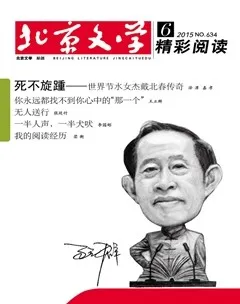张廷竹:时代激流的忠实记录者
张廷竹是个人物。他的经历丰富而曲折,命运跌宕而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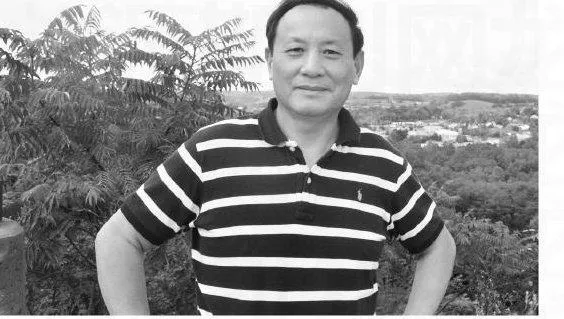
他,1950年6月出生于香港九龙,襁褓中由母亲抱回杭州定居;14岁小学毕业下乡插队,后来进船厂从锻工学徒做到分厂副厂长;34岁他参军上前线打仗荣立战功,然后从副营职一直升到正师职,以大校军衔转业后,当过台州市副市长,省建材集团、省石化建材集团副总经理,省文化厅正厅级巡视员。
他从来没进过初中、高中课堂,是一级作家、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92年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一路走来,张廷竹一直置身于时代激流中,以搏击奋斗体现人生的价值。对他来说,生活本身是如此的丰富多彩,而作家不过是个忠实的记录者。因此,无论在哪个岗位,他总是忙碌不歇,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抽出时间进行文学创作。自1963年他在《小学生作品选》发表小说《我的好朋友》始,迄今已发表和出版长篇小说10余部、中篇小说近70部、短篇小说70余篇及大量的评论、散文、通讯和报告文学等。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解放军文艺奖、庄重文文学奖、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40多次;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多次介绍过他的经历和作品;媒体称其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独特的战史作家”“跨世纪的一代优秀作家”,而他称自己是非职业作家。
一
上世纪80年代初,张廷竹住在一个老墙门里,一家三口住9.6平方米的房间,阴暗潮湿。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写作,他用什么纸都能写;不打草稿、不立提纲,一落笔文思滚滚、一泻千里,一行行遒劲秀气的字端端正正跃然纸上。
他每天写两三千字,一个月能完成一部中篇小说。在社会上曾引起强烈反响的中篇小说《五十四号墙门》《阿西系列小说》等,都是在那个小房间里写出来的。如今,张廷竹写稿已经用电脑了,不过,说起往事,对那个手写文稿的时光,他依然有一种深深地怀念。
张廷竹是个现实主义作家,从艺术角度言,小说是虚构的;但张廷竹的小说题材大多源于其家庭和本人的真实生活。
他曾整整一个冬天流浪在浙东沿海的城镇乡村,白天操剃刀给人理发刮胡子,赚几角钱换食糊口,晚上寄宿农舍或睡稻草堆。他漂泊在萧山、绍兴、宁波一带时,常常因摆地摊而被治安队驱赶得东躲西藏。他把这些经历作为题材,创作出了中篇小说《阿西流浪记》。
在写《阿西从军记》的时候,张廷竹没有拿过枪,在热心人的帮助下,他到守卫钱塘江大桥的武警部队,当兵体验生活。穿上军装,他和战士们一起出操、拉练、射击、投弹。他睡的床,刻着一行字:蔡永祥烈士生前睡的床。两个月后,他的《阿西从军记》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
1986年,张廷竹打完仗,从云南边防前线归来,带着一身硝烟,写出了他第一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阿波罗踏着硝烟逝去》。小说生动真实地描述和反映了我国当代军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献身国家的历程。发表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大众日报等媒体纷纷报道和发表评论,赞誉不断。
建国60周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30集电视连续剧《大路朝天》,便是根据张廷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是一部以改革开放、经济转型为背景的电视剧,讲述了一个个邪恶与正义、权力与金钱、信仰与背叛、个性与命运交织而成的故事。可以说,这部片子许多地方写的是张廷竹自己的生活。他在大型国有企业工作期间,曾与腐败分子进行过坚决的斗争,面对被监视、恐吓和辱骂的艰难处境,他没有妥协、没有屈服,直到腐败分子被送进监狱。送他去文化厅履新时,省委有关部门的领导宣读了对其考察的结论:“张廷竹同志长期忍受巨大的压力与委屈,与党内腐败分子进行坚决斗争,挽回了巨额国有资产损失。”
二
张廷竹为人耿直,嫉恶如仇。35年前,1980年清明节黄昏,杭州城河边,几个歹徒手持匕首,围殴抢劫一对情侣。男的被刺倒在地,浑身是血;女的跪在地上求饶。围观的人没有一个敢挺身而出。正巧,张廷竹骑车路过,他大喝一声跳下车来,冲进人群,向歹徒扑去。歹徒见状,纷纷逃窜。张廷竹盯住一个为首者,跨车追去,将其撞倒,经过一番搏斗,把歹徒押往附近的杭州机床厂门卫室。有两个歹徒转身过来想救他们的头头,张廷竹急中生智说:“我是公安局的,谁敢袭警,严惩不贷!”两个歹徒被镇住了,当场吓跑。
一个月后,张廷竹勇擒歹徒的事迹以2000多字的篇幅,刊登在《浙江日报》的显要位置上。
1984年,在文坛老前辈黄源、毛英引荐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将军在渤海之滨接见了张廷竹。后来成为浙江省军区副政委的范匡夫积极参与其中,驻中原某野战军军长杨石毅慧眼识珠,已届中年的张廷竹被特招入伍。
3个月后,他作为一名新闻干事走入了西南边境防御作战的战场。
打仗是生死未卜的事,出征时范匡夫等人为其饯行,一位副处长问他有啥需要交代的。张廷竹笑眯眯地说,如果我在战场上死了,请追认我为党员。副处长站起身,从孩子的练习本上撕下一页纸,说,写下来,就写这句话!
边境的大山浓雾弥漫,他腰佩五四手枪,肩挎微型冲锋枪,随侦察小分队去执行任务。他们穿行在丛林里,突然,他身后的指导员一声喊:“张干事,不要动,你脚下有绊发雷!”绊发雷很厉害,几颗M14地雷用引爆线连在一起,一颗爆炸,即刻引起周围的地雷同时爆炸。张廷竹闻声,立刻停住脚步,纹丝不动,像尊雕像。战友们撤离到安全地带,一个劲儿喊他:跳啊,你赶紧跳!
他满头大汗地说:“我的腿牺牲了!”
在大笑声中,张廷竹的表现还是赢得了战友们的尊敬。指导员不再叫他张干事,他伸出大拇指:“大哥,你表现真不错。”
张廷竹和侦察兵们进入炮火封锁区,在那里整整八个昼夜。一个早晨,他和一位战友往山上攀登。敌方从观察镜里发现了,看他30多岁的模样,胖墩墩的,军装上有四个衣袋,还以为他是个大官。刹那间,枪声大作。张廷竹和战友一起滚进战壕,他端起冲锋枪,哒哒哒一梭子扫射过去。冲锋枪子弹打光了,他又举起手枪还击,直到山下的战友们来增援他们。这时他才感觉胸前一阵火辣辣的疼,他撩开军装,胸口渗出殷红的血,他掏出军用匕首,用刀尖从绽开的皮肉中剔出一小块弹片。
这是1985年春天发生的事。夏天,他从边境载誉归来,胸前挂着叮当作响的军功章,仍然笑眯眯的,到处作报告。
三
1994年,他已是浙江省军区正师级研究员、后勤部副部长、大校军衔,突然递上一份转业申请书,他说:“人生是一本书,我要去地方的改革大潮中搏一搏!”
当年8月,张廷竹转业到台州地区担任副专员,后来当选为台州市副市长,分管外、侨、台事务和开放型经济工作,一度兼管金融和财贸。他跑遍台州各县镇,提出了“大经贸战略”。上下达成共识后,台州外贸和自营出口增长率明显提升。他还主持了一批区域名胜经济的规划、论证、申报、开发工作。
1997年秋,他调回杭州,在省建材总公司(改制后为省建材集团)当副总经理。他分管全省建材工业结构调整工作,主持制定了《浙江省水泥行业结构调整方案实施意见》,冲破重重阻力,带头拆除了147座低能高耗的水泥窑。张廷竹常常累得嗓子嘶哑,却依旧四处奔波,讲解结构调整的意义和政策。
2000年春节,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在一次大会上动容地说:“这位张厅长真不容易啊。这么大的压力,他都顶住了……”
今天,已从文化厅退休的张廷竹,依旧笔耕不息,百余万字的自传体长篇三部曲《绝地行走》《我以我血》《流失岁月》出版了,他重新写起最拿手的中篇小说。三年多来,他在《北京文学》发表了《江南梅雨天》《走进斜阳》,在《收获》发表了《闹市有草舍》《征衣》和《点解》,在《十月》发表了《孤驿》《城市的河》《后代》;还有《中国作家》发表的《拯救》,还有《江南》发表的《阁楼》和《一切归于平淡》等等。他的作品,绝大多数是这些刊物的头条,充分展示了一名成熟作家的高质量丰硕成果。作品的现实主义批判性深刻且一如既往,让人不能不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无论穿上军装或脱下军装,我都是一名战士。这是一种宿命。”
张廷竹的父亲张鹤龄是国民党爱国将领,13岁造反,16岁参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担任笕桥机场军代表时,张廷竹的外公是木工班头,外公的弟弟是设计师,笕桥机场因此成为张家历史的见证。张鹤龄曾因与贺龙等人密切交往和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被长期关押。1949年移居香港,1954年底飞抵台北即遭软禁,4个月后受尽折磨离开人间。张廷竹和他的六个哥哥姐姐在艰难困苦中长大成人。
在张廷竹家的客厅上端,悬挂着一块横匾,这是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题赠给张廷竹女儿的,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大字:忠良传家。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