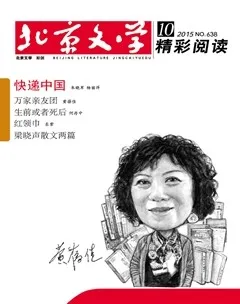爱情命题的再思索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自留地,远避尘世,隐遁神秘,李菁的小说正击中了我心中的自留地。我是在一个明媚的午后开始读李菁《再见,雪莲花女子》。起先,我担心其批判性稍弱,恐怕和针砭时弊挂不上钩,但文字雅致轻盈,读起来毫无压迫感,如沐春风的阅读感受很难让人拒绝。我就这样在夏末的阳光里,被李菁俊美的文笔带到了高海拔的藏区。“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拉萨的日光应该更为艳猛,一如李菁笔下的故事——刺目而炙热。
故事发生在西藏。很多人去西藏以求得精神洗涤,大二学生远涵独自一人踏上了西藏之行,在青朴偶遇女子薇莲。薇莲大远涵整整8岁,此行的目的是去阿里转山。两人结伴而行,辗转多地,最后在大昭寺分别。一路上,薇莲如孩童一样纯真、明媚,她身上有种来自大自然的宁静与张力,吸引着远涵。随着旅途的进展,两颗心越靠越近。两人在青唐酒吧彻夜长谈,话题不可避免地沉重而伤感。远涵得知了薇莲此行的缘由,也了解了她雪莲花般的气质来自曾经的伤痛与苦难。告别之际,远涵向薇莲表白,薇莲以“过早生涩,锋芒过利;过晚干涸,柔软不再”十六个字形容了这场萍水相逢。
优秀的短篇小说对于故事的架构颇有讲究。李菁在这方面下了功夫。虽然有爱情的内核,但《再见,雪莲花女子》披着藏区游记的外衣,这样的安排很讨巧,也成就了小说的个性。李菁不惜笔墨去描绘西藏的人文风貌,读罢让人身未动,心已远。可以说,西藏文化是这个爱情故事的灵魂——远涵和薇莲的爱情随着西藏游而萌芽,虽然无疾而终,但大众读者容易理解,毕竟旅途中的缘分归根结底只是一场陌路相逢。
小说并未因写情而落俗。远涵和薇莲的感情温克蕴藉,只有精神上的慰藉和支持,与藏区净化心灵的人文景观相得益彰。最后是凄婉离别的结局,但绝非悲剧,因为两人都找到了此行的意义。李菁笔下的故事较为独特,当不少小说在审丑的时候,她还在坚持审美。一些小说在赤裸裸地写社会的阴暗面,文字透着写作者的愤怒与焦躁,让人不忍卒读,读罢也是寒心泄气。李菁的故事里并非没有阴暗面,但她的文字看似不温不火,又积聚了巨大的正能量,熨贴人心,值得回味。
能写出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在这个年代恐怕是考验一个作家笔力的事情。李菁做到了,她的故事不仅给人美的感受,还让人陷入沉思。爱情是文学最常见的母题之一,在文学世界里,有太多仓促的感情,或悱恻缠绵,或云波诡谲。虽然读过不少爱情故事,但远涵和薇莲的故事还是让人感慨唏嘘,难道真的如薇莲所言,只有“君未白首妾未老”才是最好的遇见?记得几年前看过一部英国电影,叫《等爱的女孩》,由老戏骨朱迪·丹奇主演。戏中,丹奇跨越年龄的鸿沟,爱上了比自己小了近半个世纪的年轻人,但她不断纠结着一个问题,“当你心爱的那个人,果真迟到了50年才出现在面前,怎么办?”这大概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设问,这个设问直指本性,答案因人而异。或许如张爱玲曾在《爱》中写道,“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